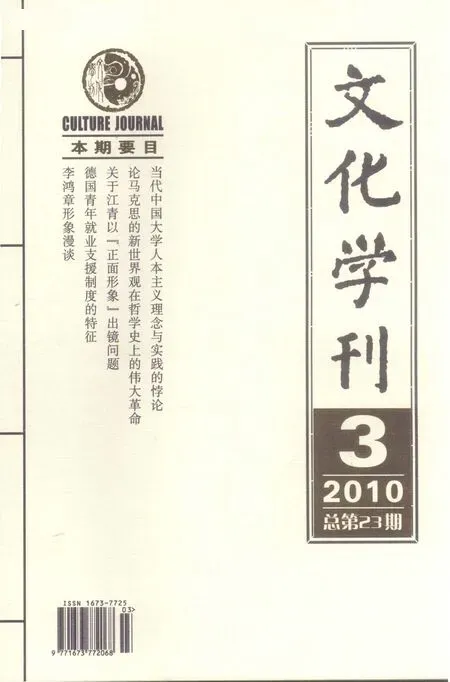東北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的社會(huì)學(xué)規(guī)律研究
高 穎
(沈陽(yáng)音樂(lè)學(xué)院,遼寧 沈陽(yáng) 110818)
所謂社會(huì)音樂(lè)生產(chǎn)是一種創(chuàng)造,產(chǎn)生音樂(lè)的人的行為活動(dòng)過(guò)程。[1]也就是說(shuō),音樂(lè)生產(chǎn)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過(guò)程,是一種行為活動(dòng)。“社會(huì)”中的音樂(lè)生產(chǎn),顯然其主角是人,這就使音樂(lè)生產(chǎn)具有了社會(huì)屬性。社會(huì)音樂(lè)生產(chǎn)涵蓋了音樂(lè)創(chuàng)作生產(chǎn)、音樂(lè)唱奏生產(chǎn)、音樂(lè)傳播生產(chǎn)、音樂(lè)伺服生產(chǎn)4個(gè)環(huán)節(jié)。這個(gè)意義上的社會(huì)音樂(lè)生產(chǎn)是一個(gè)龐大的社會(huì)音樂(lè)生產(chǎn)運(yùn)行體系。本文所涉及的東北地區(qū)音樂(lè)生產(chǎn)主要從創(chuàng)作生產(chǎn)所體現(xiàn)的地區(qū)一般規(guī)律性來(lái)探討。
一、東北地區(qū)民眾的精神需求是該地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的基礎(chǔ)
東北地區(qū)的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是十分豐富的。在民歌、民間歌舞、說(shuō)唱、戲曲、器樂(lè)的音樂(lè)生產(chǎn)上都有著豐富的內(nèi)容。同時(shí),因?yàn)闁|北是一個(gè)多民族聚居的地區(qū)。這里,既有世居?xùn)|北的狩漁獵土著居民,又有由于歷史原因外來(lái)的少數(shù)民族,更有著眾多關(guān)內(nèi)的漢族移民。紛雜的歷史和文化,使這塊雄渾粗獷的黑土地具有了豐富的色彩,這使得該地的民間音樂(lè)在多民族的土壤里顯得愈加光鮮而多姿。然而,無(wú)論這些音樂(lè)生產(chǎn)內(nèi)容、種類多么豐富多彩,卻始終沒(méi)有離開(kāi)這樣一根主脈——適應(yīng)東北地區(qū)民眾的精神需求。
(一)該地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的社會(huì)適應(yīng)性。
這里,僅以少數(shù)民族的部分民間音樂(lè)為例。從生活在東北地區(qū)的許多少數(shù)民族像滿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赫哲族、達(dá)斡爾族等來(lái)看,許多先民都經(jīng)歷了漫長(zhǎng)的狩漁獵生活階段。他們的音樂(lè)活動(dòng)行為中有許多反映狩漁獵生活的內(nèi)容。從史料記載和民族學(xué)保存的有關(guān)資料來(lái)看,東北民族保留的原始狩獵歌舞可以說(shuō)是較為原始的舞蹈形態(tài)了。而他們的這些音樂(lè)活動(dòng)行為具有鮮明的針對(duì)性和精神目的性。比如,他們的原始歌舞活動(dòng),總是與原始形態(tài)的生活環(huán)境、精神空間相聯(lián)系。他們把“原始的混淆不清的思維的各方面都結(jié)合在其內(nèi)容中。既表現(xiàn)了原始人關(guān)于自然現(xiàn)象和動(dòng)植物生活,關(guān)于宇宙結(jié)構(gòu)的空幻想象,還有關(guān)于自己來(lái)源于圖騰蒙昧的自我意識(shí)”[2],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赫哲族、達(dá)斡爾族、滿族等都有熊崇拜。比如,生活在大興安嶺地區(qū)的鄂倫春族曾把熊作為其祖先,自認(rèn)為是熊的后裔。[3]他們一方面把熊高度神化,另一方面又獵熊、分吃熊肉。因此,在處理獵殺死的熊的過(guò)程中,為避免神靈的“責(zé)罰”他們認(rèn)為要用和解儀禮。比如,割下熊頭后,要用楸木棒把頭插起,這時(shí)獵手們要齊唱儀禮禱詞:您是上樹(shù)上到半截閃腳死的;您是吃草籽后從巖上摔死的;因?yàn)槌蚤睒?shù)籽,您滑倒跌死的;因?yàn)槌源桌酰暨M(jìn)沼澤淹死的。這編造的理由正如研究者分析的是為避免熊靈的報(bào)復(fù)。可見(jiàn),儀禮禱詞在這里正是出于他們自身的精神需要而生產(chǎn)出來(lái)的。另外像人們?cè)卺鳙C之暇或歡慶場(chǎng)合所跳的《黑熊搏斗舞》(鄂倫春族)、《天鵝舞》(赫哲族)、《跳虎舞》(鄂溫克族)等等除了作為一種娛樂(lè)表演之外,也是人們對(duì)其圖騰的一種崇拜形式,是他們?cè)诟栉柚斜磉_(dá)內(nèi)心的虔誠(chéng)與敬畏。這種儀禮禱詞、圖騰崇拜表達(dá)出原始先民們模糊的音樂(lè)社會(huì)觀,卻體現(xiàn)出其鮮明的精神目的性。他們的音樂(lè)生產(chǎn)在形象中把人們的宗教想象,萌芽狀態(tài)的哲學(xué)世界觀,本民族的歷史等方面包含其中。這顯然表現(xiàn)出東北先民的精神世界對(duì)其藝術(shù)生產(chǎn)的呼喚。他們甚至是無(wú)意識(shí)地在從事音樂(lè)生產(chǎn),并在這項(xiàng)純凈的音樂(lè)生產(chǎn)中表達(dá)著精神需求。
(二)東北地區(qū)民眾的精神需求是該地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運(yùn)行模式的基礎(chǔ)。
東北地區(qū)民眾的精神需求不止在他們的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中體現(xiàn)出來(lái),同時(shí),它也構(gòu)成了該地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運(yùn)行模式的基礎(chǔ)。所謂的基礎(chǔ),在這里主要表現(xiàn)為“精神需求”在其音樂(lè)生產(chǎn)中體現(xiàn)的動(dòng)力源泉作用。從音樂(lè)社會(huì)學(xué)的角度上來(lái)看,一個(gè)地區(qū)或一定群體,不同音樂(lè)門(mén)類的音樂(lè)生產(chǎn)運(yùn)行模式是不同的。在中國(guó)當(dāng)代社會(huì)中,共有11種音樂(lè)生產(chǎn)模式。[4]這些音樂(lè)生產(chǎn)模式的形成與不同的要素有關(guān)。在東北地區(qū)的民族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中,其相應(yīng)民眾的精神需求是生產(chǎn)運(yùn)行模式中十分重要的要素之一。從這一角度分析,以“精神需求”作為該地民族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的動(dòng)力源泉或前提,并在“需求”的策動(dòng)下進(jìn)行音樂(lè)生產(chǎn)創(chuàng)作,那么筆者在上面提到的一些該地民間音樂(lè)的精神適應(yīng)性生產(chǎn)情況希望可以起到一定的說(shuō)明作用。這些民族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基本上都是以各自民眾的“精神需求”為創(chuàng)作生產(chǎn)的動(dòng)力源泉,由此引發(fā)的創(chuàng)作生產(chǎn)在不斷的完善中自然會(huì)得到東北地區(qū)人民的接受與喜愛(ài)。
在這種以“精神需求”為動(dòng)力源泉的音樂(lè)生產(chǎn)中,它的運(yùn)行情況筆者以圖示之:abc三個(gè)環(huán)節(jié)分別代表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唱奏、傳播;D代表伺服生產(chǎn);左右兩端的S代表社會(huì)精神需求動(dòng)力源泉和社會(huì)音樂(lè)接受動(dòng)力歸宿。

在中間的abc三個(gè)環(huán)節(jié)中,可能由于民族民間音樂(lè)的特定情況而出現(xiàn)其他的表現(xiàn)形式(如隱伏性),但其左右兩端的S卻相對(duì)穩(wěn)定。它標(biāo)志著以東北地區(qū)人民的精神需求為動(dòng)力源泉來(lái)進(jìn)行音樂(lè)生產(chǎn)創(chuàng)作。在此策動(dòng)下的創(chuàng)作、唱奏與傳播都是以這種“精神需求”為動(dòng)力源泉的。在模式運(yùn)行中可能并不能完全達(dá)到一種完美的境界,但這卻是東北民族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良性運(yùn)轉(zhuǎn)的表現(xiàn),同時(shí),也是對(duì)音樂(lè)生產(chǎn)本質(zhì)即適應(yīng)社會(huì)精神需求的一個(gè)肯定。
二、東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發(fā)展的不平衡性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滿族。從東北滿族逐鹿中原建立大清的一刻起,滿族就注定成為無(wú)法讓人忽略的民族。其實(shí)早在滿族先人女真時(shí)代,其音樂(lè)歌舞就已十分繁榮。東北滿族盡管由于多方面因素,其原型民間音樂(lè)已很難找尋,但從許多研究者細(xì)致耐心的考察結(jié)果中,我們?nèi)砸老】梢?jiàn)滿族民間音樂(lè)曾經(jīng)有過(guò)的繁榮。東北的滿族民間音樂(lè)從滿漢雜居或滿族聚居的情況看,是有所差異的。我們知道滿族民歌從體裁上大體有號(hào)子、小調(diào)、兒歌和各種儀式歌。如在東北廣為流傳的山歌小調(diào)有《跑南海》、《挖參謠》、《寡婦調(diào)》、《八角鼓,咚咚咚》等。兒歌有玩嘎拉哈時(shí)唱的歌謠,如“嘎拉哈,嘩啦啦,……錢碼頭,銅錢穿,稀里嘩啦上下翻……”;“紀(jì)靈靈,跑馬城,城門(mén)開(kāi),打發(fā)格格送信來(lái)。……”這種跑馬城游戲是模擬性的攻守游戲,可見(jiàn)滿族人的尚武精神自孩童時(shí)期起便有所表露。在一定場(chǎng)合和儀式上被傳唱的民歌有迎親時(shí)的《宮吹》,婚禮時(shí)唱的《合巹歌》,鬧洞房時(shí)唱的《拉空齊》,婚后跳喜神時(shí)唱的《阿司烏密》,葬禮儀式唱的《哭喪調(diào)》、《哭九場(chǎng)》、《哭十八場(chǎng)》、《解九連環(huán)》等等,甚至蓋新房時(shí)也要唱《上梁歌》。另外,薩滿儀式歌也是豐富多彩,可分為《家祭歌》、《請(qǐng)神歌》、《祭神歌》、《祭祖歌》、《請(qǐng)神詞》等。我們也都知道滿族的民間說(shuō)唱藝術(shù)影響較大的有八角鼓、太平鼓和子弟書(shū)。像八角鼓說(shuō)唱原是滿族先民在行圍涉獵之暇的一種自?shī)时硌荩笤饾u流行于八旗子弟間;太平鼓又稱“單鼓”,原為當(dāng)時(shí)滿族祭祀活動(dòng)中的一種形式。作為祭祀活動(dòng)的單鼓演唱,主要內(nèi)容有盤(pán)古開(kāi)天辟地、歷代神話故事等等;子弟書(shū)于乾隆年間文人創(chuàng)作,最初只在八旗子弟中流傳,后來(lái)民間鼓曲藝人開(kāi)始演唱,并流傳到盛京,稱為清音子弟書(shū)。子弟書(shū)作品很多,1954年傅惜華編著的《子弟書(shū)總目》計(jì)有446種,一千余部。許多研究滿族的學(xué)者都對(duì)這些影響較大的說(shuō)唱藝術(shù)進(jìn)行過(guò)考察,這里不再贅述。此外,在東北滿族人民中間也出現(xiàn)了戲曲。清代,在黑龍江、吉林等地區(qū)產(chǎn)生了滿族戲“朱春”。關(guān)于它的產(chǎn)生有眾多觀點(diǎn),普遍認(rèn)為是在八角鼓說(shuō)唱、莽式空齊歌舞等基礎(chǔ)上產(chǎn)生。滿族民間音樂(lè)中其歌舞包括民俗歌舞和薩滿教歌舞。據(jù)滿族音樂(lè)研究者考察其宗教歌舞有《請(qǐng)神調(diào)》、《排神調(diào)》、《勃勃神調(diào)》、《背燈調(diào)》等十幾種;民俗歌舞有莽式舞、揚(yáng)烈舞、野人舞、韃子秧歌等。遺憾的是據(jù)學(xué)者考察目前流傳下來(lái)的就只有莽式舞了。據(jù)《寧古塔紀(jì)略》記載:“滿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duì)而舞,旁人拍手而歌。”現(xiàn)在黑龍江省寧安縣尚有傅英仁老人保存的《東海莽式》手抄本。這些民俗歌舞大多都是反映滿族早期狩漁獵時(shí)代的生活。滿族民間樂(lè)器大部分都是擊奏樂(lè)器,流傳最廣的是八角鼓,其他還有抓鼓、扎板、幌鈴等,除擊奏樂(lè)器外,還有口弦、牛角號(hào)。再來(lái)看東北另外的一些少數(shù)民族像鄂倫春、鄂溫克、赫哲、達(dá)斡爾等。他們的音樂(lè)生產(chǎn)在不斷的完善中,已出現(xiàn)了民歌、歌舞、說(shuō)唱、器樂(lè)等體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dāng)我們把目光投放到上述同一歷史時(shí)期(主要是滿清統(tǒng)治時(shí)期)便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這種音樂(lè)生產(chǎn)表現(xiàn)出來(lái)的不平衡性。相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滿族民間音樂(lè)的綜合發(fā)展來(lái)看,這些民族的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便顯得發(fā)展較簡(jiǎn)單了。由于他們長(zhǎng)期處于東北邊遠(yuǎn)地區(qū),過(guò)著狩漁獵的生活,因此他們的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中反映原始狩獵生活的歌曲、歌舞較多,并成為他們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的主要內(nèi)容,有許多至今還保留著。如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的獵歌,赫哲族的漁獵歌以及一些原始狩獵歌舞等,像前面提到的鄂倫春族保留下來(lái)的《黑熊搏斗舞》就是早期流傳下來(lái)的模仿野獸動(dòng)作的舞蹈;表現(xiàn)達(dá)斡爾族早期狩獵生活的《哈肯舞》既有雄鷹在天空翱翔,又有林中的鳥(niǎo)鳴和熊吼;鄂溫克人的“愛(ài)達(dá)哈喜楞”(野豬搏斗舞)和“高樂(lè)不堪”(歡樂(lè)之火舞)也是對(duì)其原始狩獵生活的再現(xiàn)。盡管后來(lái)發(fā)現(xiàn)的一些說(shuō)唱藝術(shù)其價(jià)值和影響是深遠(yuǎn)的,如赫哲族的伊瑪堪、鄂倫春族的摩蘇昆以及一些薩滿教儀式歌舞等,民間樂(lè)器也有口弦琴、手鼓等,但從整體上看,他們當(dāng)時(shí)的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狀況同滿族比起來(lái)還是較為緩慢與簡(jiǎn)單的。他們的音樂(lè)產(chǎn)品其影響力也遠(yuǎn)沒(méi)有同時(shí)代的滿族大。上述關(guān)于該地少數(shù)民族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發(fā)展不平衡性的闡述,只是截取東北音樂(lè)歷史長(zhǎng)河中的一個(gè)片斷作為代表。這種不平衡性一直以來(lái)都應(yīng)當(dāng)是存在的。從哲學(xué)觀點(diǎn)上講,我們知道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決定其上層建筑的情況,因此民間音樂(lè)這種意識(shí)形態(tài)顯然也會(huì)受到其民族自身發(fā)展水平的影響。從各民族自身社會(huì)化發(fā)展進(jìn)程上看東北多民族間的發(fā)展進(jìn)程都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會(huì)導(dǎo)致其音樂(lè)生產(chǎn)發(fā)展的不平衡。
從清代以來(lái)東北少數(shù)民族的發(fā)展進(jìn)程中可以發(fā)現(xiàn),一方面處于邊遠(yuǎn)地帶的一些民族長(zhǎng)期保存著濃厚的原始社會(huì)殘余,一直處于民族形成期,沒(méi)有本民族的語(yǔ)言文字。另一方面,通過(guò)一次次的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一些古老族系中出現(xiàn)了一批批較先進(jìn)的民族共同體如滿族、朝鮮族、蒙古族等。像滿族,繼蒙古族之后在本民族不斷強(qiáng)大的過(guò)程中,建立了統(tǒng)一的全國(guó)性政權(quán)。這些民族的不均衡發(fā)展,對(duì)其自身的文化(當(dāng)然包括音樂(lè))會(huì)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xiàn)在音樂(lè)上,涉及到音樂(l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fàn)顩r。第一,從這些音樂(lè)生產(chǎn)者本身的精神需求來(lái)看。據(jù)資料記載,清以來(lái)東北地區(qū)的一些邊疆各部落至解放初一直處于氏族社會(huì)階段或稱為原始氏族末期。依靠自然經(jīng)濟(jì),不甚穩(wěn)定的物質(zhì)生活使他們一方面忙于狩漁獵,另一方面把自己的精神需求被動(dòng)地局限在封閉的生活中,體現(xiàn)他們精神需求的音樂(lè)生產(chǎn)主要是把其原始的生活面貌簡(jiǎn)單地藝術(shù)化重復(fù)。反之,發(fā)展較快的民族如同時(shí)期的滿族,在他們自身民族發(fā)展強(qiáng)大過(guò)程中充滿了曲折、艱辛,同時(shí)也與外界交流不斷增多,這些本民族成長(zhǎng)的歷程、生活的變更、視野的拓展,使?jié)M族人民的精神需求、情感表達(dá)更加多元化,反映其精神需求的音樂(lè)生產(chǎn)也會(huì)隨之豐富起來(lái)。例如,筆者在對(duì)滿族戲“朱春”的資料整理中發(fā)現(xiàn),盡管當(dāng)時(shí)在東北滿族聚居地人民生活較其他地區(qū)滿人仍較封閉,朱春劇目被保留下來(lái)的也較少,但從有記載的資料中統(tǒng)計(jì),它的劇目?jī)?nèi)容還是較豐富的。有關(guān)于祭神、祭祖的;有關(guān)于滿族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戰(zhàn)爭(zhēng)中的傳奇人物的;有關(guān)于滿族神話、傳說(shuō)、民間故事的,甚至還從漢族文學(xué)中移植過(guò)來(lái)一些戲曲和傳奇故事。考察到的劇目如《祭神歌》、《祭龍王》、《額真汗》、《濟(jì)爾圖勃格達(dá)汗》、《胡獨(dú)鹿達(dá)汗》、《雁門(mén)關(guān)》、《穆桂英大破天門(mén)陣》、《張郎休妻》、《關(guān)公斬蔡陽(yáng)》等;第二,從各民族的發(fā)展和社會(huì)化進(jìn)程所帶來(lái)的社會(huì)影響上看,發(fā)展程度較快的民族,不僅更大程度上推動(dòng)或引領(lǐng)社會(huì)進(jìn)程,同時(shí)作為歷史舞臺(tái)的“寵兒”也會(huì)極自然地受到外界的關(guān)注,并有更多機(jī)會(huì)觸及外界,這應(yīng)當(dāng)是自然的規(guī)律。表現(xiàn)在音樂(lè)生產(chǎn)上,他們的音樂(lè)會(huì)自然受到更多人的關(guān)注,也會(huì)更有機(jī)會(huì)關(guān)注他民族的音樂(lè),直至兩者互相影響,這當(dāng)然會(huì)促進(jìn)其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發(fā)展。而相對(duì)發(fā)展緩慢的民族,一般來(lái)講受外界關(guān)注的程度較低,其自身對(duì)外界的接觸也非常局限,這會(huì)使他們的音樂(lè)生產(chǎn)更加不易引起關(guān)注,也使得其發(fā)展更為緩慢。這種規(guī)律,有些類似于西方學(xué)者曾提到的馬太效應(yīng)。值得慶幸的是,現(xiàn)在越來(lái)越多的人們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少數(shù)民族民間音樂(lè)中的許多有價(jià)值的音樂(lè),并早已開(kāi)始搜集與整理,如赫哲族的伊瑪堪、鄂倫春族的摩蘇昆等等。
綜上,東北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受其特定的人文地域影響,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這些規(guī)律有著一定的代表性,并體現(xiàn)出了東北民間音樂(lè)生產(chǎn)的良性發(fā)展?fàn)顟B(tài),通過(guò)這些規(guī)律的考察為保護(hù)推動(dòng)其民間音樂(lè)的健康發(fā)展希望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1][4]曾遂今.音樂(lè)社會(huì)學(xué)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7.108,137.
[2]格·尼·波斯波洛夫.論美和藝術(shù)[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284.
[3]秋浦.鄂倫春社會(huì)的發(fā)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