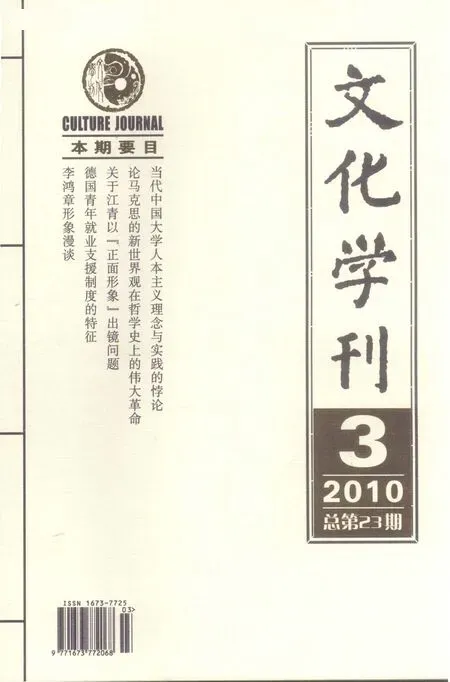從展示官場生態到揭示官員心態
蘇楷越
(作者系暨南大學中文系學生)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以著力描寫當代中國社會官場現狀、展示官場復雜險惡、記錄官員命運沉浮的“官場小說”應運而生。特別是當湖南作家王躍文的長篇小說《國畫》推出后,一批“官場小說”更是接踵而至。從王曉方的《駐京辦主任》系列到丁邦文的《中國式秘書》,從李國征的《后備干部》到吳國恩的《文化局長》、《宣傳部長》等,令人目不暇接。近十年來,“官場小說”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據有關機構統計數字顯示,僅2009年1至3月出版的“官場小說”就多達123種。十多年間,“官場小說”之所以暢銷不衰,自然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社會空間。在這十多年里,作為一幅幅當代中國社會官場“清明上河圖”式的生態長卷,“官場文學”走過了一條從人物設置簡單蒼白、故事情節程式化到對官場生態和官員心態進行深入透徹解析、充分揭示官員復雜內心世界這一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歷程。在從步入“類型化”到走出“類型化”的過程中,“官場小說”的讀者也經歷了一個從單一的窺視欲滿足“官場教科書秘笈”,到看到更多揭示官員復雜情感天地、細膩展現世間官場日常生態的階段,這不僅僅只是分享作品中艱難式的教化和啟蒙、腐敗官員與反腐力量的較量,更是一次閱讀境界上的超越。這一切都需要涉獵官場題材的作家不能陷入“類型化”創作的模式,而應進一步地拓展思路。正如作家吳國恩在創作《文化局長》和《宣傳部長》時感言:“文學應該是放射狀的,官場作為一種存在,成為文學描寫的一個對象。我不過是借助官場這個殼,而它的核,卻是文學所共同關心的東西,人性的存在及其變異。”只有在創作時具有這種認識,才能使作品有所突破。
一、走出“類型化”的模式
近年來,隨著“官場小說”的熱涌,“官場小說”逐漸走向“類型化”,逐步呈現出文字淺顯易讀、編撰情節共性、故事離奇、戲劇性強、人物性格單薄、人性探索功能乏力、社會批評功能退化等特征,致使“官場小說”中的官場原生態展示特性加強,文學審美愉悅作用削弱。有人說,小說創作的“類型化”是普通人閱讀趣味的勝利,也是文學大眾化的勝利。但在“官場小說”日趨“類型化”的過程中,“類型化”對“官場文學”只起到了簡單摹寫現實但又不能真實反映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的作用。于是,一批以“類型化”的面目匆匆出現的“官場小說”,只能在故事淺顯、人物單一、一味追求情節熱鬧的模式中徘徊,以此滿足那些對官場充滿窺視欲者的獵奇心態。在功利目的鮮明的營銷手段推動下,不少“官場小說”還被一些網站的讀書頻道分為“入仕必讀書”、“晉升必讀書”、“守位必讀書”等。這樣的“官場小說”分類法,自然也會使一些作家在創作時弱化文學審美功能和批判精神,過度沉浸于官場權利旋渦、人性險惡、黑幕交易的情節編織事件中不能自拔。文學批評家楊劍龍認為,中國“官場小說”乏善可陳,陳舊的全知敘事者視角,兇殺與情色元素,行文間缺乏多義性,滿足于“批量復制揭秘”,同樣的東西讓人看多了必定起膩。面對在“類型化”過程中“書名雙胞胎、內容克隆沒商量、重復雷同之作比比皆是”的“官場小說”,這些作品似乎都相當于工業化大生產中固定型號、標碼的零件,只要按其型號組裝完成,就可順利下線出廠上市。
這些“類型化”的“官場小說”也許會表層刺激讀者的感官,但絕不會在深層觸動他們的靈魂,激活他們的情感。由于受圖書市場營銷的“類型化”左右,對“官場小說”的寫作者來說,首先是在落筆之前就有了一個類型的清晰界定,人物命運、故事情節等都在依照“類型化”的生產模式,在流水線上組裝完成。也許在一些批評家看來,“官場小說”只是銷售過程中的一種分類方式。但正是由于這種“類型化”的分類方式,在作家心中過于強化,使他們只注重展示官場生態圖,為了滿足人們對官場文化特有的獵奇心,甚至還不停地往官場這鍋湯里添加各類暴力、色情、秘聞野史等諸種暢銷流行元素。在這種以“類型化”模式批量生產出的“官場小說”里,無論是《領導司機》、《市長司機》、《誰坐在市長前面》、《中國式秘書》、《市長秘書》、《秘書長》,還是《國稅局長》、《質監局長》、《反貪局長》、《掛職》等大量“官場小說”,往往只停留在揭秘式的事件陳列過程上,并未著力從文學角度去塑造人物形象,并未以批判的精神審視“官場文化”這一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遺存下來的怪胎、深入解析官場中人性的扭曲變態。這樣,在一大批“類型化”的“官場小說”中自然也就很少出現諸如王躍文的《蒼黃》、《梅次故事》、《國畫》,吳國恩的《宣傳部長》、《文化局長》,王曉方的《公務員筆記》等突破“類型化”模式束縛,真正對官場政治生態、官員心靈世界充滿人性關懷,對中國特色的“官場文化”給予深入透徹解讀、真實生動再現的優秀“官場小說”佳作。《蒼黃》等作品再一次告訴我們,在“官場小說”的創作中,不能只停留于初級“類型化”階段止步不前,而要加大人物塑造和立意開掘方面的力度和廣度,而要呈現人物性格發展演變歷程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些又是在“類型化”模式內所無法完成的。因此,走出“類型化”模式這一誤區,對于打破“官場小說”創作僵局,將會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二、探究“官場文化”中的人情人性
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演進過程中形成的“官場文化”,自有其不成文但又被廣泛認同的特征,也就是《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一書的作者吳思所歸納的“潛規則”,“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規定,支配著現實生活的運行”。也正是這些“官場小說”中隱性的規則,使得官場中人們的心靈產生了某種變異。穿過貪官與“清官”、腐敗與“反腐”較量的長廊,獨辟蹊徑地將關注的目光投向這些官員矛盾、焦慮的內心世界,揭示那種生存邏輯和生活氛圍對人性的扭曲、情感的裹挾,并由此展現這些在宦海沉浮的官員與社會環境、體制結構間的激烈沖突,以及個人命運中的種種無奈,才是“官場小說”所應探究的終極目標。《駐京辦主任》、《公務員筆記》的作者王曉方就曾講過,“小說家的任務不是講故事,更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表現人的本質,揭示人性中最隱秘的東西。小說家必須有潛入裂開的無比深淵去一探究竟的勇氣”。因此,“官場小說”作家要充分顯現其獨有的洞察世事與人情練達,通過對官場日常生態細致入微的描繪、對內在邏輯的詮釋,進一步將一個個鮮活生動的官員形象樹立起來。遺憾的是,在泥沙俱下、蕪雜不堪的“官場小說”領域,這樣的作品難覓其蹤。
官場并不僅是官僚腐敗、權錢交易、勢力角逐的場所,在表面風平浪靜、內心深處暗藏玄機的神秘領域里,官員們也有許多的無奈。而這正是“官場小說”應有的閃光點。王躍文在其新著《蒼黃》中塑造的主人公既不是大義凜然的領導干部,也不是一腦門子官司的平頭百姓,他就是一個在官場狹縫中頑強生存的縣委辦公室主任。他既是官又是民,既有民身上的尋常情感,又有官身上的規矩。于是,正義與邪惡、良知與貪婪都在這個在無奈、尷尬環境中生存的李濟運身上交織。不合理與非做不可的事情反復地拷問著他的人性,探究著他的官德。一般的“官場小說”都在延續過去柯云路的《新星》、張平的《國家干部》、陸天明的《省委書記》等“改革文學”、“反腐文學”的模式,即地方黑惡勢力欺壓百姓,腐敗官員是他們的保護傘,老百姓最后終于找到一個說理的清官,討回應有的公道。而在《蒼黃》里,王躍文卻告訴我們,官員同樣也是受害者,官員也有優秀的,也有一般的。而迫害他的卻是更大的官員。當迫害他們的官員倒了,他們卻依然沒有翻身。在王躍文的另一部“官場小說”《梅次故事》里依舊沒有宏大的敘事、波瀾壯闊的場景、驚天動地的沖突,有的只是些瑣碎庸常的官場小事,一個個八面玲瓏、在復雜的官場中游刃有余的官員。他們只是在遵循官場潛規則來決定自己的行為。當作家將這種紛繁復雜的官場潛規則,以及行走其間的官員們的游戲、內心深入的情感沖突淋漓盡致地再現時,一個個鮮活生動的官場中人也就躍然紙上。王躍文在其創作談中提及:“這部小說起名《蒼黃》,原意是用《墨子·所染》里的典故。墨子見素絲入了染房,遍染五色,變化反復,面目全非,黯然神傷。‘墨子泣絲’也許并非多愁善感,而是由此感嘆世事無常。蒼黃還有一義,即帶有青的黃色,就是青黃。既不是明快熾烈,也不是灰暗陰冷,而是一種中間色。”作家在《蒼黃》、《梅次故事》、《國畫》等作品中竭力追求的正是這種“渾濁感”。在他的心目中,官場只是他為其人物搭建的一個平臺。這里的大小官人首先是一個人,他們有著常人一樣的人性、人情、人欲。這樣,作品描寫的自然是諳熟官場潛規則,適應官場生態圈、生存環境的一群官員游戲,而不是從一開始就從“類型化”的角度設置人物、矛盾沖突。
近年來,一些成功的“官場小說”代表作往往都是從開始創作時就走出“類型化”這一嚴重制約“官場小說”的發展模式,打破“類型化”大批量生產的統一結構,在氛圍營造和人物刻畫上都力求多面性、復雜性和立體感,既有情節上的沖擊,更有心靈上的碰撞,令人跟隨主人公在一次次無形的博弈后,陷入無限的沉思。由此可見,時常被等同于“惡俗”、“庸俗”的“官場小說”,是能夠在其通俗的結構里彰顯作家的責任與良知,將可讀性與耐讀性有機地融為一體,把流行暢銷元素與文化反思巧妙地統一起來的。讓作品中的主人公既說人話,干人事;又思人慮,發人情。正如《后備干部》的作者李國征所說的那樣:“文學的功能之一是引導、教育和啟迪讀者,跟隨作品從更深層次、更大寬度、更高領域去認識人類自身,認識世界,而不是簡單地靠暴露社會陰暗面來誤導讀者,或者靠展覽原生態的官場丑惡現象來博得廉價的喝彩。”創作出《宣傳部長》、《文化局長》的吳國恩,之所以能將“官場小說”寫得讓人心靈震撼,寫出一個文化局長官場日常生活的同時,更讓我們看到內心深處潛藏著的“局長文化”,同樣也是因為他在創作時就認為“官場小說”這種分類其實毫無意義。由于這種認知上的升華,才使得他和王躍文等作家一樣,真正將自己筆下的官場當成人間畫卷,把官員當凡人來寫。這也就是評論家潘凱雄在談及《宣傳部長》時說的,“這部作品和流行的官場小說之間的明顯區別,那就是多了一番民間情感和真誠”。這“一番民間情感和真誠”,也正是這些年來圖書暢銷市場上持續升溫的“類型化”“官場小說”“所真正缺失”的。在這些批量復制的作品中,往往是有了《領導司機》就有《市長司機》,有了《市長秘書》就有《秘書長》,有了《國稅局長》就有《質監局長》、《工商局長》,無論是人物、情節、細節都是可以大量克隆,每個人物的心態、個性、情感歷程的獨特性歷程顯然無從談起。至于說那種讓廣大讀者心靈顫栗的真誠撞擊就更讓人無法企及。因此,面對“官場小說”這種非理性的熱銷,特別是當它作為一些人的“求職指南”、“晉升寶典”而出現時,以文學形式出現的“官場小說”,就需要在創作時嚴防作家心中藝術標準的隨意跌落,大力拓展和深入開掘其作品的思想精神空間。防止在人為展示官場原生態現象時,使人物的人性空間極大地萎縮。在過度強調時尚好看時,使其人物靈魂不斷矮化。因為對于一部優秀的“官場小說”而言,“可讀性”、“好看”和“人性”、“深刻”之間并不存在尖銳的沖突,選擇“通俗”也不意味著就要放棄“深度”。官場刺激和心靈震撼同樣會在一個官場上發生。從官場入手,但又超越官場去更深入地對社會現狀進行批判與反思,這才是當今“官場小說”亟待提高的方向所在。
當今暢銷不衰的“官場小說”,脫胎于20世紀90年代的“反腐小說”。在《人間正道》、《省委書記》、《天網》、《國家干部》等“反腐小說”的代表作里出現的,一般都是在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中領軍人物與保守勢力、腐敗分子之間的生死較量。作家盡管也是表現官場,但主要還是展示正義與邪惡的交鋒,催人奮進之時也引人深思。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般都不食人間煙火,讓廣大讀者無法找到“身邊人”的感覺。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更渴望看到一些貼近現實生活,切實反映官場生態、官員種種生活狀態的文學作品。于是,一批以展示官場生態圈、帶有一定揭秘性的“官場小說”就出現了。
當王躍文的《國畫》面世后,讀者對這一類型的小說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值。但這十年來“官場小說”的持續熱銷,并不能代表其思想和文學價值的升值。尤其是近年來,在諸多市場營銷手段的推動下,許多“官場小說”作者一味迎合一些讀者窺視官場隱私、尋找為官“寶典”的心態,大量復制出一批交織著明爭暗斗、爾虞我詐、情色暴力、黑惡勢力、秘聞野史等各類流行元素的“類型化”“官場小說”。這不僅無助于人們對官場這一社會日常生存環境的認識,而且還導致廣大讀者對這個看似神奇的世界產生種種曲解和誤讀。
從昔日強化遠離人間冷暖、只注重宏大敘事的“反腐文學”,到后來任自然主義泛濫、陷入重重“類型化”模式的套路,“官場小說”走過了一條從疏遠淡漠讀者到過分迎合讀者的道路。近年來,隨著廣大讀者和批評界對“官場小說”關注和研析的加深,這一領域的作家也開始反思自己的創作,并涌現出像王躍文的《蒼黃》,吳國恩的《宣傳部長》、《文化局長》等一批“官場小說”力作。這些作品走出了過去簡單陳列官場原生態、隨意堆砌官員眾生相的初級階段,開始真正步入生活于官場這個神秘而又特殊環境中的人之心靈世界。這里不僅有濃郁的人情,也有扭曲的人性,令人在激烈的沖突中感受人性的掙扎與無奈,在真實鮮活的故事里體味生命力的勃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