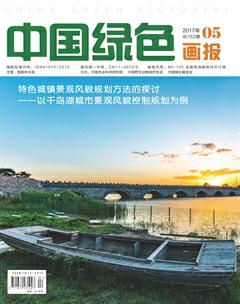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孫慶江
【摘要】:森林病蟲害是威脅森林建設的最主要的災害,會對森林資源產生質和量的嚴重影響,因此需要特別注意森林病蟲害的防治工作。但目前由于經濟和技術等方面的因素影響,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還存在著一定問題,導致其常呈高發趨勢。以佳木斯市松木河林場為例,通過對當地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其產生原因的分析,研究這些問題的解決對策。
【關鍵詞】:森林病蟲害防治;問題;對策
【引言】
黑龍江林區是全國重要的林業生產基地,森林資源豐富,森林面積和蓄積均居全國前列,而且多為天然林;樹木種類百余種,材質優良,利用價值高的30多種,如紅松、云杉、水曲柳等。松木河林場屬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森林覆蓋率65.8%,為人工林和天然次生林,屬生態公益型林場,主要經濟項目為食用菌、堅果、苗木花卉、木耳和五味子等,病蟲害的發生會嚴重影響到松木河林場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以松木河林場為例,通過對森林病蟲害防治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分析,研究病蟲害的防治對策。
1、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存在的問題
1.1常發性病蟲害發生面積逐漸擴大,增加了防治難度
受氣候和環境變化影響,防治技術的限制,以及人造林面積的增加,特別是單純林面積的增加,常發性病蟲害的發生面積一直居高不下。另外對病蟲害防治工作的不重視,退耕還林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加大了防治難度。
1.2病蟲種類增多,加大了損失
很多地方的次要害蟲逐漸上升為主要害蟲,使造成重大危害的病蟲種類不斷增多。大量化學農藥的使用使很多病蟲發生變異或基因突變,產生不少新種類或耐藥性的病蟲,再加上很多外來品種的侵入,使當地的病蟲害種類增多,增加了防治難度。
1.3災害時有發生,損失嚴重
很多過去就威脅程度較重的病蟲害至今未得到較好地控制,例如天牛、鼢鼠等。有的地區甚至年年發生病蟲害,造成嚴重的損失。每年因病蟲害造成大量林木減產,生長速度下降,且淘汰率增高,給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造成嚴重的影響。另外很多病蟲害的潛在威脅依然很大,特別是在以前對病蟲害的防治主要是通過化學藥物實現的情況下,之前得到控制的病蟲害很有可能再次復發,并擴大危害面積,給林木造成毀滅性打擊。
2、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存在的問題原因分析
2.1防治意識不足
眾多的林業企業只看重經濟效益,忽視生態效益,將工作重點放在森林資源的開發上,而忽視了對森林資源的養護和管理,沒有足夠的病蟲害防治意識,導致森林病蟲害多發,且不能及時進行防治,最終造成巨大的經濟和生態損失。
2.2防治技術不足
當前林業部門和企業對森林病蟲害的防治方法主要還是采取的化學藥物防治,雖然在初期有較好的效果,但長久以來,林木對很多化學藥物產生了較高的耐藥性,而且大量化學農藥的使用還會造成農藥污染,影響生態效益。另外還出現了變異的耐藥的病蟲,為了較好地防治就需要效果更好的化學農藥,進而再次產生耐藥的病蟲,形成惡性循環。
2.3防治投入不足
當前企業對森林病蟲害的防治資金的投入較少,使病蟲害在高發年份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防治,延長了病蟲害的發生時間,加重了危害。而且由于缺乏資金,在進行病蟲害防治時不能應用有效病蟲害防治的措施和設備,也就不能及時控制病蟲害的蔓延趨勢,解決病蟲害對森林的影響。
2.4防治機制不足
我國林業部門的管理體系是縱向行政管理體系,對于政策的傳達有著良好的優勢,但是缺少橫向的不同林業部門之間的協調,導致在發生森林病蟲害時因為不能及時協調不同部門之間的配合工作,使病蟲害進一步蔓延,得不到良好的遏制。另外,實現病蟲害防治的先決因素首先是發現病蟲害,而當前對病蟲害的監測和預報工作效果較差,不能及時發現病蟲害的發生和預測發生范圍,從而不能及時采取措施進行防治,加大了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上的損失。
3、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問題的解決對策
針對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對策:
3.1提高病蟲害防治意識,加強宣傳
通過發放宣傳單、開辦森林病蟲害講座、病蟲害防治技術試驗等活動,加強對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重要性的宣傳,提高林業企業和人員的病蟲害防治意識,尤其是對外來物種的防范意識,重視病蟲害的危害。同時也要宣傳相關的法律法規知識,加強社會對森林病蟲害的認識, 從意識上為病蟲害防治工作打好基礎。
3.2完善病蟲害防治體制,加強管理
林啟企業和部門應建立健全完善的防治體制,特別是在病蟲害發生期間,加強不同單位之間的協調合作;設立獨立的病蟲害防治部門,落實責任,明確防治制度,遵守“誰經營,誰防治”的責任制度;加強監督體系的構建,制定嚴格的獎懲制度,督促企業和個人做好防治工作;加強森林的日常管理和養護工作,規范植物檢疫執法行為,嚴格把關林木的引進、檢疫、監管和復檢等工作,防止外來物種的侵入和危險性病蟲害的傳播。
3.3提高防治技術水平, 加強效率
加大對病蟲害防治技術的研究力度,創新防治技術,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推行生物防治(例如以蟲治蟲、以鳥治蟲等)和物理、機械防治(例如燈光誘捕器等)措施,減少投入成本的同時降低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開發新型的靶向性強的生物農藥,在提高防治效率的同時降低耐藥性的發生。加強病蟲害監測和預報技術的應用,學習并引進他人的先進技術,提高監測和預報效果。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類型的病蟲害要針對其特性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目的的提高防治效率。
3.4加大防治資金投入,加強建設
林業企業或部門應該加強對病蟲害防治的投入,積極引進先進的防治技術和設備,以及先進的病蟲害監測和預報設備;增加人力資源的投入,以良好的待遇吸引更多的專業人才從事防治工作;加強森林資源的建設,特別是對人工單純林,要增加植物種類,從本身的生態系統方面加強病蟲害的預防。
結語
森林是國家進行林業建設的重點資源,是影響生態平衡的主要林業產業。病蟲害是影響森林質量的重要災害之一,常對森林資源造成毀滅性打擊,不僅會影響森林資源的質量和林木的生長速度,還會影響林區的經濟和生態效益。我們需要加強對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的重視程度,并結合實際情況,研究當前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存在問題的解決對策和有效進行病蟲害防治工作的措施。
【參考文獻】:
[1]李嘉慶.試論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農業與技術,2014,34(12):59-60.
[2]王巖. 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黑龍江科學,2014,5(1):78.
[3]桑成達,李生彪,白雪芹. 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現代農業科技,2010,(13):197-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