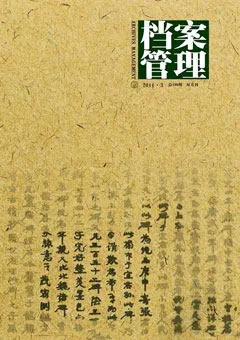試析福柯“知識考古學”對于檔案學的貢獻
??從《詞與物》到《知識考古學》,福柯對于知識的起源、形成和發展進行了譜系學式的清理和分類。在其整理和分類的過程中,他力圖將陳述及其包含的特殊性的放射相對性地區分開來,以求尋繹和概括出陳述的特質和規律,從而獲得陳述對象的確定性、明晰性和完整性,這與檔案學自身的性質,即要求檔案材料保持原始記錄性、客觀真實性、利用價值相吻合。因此,對于檔案學清除由檔案知識波及的指涉條件和外部內容,總結和概括出檔案學自身的規則或規律,對檔案材料作出較為完整準確的鑒定和相對科學的分類,并從某種意義上回歸到材料和陳述本身,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借鑒價值。
1陳述規則與話語空間
在福柯看來,陳述是特定的話語陳述,而話語有其不同的形成規則,陳述因其隸屬于不同的話語形成規則而構成不同的話語。“在最初的某個表達和在數年或數個世紀后多少是準確地重復出來的這個表達的句子之間(考古學)的描述并不去建立任何價值的等級,也不作它們之間的徹底區分,它只試圖建立陳述的規律性。”福柯認為,陳述是對對象的話語敘述,陳述的立場和角度不同,關于對象的身份認證方面就會存在差異。對于某個陳述來說,會存在著許多具體位置,由于不同的個體都可以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占據這些位置,陳述才可以成為具有交叉合并性的被言說的對象。因此,陳述為個體的表達和言說留下了諸多空間,這些空間不僅造成了陳述內容的交叉并合式的復雜化,而且,使得陳述對象的指涉空間和表達視角也趨于寬泛和多樣化。從檔案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空間都是由檔案的話語陳述延伸出來的話語空間,這些空間對于檔案學的作用和價值來說是復雜的,一方面,由于它的連帶和輻射關系而可以被納入檔案的范疇而具有檔案學的利用價值,另一方面,由于個體視角和立場的介入而具有相當多的主觀成分,這些成分,在檔案的使用過程中是應當被剔除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檔案原始記錄的真實性。
福柯認為,無論是利用還是剔除,在一個陳述的周圍,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層空間,第一是側位空間,
即由構成同一群體的另一些陳述所組成的側位空間。在福柯看來,每一陳述都與通過媒介連接起來的異質陳述不可分離,由此構成合作或毗連的空間,在這一空間中活躍著陳述、陳述家族以及陳述話語。側位空間在檔案學中的意義非常重要。例如,某一陳述句是:A是B和C,與之相關的陳述句還有:B是E和F,C包括D和H等領域。A,B、C,E、F,D、H都是陳述家族中的成員,我們可以通過B、C兩個媒介推斷出另一陳述句:A是E、F并包括D、H兩個領域。顯然,A通過B、C兩個媒介開拓出了除B、C之外的兩個空間,這兩個空間正是通過相關媒介而開拓的側位空間。以往的檔案學只關注陳述話語以及話語本身的知識內容,忽視了從語言學和知識考古學的角度去把握和開拓本已存在的新的多樣化的空間。《知識考古學》為檔案學把握陳述話語、陳述對象以及開拓檔案話語的陳述空間,無疑從側位的體位為我們開啟了一條新的思路,即對于檔案材料及其空間的開拓必須掌握相對性和適度原則,唯其如此,才能相對比較準確地尋找和開拓與檔案材料及話語陳述相關的領域和內容,并把陳述和陳述內容以及相關領域區分開來。
第二是對應空間,即與陳述的主體、對象及其觀念相關聯的空間。陳述自身包含著主體的、對象的和概念的功能,由此構成陳述家族中主體、對象和概念的地位或位置的話語秩序。因此,對于詞、句子和命題是偶然的東西,對于陳述卻成為規律。這一規律,對于檔案學關于檔案中語用學規則或規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在利用檔案材料或陳述話語的過程中,可由語用學的對應空間規則或規律來重構主體與對象的話語秩序,并進一步找出其他陳述之間的對應邏輯關系,從檔案材料中通過媒介剝離出陳述對象,使之在語用學規律的指導下同知識內容有一個相對明確的區分。正如德勒茲所言,陳述“不是詞,不是句子,也不是命題,它是當句子的主語、命題的對象、詞的所指被擺進‘人們說’之中,被分配和擴散到語言的深層之中而轉變其性質之時,唯一能夠從這個資料體中表現出來的某些形成”。對應空間在檔案材料中占有相當的分量,找出對應空間中各種關系相互對應、糾結、作用的場,進而找出各種力的聯系之間的對應關系,有助于對陳述以及對應空間作出較為明晰的界定和區分,還原檔案材料(主要是話語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
第三是外在的空間即補充空間,即由制度、事件等的實踐過程組成的非話語形成的空間。補充空間實際上是陳述話語(包括概念與對象)與其產生背景之間的關聯域,陳述背景以其物質性顯示了陳述對象及其秩序,陳述對象及其背景的關聯域是側位空間和對應空間之外的第三重空間,它不僅構成了對前兩重空間的必要補充,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傳統的檔案學乃至語言學在陳述對象和話語內容(知識)區分方面的缺陷乃至先天性不足。例如,以往的檔案學在研究方面對于話語陳述的背景很少聯系起來加以說明,因而,對檔案材料的鑒定缺乏必要的補充空間和陳述背景。不過,迫切需要研究的是外在于物質性的作為未確定點的特殊性的純粹放射,有必要從作為物質性的特殊入手,進而超越物質性,從規律或者宏觀方面來把握由特殊性引申出的放射域,在適度原則下重新考慮檔案材料的遴選、鑒定以及區分和分類工作。
2話語實踐與分類
從實證主義的角度來看,福柯的區分實際上是一種話語形成的實踐。這種實踐既在話語范圍之內,又超越話語的范疇,有能力并不時地表示變化,由原來單一的陳述形成話語實踐的多樣性,把語言學(包括檔案學)的研究從本質主義導向了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同時,并不排除堅持陳述第一和回歸檔案材料客觀性的原則。
福柯認為:“如果語言存在的話,這是因為在同一性和差異性的下面,存在著由連續性、相似性、重復性和自然交織提供的基礎。自從17世紀開端被排斥在知識以外的相似性,始終構成了語言的外部邊緣:這一環狀物,圈住了能被分析、整理和認識的事物的領域。”這一環狀物就是他在《知識考古學》中所說的知識圖式,福柯把知識圖式分成三個絕對獨立的形式,即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圖式、古典時代的知識圖式以及近現代的知識圖式。從一個圖式到另外一個圖式之間存在著斷裂,而每一圖式內部則存在著共時的連續性。福柯要做的正是尋找和發現從一個圖式到另一個圖式之間的斷裂,從而證明不同的圖式之間是如何進行轉換和過渡的。
他認為,在所有的符號中間,語言具有成為連續性的特征:并非由于語言本身屬于年代學,而是因為語言把表象的同時性展示為連續性的聲音,顯示了他從一元走向多元的思想探索和理論創新。在福柯看來,話語是不能還原為語言或言語的,“話語并不只具有意義或真理,而且還具有歷史,有一種并不把它歸結于奇異的生成變化率這樣的特殊的歷史”。話語是歷史地形成的,屬于歷史范疇,這種歷史解構了話語先天性的存在某種本質的神話,從而在無意識中與結構主義形成了對峙的格局。福柯斷定,所謂千篇一律的宏大歷史不過是一種建構,其目的是為了傳達其文化功能,即“記憶、神話、傳播《圣經》和神的儆戒,表達傳統,對當前進行有意識批判,對人類命運進行辨讀,預見未來或允諾一種輪回”。當然,福柯也指出,今天爭議的焦點是針對在尚未完全結構化的范圍里屬于主體的位置和狀態的問題。在結構主義的框架下,主體的位置是預先設定的,結構中的元素是異質同構的,因此,在諸多話語內容和語言現象背后存在著一種預定的本質,因而結構主義并沒有逃出本質主義的窠臼,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會直接將歷史同結構對照,并由此認定主體也保留著某種意義,這種意義被看做是組成的、收集的和統一的活動。但是,只要將時代或歷史形成看做是統一性和差異性的綜合體,看做是具有超連續性的多樣化特征時,主體的統治范圍也就不再有效,結構中設定的本質也就不復存在了。
總之,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理論較好地實現了對傳統歷史學改造的任務,對于現代檔案學作出了有益的貢獻。這對于我們辨析檔案中的話語陳述及其與陳述對象的關系,對于認定結構與功能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交叉與合并關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特別是其對間斷性的強調,成為我們改造傳統檔案學、堅守檔案客觀性的決定性的依據。
(作者單位: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來稿日期:2011-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