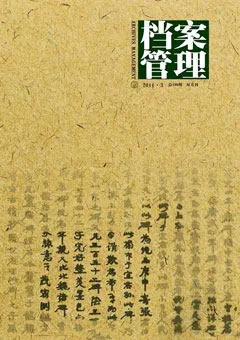一課之恩
2007年,在江蘇但不是蘇州的那個城市,我第一次遇到了蘇州大學的張照余老師。初秋的海港城市已經涼爽得有些冷了,就在一個超大的、有些嘈雜的教室里,張老師的準時到來,讓整個教室突然安靜得好像音樂遭遇停電似的,變得鴉雀無聲。大家的目光開始一致投向了他,他也面帶微笑,由于在座的大部分同學都已經穿上厚外套了,而只有他,著一件雪白的襯衣配深色長褲、腳登黑皮鞋,精神抖擻。后來,我又見過張老師的照片,頭發微微有點長,但那天,我清楚地記得他留著平頭。
就見過一次面,所以,對于我來說,每一個鏡頭都那么珍貴,我甚至希望那時的時間,即使是回憶,也要過得慢一點。
張老師徑直走向了講臺,那講臺對于偌大一個教室來說,顯得很小,張老師坐在那里,開始講課。課大約有兩個小時時間,張老師講的是科技檔案的內容,盡管,那和我近3年的檔案工作不是太掛鉤,但是,卻給了我深深的啟發。現在,再回想起那節課對于我的重要性,不亞于被人給了一把開啟檔案學科的“金鑰匙”。我不是檔案學科畢業的,巧合的是,張老師也不是檔案學專業畢業的,他是畢業于蘇州大學物理系的,這給了我極大的鼓舞與信心。
張老師的講課是系統的,他從回答什么是科學技術開始,圍繞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展開并引出了“科學技術檔案”這個名詞來。從科技檔案的特點到管理,以及具體的組卷方法,他的講述是一環套一環,不斷地引人入勝。我記得,當時的課堂格外安靜,那安靜中仿佛有一股力量正無形地糾結在一起,簡單地說,就是大家聽得都很過癮。現在想想,那時的張老師大概被我們這些“如狼似虎”求知欲極強的學生累壞了,他拼命地講,聽課的人也像要人命似的聽,終于,張老師來了個自我“解救”……
聽過很多教授的課,普通話非常標準的人并不是很多,照余老師的普通話也是“非標”的,因為老師是無錫人,那些“非標”的成分應該就是無錫口音吧。那堂課,我們除了授課內容記得很清楚以外,還對老師的一個發音印象很深刻。他一講到論文的相關內容,就必須提到一個“論”字,而這個“論”字,若是老師含糊其辭說過去,我們也不會覺得什么,有趣的是,老師每次都很認真地去發這個音,結果是“論”“潤”不清,越描越“黑”,“黑”到滿屋子笑聲蕩漾,大家不亦樂乎。兩個小時下來,既緊張,又放松。 ?
下課后,同學們都積極地找老師合影,當然,女同學顯得更積極了一些。我雖然心里很想,但終于沒敢往老師身邊湊。大概我是南方女子的性格,只默默地在一旁記下了老師的聯系方式,并在老師離開的最后時刻走向了他,希望能夠簽個名留作紀念,僅此而已。一課為師,終生為師!那個簽名,讓我永遠記得,檔案學學科是足以讓我攀登的一座高峰!盡管客觀地講,照余老師不是那個登上最高峰的人,學無止境。
涼爽得有些冷的海濱城市啊!給了我最清醒、最深刻的回憶。幾年之后,我都沒有再見到照余老師,由于工作地點的關系,后來,我們和湖大的覃兆劌老師倒是經常有些聯系,這兩個人據說是“哥們兒”。而這一對“哥們兒”又都是我的恩師,還據說,他們有一次談到了那個叫“月光”的檔案人,老師的學生有那么那么多,至此,我已感覺萬分幸福了。
(摘自《檔案界》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