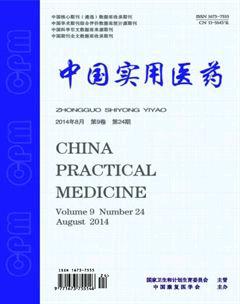肺結核合并咯血的臨床觀察
金京愛
【摘要】 目的 觀察肺結核合并咯血的臨床特點和治療方法。方法 42例肺結核合并咯血患者, 對其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結果 有35例患者得到控制, 6例患者好轉, 1例死亡。結論 在肺結核合并咯血疾病確診后, 需及時接受有效治療, 減少死亡率。
【關鍵詞】 咯血;肺結核;治療方法
在臨床中肺結核合并咯血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疾病, 據調查患病年齡大約在30~60歲之間比較多見, 在肺結核疾病中其發病率約占50%左右, 發病速度較快并且嚴重, 在確診后必須盡快接受治療, 因為隨著血管損傷程度咯血量會不斷增大, 嚴重時會引起休克甚至死亡[1]。針對肺結核合并咯血患者的病情需要細心觀察, 同時應用有效的治療方法并做好護理工作, 在增加生存率的同時減少死亡率。為了研究這種病癥的臨床特點和治療方法, 選取本院于2012年3月~2013年2月收治的42例肺結核合并咯血患者, 對其治療效果和臨床特點進行回顧性分析, 現總結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于2012年3月~2013年2月收治的42例肺結核合并咯血患者, 其中男22例, 女20例, 年齡17~67歲, 平均年齡34.8歲;初次咯血32例, 反復咯血10例 。臨床癥狀包括發熱、乏力、盜汗和缺乏食欲等, 經過各項檢查診斷有6例患者肺結核痰中帶血, 10例肺結核少量帶血, 14例肺結核中量帶血, 12例肺結核大量帶血。所有患者均為繼發性肺結核, 其中包括12例浸潤性肺結核, 15例纖維空洞型肺結核, 14例干酪性肺炎, 1例空洞型肺結核。有3例患者病變涉及1個肺野, 10例患者涉及2個肺野, 29例患者涉及3個肺野。
1. 2 咯血的臨床特征 通常咯血量在24 h內控制在100 ml以內即可表示小量咯血;咯血量在24 h內控制在100~500 ml以內即可表示中等量咯血;咯血量在24 h內為500 ml以上即可表示大咯血, 或者1次咯血超過300 ml, 或出現窒息和休克等情況也列為大咯血范圍。根據引起咯血的因素不同而導致咯血均有不同程度的臨床癥狀, 其中活動性肺結核是最容易患有咯血癥狀的疾病, 發生咯血后會發生結核病中毒癥狀, 同時咽喉異常, 后背疼痛, 通常在1 d后咯血顏色就會發生改變, 不會再呈暗紅色, 咯血量較少的患者痰液易與血混合呈泡沫狀, 胃內容物不會發生混雜。出血量較大的患者臨床癥狀較為嚴重, 由于體內血量大量流失導致患者面色蒼白, 病情的加重也會引起患者精神壓力變大、情緒緊張等癥狀, 嚴重時會出現失血性休克或者窒息而導致死亡。
1. 3 治療方法 在臨床中, 治療肺結核合并咯血的常規治療藥物有利福平、異煙肼、比嗪酰胺、鏈霉素、乙胺丁醇, 用于佐依止血的藥物包括止血敏、垂體后液素、氨基乙酸、安咯血、立止血和淺冬眠療法, 在纖維支氣管鏡下實施外科手術治療、保守止血治療。量較少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應注意減少運動量, 多注意休息;咯血量多的患者則必須臥床休息, 不允許下床活動, 同時使用冰袋敷在患處, 并進行鼻部吸氧, 給患者翻身時注意動作不要太用力, 待咯血得到控制后, 患者仍需臥床休息6 d左右。
2 結果
經過常規的輔助治療后, 咯血得到控制的患者有31例, 有3例患者采用支氣管動脈栓塞治療后咯血得到控制, 有1例患者經手術治療后咯血得到控制, 其中有6例患者咯血減輕, 有1例患者窒息性死亡。
3 討論
肺結核病是肺臟在被結核桿細菌感染后引發的慢性傳染性疾病, 是一種最常見的結核病。肺結核病灶內及周圍的血管受到損傷后將造成出血情況, 從而引發咯血癥狀, 血管損傷程度不同則咯血量也相對不同。咯血占肺結核死亡原因的1/3, 在肺結核患者中咯血癥狀的發生率較高并且也是一種風險最高的并發癥[2]。引起肺結核合并咯血疾病的因素比較多, 主要是氣候的轉變、季節的轉變和咳嗽為較重要因素。在臨床治療中, 咯血在我國是肺結核病最常見的一種并發癥狀。由于肺內炎癥具有特異性和非特異性, 毛細血管壁被細菌毒素刺激, 都會增加毛細血管壁的滲透性, 大量紅細胞滲透至肺泡內, 而肺泡內分泌物會和血液相互混合, 形成血痰。肺結核病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 會引起組織細胞破壞和干酪壞死的情況, 并且血管壁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傷, 結核病灶對周圍血管的直接侵蝕或因病變周圍組織的牽拉使血管破裂, 在臨床中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咯血情況。肺結核患者也容易并發支氣管結核疾病, 從而支氣管會不斷的受到損傷、潰瘍甚至糜爛, 最終導致毛細血管增生、破裂引發咯血。并發結核性及非結核性支氣管擴張易并發感染, 引起管腔充血、水腫, 使管腔狹小, 分泌物易阻塞管腔而導致引流不暢, 加重感染, 促使支氣管擴張的發生發展, 引起反復中等到大量咯血。護理工作的實施對患者的治療意義也非常重要, 主要是對咯血的護理工作, 醫護人員對患者需要做好臨床監測措施并進行預防處理, 比如保持患側臥位保持氣道通暢, 禁食過熱、刺激性食物, 減少刺激引發咳嗽, 準備冰袋放于患處, 隨時準備搶救時需要使用的藥物和設備, 保持靜脈通道暢通, 并保證輸血能充分供應, 以減少咯血窒息及血液流失過多引起失血性休克[3]的發生。
參考文獻
[1] 單淑香, 王鳳蓮, 閏紅玲, 等.肺結核合并咯血的臨床觀察與護理.現代預防醫學, 2007, 34(4):885-886.
[2] 湯春梅, 肖海浩, 張言斌, 等.肺結核患者咯血的臨床分析.現代醫院, 2012, 12(10):27-29.
[3] 陳淑君.臨床護理路徑在肺結核合并大咯血圍手術期中的應用.西部醫學, 2011, 23(8):1594, 1596.
[收稿日期:2014-05-0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