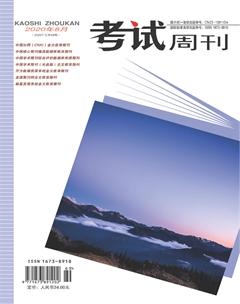新課程下小學語文古詩教學的基本策略探析
摘要:隨著新課程革新工作的全面展開,小學古詩教學也緊跟新課程革新理念,全面推廣小學語文古詩教學。在小學語文古詩教學中,不僅要促進學教師的教學水平提升,還需要找到關于小學古詩教學的基本策略,改善緊張的課堂氣氛,加強師生互動與交流,從而達到培養學生素質全面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教學目標,實現對小學生的情感教育和德育方向的培養。
關鍵詞:小學語文;古詩教學;基本策略
一、 當下小學古詩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難以進入詩的意境
在新課程改革下的小學語文古詩教學,要充分發揮古詩的教學功能,就要對其教學目標進行改良。新課程改革下的語文學科教學的目標要以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為前提,實現學生的個性發展與綜合性發展為目標,并且要求教師從學生的情感態度方面、教學的過程方法以及知識與能力目標三個角度進行教學目標的創建。在以往的教學目標中,偏重于過程與方法,沒有對情感態度和學生的知識與能力方面進行著重培養。在新課程改革的背景下,語文古詩教學需要使學生將朗讀詩文、背誦詩文和品味詩中的意境以及詩人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的理解方面內容正確結合,語文教師需要克服古詩教學的難度,引領學生進入詩文中的意境,從而實現對于學生情感態度與知識能力的培養。
(二)教學內容重心偏移
在普遍的小學語文古詩教學中,針對一首古詩的教學要點有很多,但是一堂課的時間有限學生的精力也有限,所以語文教師需要找到教學中的重點內容進行詳細講解,合理精選總結教學內容可以提升古詩課堂的質量與效果。在實際的語文課堂課堂中,小學語文教師需要對于古詩進行課前準備,需要進行相關的材料和詩文創作背景查閱,將古詩中提到的重點信息和相關內容進行詳細分析,并在教案中體現出本首詩中需要突出強調的教學要點,但是一定要控制在對于教學內容重點的詳細分析與展現,切勿偏移教學內容重心。
(三)教學方法有待調整
在小學語文古詩教學中,教學方法的高低與教學效果的強弱程度成正比。在日常小學語文古詩教學中,教師需要選擇恰當的教學方法讓學生高效地學習古詩。在實際的課堂教學中,普遍小學語文教師容易出現的錯誤是對小學生的教學心態過于急功近利,從而忽略了小學生的年齡特點,并且沒有讓小學生對古詩內容產生學習激動情緒與動力。想要讓小學生有效地學習古詩,語文教師需要耐心進行輔導,并且采用相應的教學措施引導小學生對古詩的學習消除抵觸情緒。從另一個方面講,如果在一堂古詩教學中,小學教師運用過多形式的教學方法,反而會破壞了古詩的原意,使低齡小學生對于課堂內容的領悟出現迷茫的狀態,也降低了古詩教學的效率與質量。
(四)教學評價過于單調
在小學語文古詩教學中,利用正確的教學評價有利于學生對于新知識接受的學習動機養成。正確的教學評價有利于教師和學生正確的自我認識,明確將來的努力方向對以后的教與學起到促進作用。在以往的教學評價中教師是主體,而如今的參加教學評價的參與者不僅是教師,還包括學生和學生家長對課堂內容和授課效果的評價。所以在小學語文教師的教學過程中,要將教學內容發展到全面化具體化,改變以往單調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語文課程成為學生和學生家長,都廣泛接受的教學形式,從而促進教學評價的形成。
二、 小學課堂古詩詞教學的方案探究
(一)吟詠誦讀古詩詞
在小學低段語文課堂中,采用多形式朗讀有效促進學生對于課文內容的全方位理解。在小學課程中的古詩文教學中,采用多種形式的吟詠誦讀,可以讓學生感受到詩文中的準確的節奏和感情,關于古詩的多樣誦讀分為:出聲誦讀法、低聲誦讀法、欣賞誦讀法等不同的應用誦讀方式。在出聲誦讀法中,要求學生將古詩的韻律節奏帶有感情地朗讀出來,低聲誦讀法則要求學生放慢閱讀速度,講古詩中音律回環曲折之美誦讀出來,欣賞誦讀法,要求學生在誦讀古詩的過程中進行詩文欣賞。
(二)啟發解讀古詩詞
有關于學生的學習態度方面,學習的形象及個性等因素都會影響古詩教學的結果。一部分學生對于古詩產生抵觸情緒,所以語文教師要啟發學生對于古詩的喜愛與欣賞。詳細來說,主要在于學生的思維與認知能力方面。在小學語文課程中,學生的年齡較低對于古詩意象層面的理解欠缺,因為想象力和抽象思維的有機結合還不夠完美,所以作為小學教師,要啟發學生解讀古詩中的優美意境,培養對于古詩的喜愛之情與欣賞能力,教師要抓住學生不同階段的思維特點巧妙地設置啟發,利用對古詩的詳細分析與講解,培養學生認知方面的能力,從而達到古詩教學的相應目標。
(三)品詞析句學會審美
每一首古詩都有其含蓄的思想感情,引導學生了解古詩中的優美意象以及美妙的音律之美。要求小學語文老師,按照相應的課堂步驟,關于學生的信息方面的處理能力以及問題的分析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進行重點培養。在古詩文教學中,小學教師要注意幫助低齡年級學生積累鮮明生動的古詩意象素材,對低年級小學生在今后的小學古詩學習中有一定的幫助。例如在課后要求學生對于描寫景物的古詩進行搜集,還可以倡導學生利用圖畫的形式展現出古詩內容的景物以及人物狀態。這樣有效促進小學生品詞析句,并且通過古詩的學習提高了審美能力。并且可以鼓勵學生跳出古詩固有的思維定式,讓學生圍繞詩意展開自行創作,教師可以借助古詩的主題思想來設計相關的寫作內容,也可以進行其中相關指定意向的主題限定,讓學生充分發揮想象力進行詩畫創作。
三、 利用古詩教學提升學生審美能力
(一)啟發學生初探古詩之美
審美教育作為新課程改革背景下,提倡的教學創新類型的觀念之一,在小學語文的古詩類教學中,提升小學生的審美水平,提高小學生感受到美、鑒賞出美、創造出美的能力水平。在小學教材的古詩中,大多數古詩具有語言精練、字句平仄押韻、音律之美。所以在實際的古詩教學中,教師可以采用講解古詩相關背景的方法,作為課堂的導入部分,讓學生對所要學習古詩文的創作背景、詩人經歷簡介、詩中相關意象的等進行初步了解。小學語文教師在古詩教學中,可以向學生講解古詩的創作背景,從而引導學生熟悉古詩大意,然后深入地感受到古詩中的玄妙、唯美之處以及詩人利用美妙的意境和景物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
(二)詳細講解古詩基礎內容
在實際的小學語文課程中,教師需要講解與古詩相關的景象來輔助學生理解古詩,學生掌握古詩文中相關的想象之美,方可對詩中的中心思想進行深入了解。例如在小學課本中有一篇名為《江畔獨步尋花》的古詩鑒賞,這首古詩是唐代著名詩人杜甫所寫,詩文中黃四娘家在四川成都,她家的巷子開滿了五光十色的鮮花,千萬朵碩大的鮮花把枝條都壓彎了,花叢中不計其數只蝴蝶在翩翩起舞、嬉鬧許久不愿離開。這樣美麗自在的自然景象呈現在小學生面前有利于學生對古詩的鑒賞與學習。
(三)講解古詩常識促進理解
在小學語文古詩課程中,教師除了需要對詩人所生活的背景講解還要對文中的常識進行解說,這樣有利于學生對于古詩內容的深入了解和古詩主題思想的理解。例如在小學課本中一篇名為《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教師可以向學生介紹農歷九月初九是我國傳統節日重陽節,這一天在外游學的游子會回到家鄉,與親人們一起插茱萸,登高、飲酒來慶祝節日。在對于古詩的創作背景進行詳細講解之后,有利于學生對于重陽節的認識以及關于重陽節習俗的了解,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學生對于古詩內容和主題的深入探究與理解。
四、 利用古詩教學滲透德育方面的指導
(一)古詩教學中滲透德育
古詩是華夏傳統優良文化的一個縮影,其中運用精短的文字篇幅烘托出詩人偉大的家國情懷,用文字勾畫出一幅幅美好的畫卷,在實際小學語文課程中,教師利用古詩詞滲透德育方向的教育。例如在小學古詩《游子吟》當中是對親切誠摯的母愛進行歌頌,關于作者孟郊的創作背景,教師可以進行詳細介紹,作者孟郊一生顛沛流離,直到年過半百歲才得到一個卑微的官職,這首詩是在他做官之后創作而成。這首詩藝術地再現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又偉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來獲得了無數讀者強烈共識。
(二)小學德育方面的指導的重要性
德育方面的指導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不可忽略教育方向,尤其對于小學生階段的德育方面的指導至關重要。小學階段作為人一生思想最單純、潔白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對小學生進行德育方面的指導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處于啟蒙階段的小學生的心智還未發育成熟,對世界的認知還是一個模糊的狀態,任何因素都可能改變他們的道德觀念對今后的人生產生影響。在塑造小學生品行的關鍵時刻,德育方面的指導千萬不可忽視,小學教師應該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道德觀,這對于他們來說可以受用一生。所以在小學階段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引導懵懂無知的小學生創建起正確的道德意識,以及道德品質極為重要。
(三)利用古詩教學發揚傳統文化
優秀的傳統文化既是民族振興的精神方面的動力,又是建設先進文化的重要基礎。在經濟全球化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并結合時代特點加以創新。在古詩教學中發揚傳統文化是語文課程的育人功能,在小學語文課程中,發揚和培養民族精神使學生受到優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熱愛祖國和華夏文明,獻身人類進步事業的精神品格,形成良好的情感與奮斗向上的人生態度。在新課程改革的背景下,所以要求學生學習中國古代優秀作品,體會其中蘊含的華夏民族精神,形成一定的傳統文化底蘊。
五、 結語
小學語文古詩教學應從知識與能力方向以及情感與態度和教學與方法三個角度來創建教學的目標。古詩作為華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也能提升學生的文化素養還能提升學生的審美能力水平。因此從各個角度提升學生的綜合能力與素質尤為重要。通過各種不同角度和方向的教學,從而達到新課程改革下,對于小學生古詩教學的基礎要求與相應教學方面的目的。
參考文獻:
[1]冉鳳.新課程背景下小學語文經典古詩文教學策略探析[J].文淵:小學版,2019(1):439.
[2]張雪云.新課程改革背景下的小學語文古詩教學策略探討[J].讀天下,2019(1):1.
[3]關淑玲.新課改背景下小學語文古詩詞教學策略探析[J].課程教育研究,2017(24):235,279.
作者簡介:
張文娟,山東省日照市,日照市第三實驗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