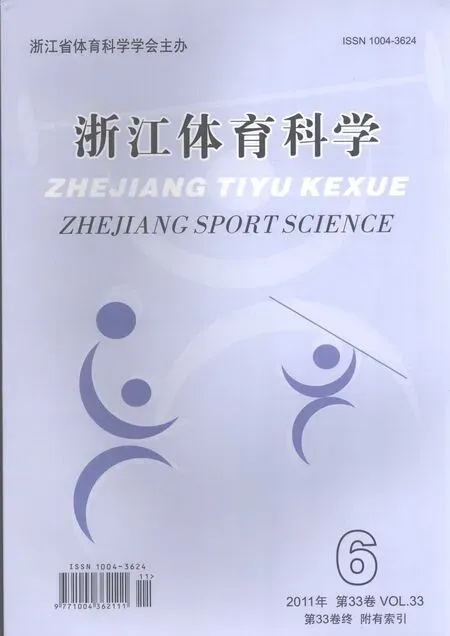我國大眾體育文化的發展現狀研究
桑振洲,王少春
(寧波大學體育學院,浙江寧波315211)
0 前 言
體育作為現代人必不可少的一種生活方式,是其全面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在物質生活得到不斷滿足的同時,開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而體育所具有的功能恰好迎合了人類在這方面的需求,所以體育順理成章成了現代人精神生活的首選項目。建國以來我國社會趨于穩定,人民逐漸擺脫外患的陰影,開始加快發展生產、提升國力的步伐。在此過程中,體質的重要性逐漸凸顯出來,以致黨和領導高度重視大眾體育事業的開展。隨著“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陽光體育運動”、“全民健身”等體育思想提出,大眾體育運動的觀念深入人心,人民參與大眾體育活動的積極性得到極大的提高。大眾體育活動已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及其發展水平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標志之一。但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其大眾體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呈現出“W”型(即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兩次受挫時期)的發展模式。“前車之鑒 后車之師”為了更好地建設具有我國特色的大眾體育文化事業,對其發展現狀進行分析已極為重要。筆者查閱大量有關研究大眾體育文化發展現狀的資料,大都集中于物質層面,對其觀念層面的研究還是一個空白。本文立足于觀念層面來研究我國大眾體育文化的發展現狀。
1 大眾體育
大眾體育活動作為體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今天大部分學者將體育分為三個部分即“學校體育”、“競技體育”和“大眾體育”。在我國群眾體育和大眾體育屬于同一范疇,群眾體育起始于19世紀中期,大約100年后開始形成,20世紀60年代后以其業余性和廣泛性的特點區別于競技體育并在發達國家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文化運動。群眾體育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指“在社會成員余暇時間中廣泛開展的,以身體運動作為主要手段,以提高健康水平,進行娛樂消遣為主要目的,在身心健全發展的階梯上不斷超越自我,促進社會物質、精神文明進步的社會實踐[1]。”在國外稱為“S p o r t F o r A l l或S p o r t F o r E v e r y b o d y”——也就是所有人的運動或人人的運動。狹義是指:“除在學校和武裝力量中開展的體育之外,在社會一切其他行業或活動領域人們的余暇時間中開展的體育[1]。”所以筆者在這里談的“大眾體育”是狹義的群眾體育。
2 大眾體育文化
大眾體育文化是體育文化的下位概念。根據任蓮香[2]的觀點:體育文化實際上有兩個上位概念,一個是“體育”,一個是“文化”。從這里可以看出要研究體育文化就要先從“體育”和“文化”這兩個上位概念起始,大眾體育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
有關文化概念界定方面的論文可謂非常之多。19世紀人類學家愛德華·伯內特·泰勒第一次十分明確和全面地對文化下了定義,之后文化的定義層出不窮。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一書中把文化定義:“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 、法律、習慣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習性的復合體[3]”。這是第一個也是最經典的文化定義之一,后來的學者雖依據各自不同的需要賦予文化不同的內涵,但都受其影響。如我國學者梁漱溟從民族學的視角把文化定義為:“所謂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總括起來,包括精神生活、社會生活和物質生活三個方面[4]。”雖然學者們對文化的認識有差異,但人類在生活過程中創造了文化,這是現在被廣泛認同的觀點。按照約翰·赫伊津哈德[5]在其《游戲的人》一書中的觀點“我們可以說游戲是我們生活的基本范疇之一”。他把游戲作為生活的一部分,這是赫伊津哈在這一領域最重要的貢獻。從他的觀點中不難看出,體育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人類創造的各種文化系統中必然也包括體育文化。
體育的定義和文化的相似,對其的界定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學者們根據各自研究的需要來對其進行界定。如姚頌平界定體育為:“體育是社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特征是以合理的身體活動為基本手段,針對社會和個人生活需要,優化身體狀況和身體發育,促進身心發展的活動[6]。”曹湘君學者將其界定為:“體育(廣義的,亦稱體育運動)是指以身體練習為基本手段,以增強體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豐富社會文化生活和促進精神文明為目的(的)一種有意識、有組織的社會活動[7]。”雖然他們對其的界定各異,但是他們對于體育是一種文化現象這一點他們具有共識。
由于“體育”和“文化”這兩個上位概念尚未明確,那么其下位概念“體育文化”也難以統一。但是這不會影響學術家們對其的研究。學者們大多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對體育文化進行界定。如盧元鎮[8]學者認為:“體育文化是關于人類體育運動的物質、制度、精神文化的總和,包括體育認識、體育情感、體育價值、體育理想、體育道德、體育制度和體育物質條件等。”按照體育的分類我們可以把體育文化分為競技體育文化、學校體育文化和大眾體育文化。所以對大眾體育文化的研究也要從物質、制度和精神三方面著手。目前國內對大眾體育文化現狀研究的視角多集中于物質層面并形成了相應的體系,而精神層面的研究相對甚少。本研究從觀念的層面來分析我國大眾體育文化的發展現狀。
3 大眾體育文化發展現狀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離不開其所依附的社會歷史環境,大眾體育文化的發展也不例外。為了便于研究,我國學者崔樂泉、楊向東將其劃分為六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體育思想(1949-1956年);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體育思想(1957-1965年);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體育思想(1966-1976年);歷史性轉變時期的體育思想(1977-1982年);改革開放時期的體育思想(1983-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與建設時期的體育思想(1993年-)[9]。”依據我國的特殊國情,本文將其發展軌跡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3.1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大眾體育文化(1949-1957年)
1949年新中國成立,結束了長期的社會動蕩,全國上下在黨的領導下進入國民經濟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當時我國人民經歷了多年戰爭的迫害,人民體質水平不高;國外西方列強對我國虎視眈眈,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進行嚴密的封鎖,企圖使新中國不攻自破。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形勢下,黨和政府深刻認識到:改善民族體質,使之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突破列強的封鎖是當時的首要任務。1949年10月,朱德在全國體育總局籌備會上的發言中指出:“過去的體育,是和廣大人民群眾脫離的。現在我們的體育事業,一定要為人民服務,要為國防和國民健康的利益服務。”馮文彬前輩指出:“……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和人民的國防而發展體育[10]。”與之相似毛澤東同志于1952年發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號召。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大眾體育事業的發展,為大眾體育事業創造了有利的發展條件。
大眾體育文化的發展受到黨和領導人的高度重視。“體育為人民服務、為國防建設服務。”是當時體育的主導思想。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借鑒“老大哥”的經驗,建立了一系列的大眾體育制度。如:1951年由國家機關單位發出《關于推行廣播體操的通知》,同年又頒布了《準備勞動與保衛祖國體育制度》,1955年正式在全國推行。“在借鑒蘇聯經驗的基礎上,一系列有關群眾體育制度開始出現,如勞衛制、廣播操和工間操制度、職工體育制度、基層體協制、產業體協制度等[1]。”這些制度的實施主要是為了達到: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1953年4月27日,賀龍在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上也發出了同樣的號召。廣大人民群眾積極響應,以大比武、大會操等為主要形式,提高身體素質,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達到保家衛國的目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一時期我國大眾體育達到了預期的目標。
建國之前,由于長期的社會動蕩,廣大人民流離失所,受教育水平較低。所以在建國初期,人民群眾無法形成自己的體育觀念。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安定生活,他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開展多種多樣的體育活動。最終形成以國家指導思想為主的大眾體育觀念:增強體質、發展生產、服務于經濟和國防建設的“保家衛國”思想。
3.2第一次挫折時期的大眾體育文化(1958-1965年)
“大躍進”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標志著大躍進運動的正式開始。從1960-1965年的大眾體育文化是在解決大躍進運動的遺留問題,所以本研究將其劃分為同一個階段。
在這一階段,大眾體育文化的發展主要受 “體育大躍進”、“八字”方針、“小型多樣”的大眾體育等思想影響。在左傾思想的大環境下,1958年2-3月國家體委制定的《體育運動十年發展綱要》沒有得到落實,弄虛作假和形式主義隨之而來,出現了“白天千軍萬馬,晚上燈籠火把”、“體操城”和“勞衛縣”等現象,這種沒有實質意義的大眾體育活動極大地挫傷了人民群眾參加鍛煉的積極性。另外在“一切為了體育大躍進”的口號下,形式主義愈演愈烈,影響了經濟和國防建設。這種現象直到1960年“八字”(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提出及運用到大眾體育中去才有所好轉。1961年2月10日,國家體委下發了《關于1961年體育工作意見》對大眾體育活動做了特別的關注。《意見》客觀地審視了當時大眾體育現狀,指出按照“八字”方針制定大眾體育工作。“體育戰線在1961年貫徹‘八字’方針是比較迅速和及時的,尤其是群眾體育工作,很快就擺脫了‘繼續躍進’的‘左’傾思想,使1961年的群眾體育的調整工作,收到了明顯的成效。”“1963年以后,體委加強了對群眾體育的行政性領導,‘業余、自愿、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小型多樣’成為開展群眾體育的指導思想[9]。”1962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毛主席在講話中再次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在當時對大眾體育文化的發展是利大于弊,但是也導致了大眾體育發展的第二次受挫。
這一時期,人民對大眾體育活動已有了自己的認識,但是迫于種種壓力在本階段前期新的觀念尚未形成。隨著“八字”方針的提出及《意見》的出臺,體育運動的實用性提高,人民的體育觀念有了新的變化。但主要還是以“保家衛國”為主,不同的是這一時期“保家衛國”的內涵與上一時期有所不同,將其對象轉移到國內。
3.3 第二次挫折時期的大體育文化(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文革)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體育受到了毀滅性打擊。但在部分中央領導的關注下還取得了微弱的發展。“文革”是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這場所謂“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運動被部分不法分子所利用進而發展為禍國殃民的大災難,在“紅衛兵時期”到達了頂峰。
在這場政治文化運動中,體育也遭受了嚴重的破壞。文革一開始,體育部門的大批領導干部被揪斗,體育制度被視為“修正主義貨色”而遭到廢止。致使大眾體育事業的開展處于停滯狀態。“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我國群眾體育事業遭受到了一場空前的浩劫,體育戰線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和破壞,大量體育設施荒廢被搗毀,群眾體育活動的組織管理體系已消失,自發、自娛的群眾活動被迫停止。職工體育協會等體育組織網絡和業余訓練隊被解散,農村開展的民間傳統體育活動也被‘破四舊’的狂潮淹沒農村體育開展流于形式,妨礙了農業生產[11]。”
這一時期體育最大的特點就是其突出政治的特色,對其施加政治干預,給大眾體育活動上綱上線,突出其的政治功能。在這種體育路線的指引下,大眾體育活動再次出現形式化,其嚴重程度與“大躍進“時期有過之而不及。如:“如出于政治需要,停工停產,大搞‘千人操’、‘萬人橫渡’等形式主義活動;競賽活動中繁文縟節的政治儀式。在農村,組織體育運動隊為‘學習大寨’的硬指標,成立體育領導機構,突擊修建球場,購買體育器材,成立體育表演隊,有生產隊補貼公分。群眾體育的‘政治功能’也發揮到了極致,‘極左’思想以實用主義的態度,根據自己的需要給群眾體育貼上各種政治標簽,忽而將群眾體育作為政治運動,為路線斗爭服務;忽而將群眾體育作為政治指標上綱上線,為‘抓革命,促生產’服務;忽而以群眾體育為政治櫥窗,虛浮鋪陳,粉飾太平[1]。”然而在這種給體育上綱上線、大搞形式化的同時恰恰刺激和促進了大眾體育文化物質層面的發展。特別是1970年社會的政治形勢相對穩定,1971年“乒乓外交“為契機,大眾體育文化事業開始復蘇。
人民對體育的認識也開始有微妙的變化:“保家衛國、為生產服務、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等觀念雖還占據主要地位,但開始有弱化的跡象,新的觀念開始出現。如:人們參加大眾體育活動的目的已經向個人的需要轉變,其交流、娛樂等作用開始凸顯。
3.4 新時期的大眾體育文化(1977年-)
1976年以“四人幫”集團被粉碎為標志,十年“文革”結束。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我黨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大會,在這次會議中黨提出了:“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等號召,從此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物質文化程度的提高,不斷完善著大眾體育發展的基本條件并呈現出法制化和規范化的趨勢。是大眾體育事業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我國體育觀念的轉型時期。
粉碎“四人幫”后,全國人民走出陰霾,積極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體育工作也迎來了春天,大批遭受迫害的領導干部、體育工作者在“撥亂反正”運動中被平反,體育組織、制度得以恢復,體育工作納入正軌。國家體委在1971年1月,下發了《做好縣的體育工作的意見》;1982年8月27日,頒布了《國家體育鍛煉標準》;1993年12月4日,頒布了《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制度》;1995年6月20日,國務院頒布了《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并制定了《中國成年人體質監測制度》和《中華體育健身方法》;同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頒布實施。2002年7月22日,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時期體育工作的意見》。“這些措施正在極大地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在諸如群體活動內容的完善與創新、體育事業基本要素的結構優化與功能改善、體育知識的普及、體育意識的培養及我國體育理論的發展等方面產生積極影響[1]。”使我國大眾健身更加科學化、法制化。
隨著改革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大眾體育活動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雙休日”制度的實施更加刺激了人們參與體育運動的熱情。使大眾體育活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形勢。國家體育總局號召開展:“億萬職工健身活動”、“全民健身與奧運同行”和“體育三下鄉”等活動,都為大眾體育活動的開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2009年,國務院批準自2009年起,每年8月8日為“全民健身日”,這無疑再次推動大眾體育活動的普及和人民參與大眾體育活動熱情的提高。現階段我國大眾體育活動的開展呈現出新的趨勢:從原來的“三化促騰飛”(以革命化靈魂,以社會化和科學化為兩翼,實現體育騰飛)的體育戰略思想向“各類體育協調發展”以及“六化六轉變”(“六化”:生活化、普及化、社會化、科學化、產業化和法制化;“六轉變”:個人體育活動費用從福利型向消費型轉變、社會體育活動從體育部門一家辦向大家辦轉變、體育組織形式從行政型向社會型轉變、體育活動由經驗型向科學型轉變、體育設施由事業型向經營型轉變和體育“人治”向“法治”轉變)的方向發展。
這一時期人們的體育觀念發生了前所未有轉變。從建國初期所形成的:“保家衛國”、“開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等等體育觀念向“促進人自身的發展,健身、休閑、娛樂和社會交往”等等方向轉變。現階段人民的體育觀念整體上從“國家利益向多元化利益”方向轉變,從“健身型向娛樂、休閑型”轉變。人們在參與大眾體育活動的過程中以主體的滿足為主,很少甚至沒有人在提“鍛煉身體 保衛國家”等口號。這是現階段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會安定的必然表現。
4 結 語
我國大眾體育文化事業在觀念層面的發展主要受黨和政府指導思想的影響,這一現象在建國初期表現的最為明顯。黨和政府依據國家建設的需要提出一系列的指導思想,廣大人民群眾為了保衛來之不易的安定環境積極響應,并形成與之相適應的大眾體育觀念。在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社會的發展相對來說比較模式化,人民的大眾體育觀念的發展也相對比較緩慢;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經濟制度由原來的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時期,人民的大眾體育觀念也進入了快速轉變的新時期。現階段大眾體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基本上是按“六化六轉變”的形式進行,但是如何更好地實施“六化六轉變”以及拓寬大眾體育活動的發展路線,現階段學術界對其的研究還沒有形成體系。學者們對大眾體育文化的研究多重視物質層面,對其發展路徑的研究還不完善。大眾體育文化發展程度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體現,為了進一步促進大眾體育文化更好、更快地發展,對大眾體育文化發展路徑的進一步研究勢在必行。但是目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群眾的體育意識、法規制度、科學化等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人們“花錢買健康”的觀念還不強,大眾體育活動的開展得不到科學的指導以及制度化的保障等等極大地影響了大眾體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從觀念上引導人民參加大眾體育活動以及制度上保駕護航以促進其快速的發展,已迫在眉睫。隨著社會的進步,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眾體育文化事業的當務之急是立足于制度和觀念的層面來探討大眾體育文化的發展路徑,確立我國特色的大眾體育文化發展方向。
[1]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課題組.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與研究[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98:10,20,24.
[2]任連香.體育文化論綱[J].體育文化導刊,2003(3):30.
[3]泰勒.原始文化[M].連樹聲,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1.
[4]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梁漱溟全集第一卷,1989:339.
[5]約翰·赫伊津哈德.游戲的人[M].北京:中國美術出版社,1996.
[6]姚頌平.體育運動概論[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6:5.
[7]曹湘君.體育概論[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85.
[8]盧元鎮.中國體育社會學[M].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98:188.
[9]崔樂泉,楊向東.中國體育思想史[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4;84;98.
[10]馮文彬.新民主主義的國民體育[J].新體育,1950(1).
[11]國家體育總局.拼搏歷程 輝煌成就——新中國體育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