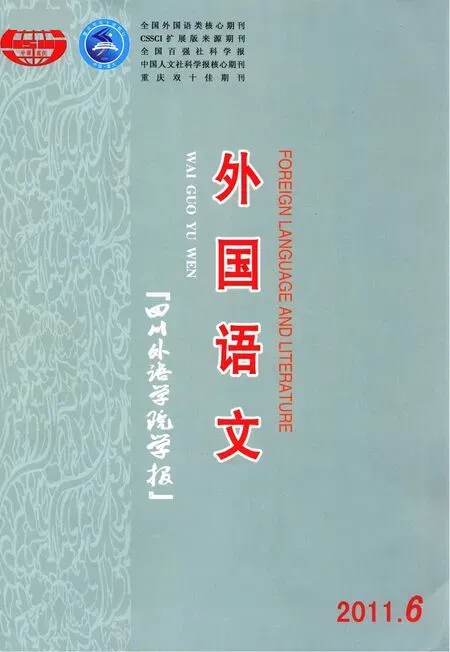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強暴幻想》中的雙性同體意識
史菊鴻
(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一、“強暴幻想”命題的政治意蘊
女性的生存狀態、身體意義以及男女兩性關系等問題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作品長期以來所關注的主題之一。她的大部分長篇小說都以女性為主角,一些短篇直接面對一些很敏感的女性話題,其中一篇短篇小說就直接命名為《女體》。在1975年發表的《多倫多生活》短篇小說集之《強暴幻想》中,阿特伍德以戲謔的文體表達了自己對話語特權、理想的女性生存方式以及女性主義理論等問題的嚴肅思考。
小說的敘事起源于一本流行雜志上的一個話題:“所有女人都有強暴幻想”。小說創作于20世紀70年代,當時激進女性主義風卷歐美,女性的身體和性欲這類問題由曾經的禁忌變為一個勁爆話題。前衛的現代女性不僅可以毫無忌諱地談論自己的生理特征,甚至以自己的身體和性欲為自豪,隨之出現了“我欲故我在”這樣把性欲意識等同于女性主體性的激進口號。流行雜志的普通女性讀者看到類似的所謂心理測試問題時,很少會去質疑這類問題的價值,卻首先默認這個命題,然后從自己的記憶或者想像中去尋找能夠證實這個命題的例證。把“女性具有強暴幻想”這類話題的流行跟激進女性主義之間畫等號肯定是錯誤的,但是女性積極回答這類問題的熱情無疑跟激進女性主義的興起有直接的關系。然而女性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應該首先思考的是:這個話題有價值嗎?女性真的有強暴幻想嗎?這個話題有無政治意蘊?克里斯蒂娃以及福柯的理論或許有助于回答這些問題。
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的時間》一文中將20世紀女性主義發展史從政治歷史角度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指從女性主義運動的最初發端到1968年,該階段的基本主題是女性要求平等地進入拉康在心理分析中提出的代表著權威和秩序的“象征界”,要求平等的社會與政治權利。對于這個階段女性主義運動的成就,克里斯蒂娃評價說這場運動在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卻沒有讓現存的權力結構受到任何震動。克里斯蒂娃把1968年之后的第二代女性主義運動跟拉康心理學所界定的“符號界”相聯系,這個階段女性以差異的名義拒絕進入“象征界”,提倡返回到母性“符號界”。這個階段也被稱作激進女性主義階段,其代表人物當屬女性主義學者兼作家西蘇,她提倡女性停留在前俄狄浦斯的母性認同階段,同時也提出了“女性寫作”的主張。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之下,欲望表達以及“身體書寫”成了一種時尚[1]。克里斯蒂娃對于這種思想有所否定,她認為這種“女性夢想”永遠是一種烏托邦,最終只能演變成為另一種宗教,使女性“重新加入到那些滿懷神秘的精神期望的邊緣群體”[2]。美國女性主義學者托麗·莫伊對這個階段也提出了質疑,她認為這種做法“沒有意識到用性別界定身份的形而上本質,存在演變成為另一種性別主義的風險”[3]。有鑒于此,克里斯蒂娃在《關于中國女性》一文中提倡摒棄闖入“象征界”和退回“符號界”的這兩種極端模式,而建構一種“這兩種術語辯證交替”的模式[4]156,即拒絕形而上學的男女兩分法,建構一種兩性和睦相處的模式。按照克里斯蒂娃的這種解釋,女性如果滿足于恣意展示自己的生理特征,拒絕進入象征社會等級秩序的“象征界”,她們只能永遠處于邊緣地位。據此判斷,女性可以在辦公室大談其“強暴欲望”的現象并不能說明女性已經獲取自由。
福柯在《性史》一書中對這種社會現象也提出了冷靜的警告,他認為這種貌似進步的語言其實是壓制權利的一種結果或者表現。他提醒大家不要樂觀地以為20世紀的人們已經擺脫了過去的權利壓迫機制。他指出,我們今天因為能夠公開談論性欲這個曾經被視為禁忌的話題而心存感激,“能夠公開談論這個話題的這一事實給人一種故意僭越的感覺,我們感到我們是在挑戰既定的權威,我們的語調表明我們是在顛覆”[5]6。但實際上,這種因為感覺自己擁有言論自由而產生的感激之情恰好是“一個生產‘性話語’的機器”的控制結果。這個“機器”存在于一個由各種話語和行為組成的網絡之中,從宗教、法律、醫學、心理學、犯罪學以及教育學等各個傳統或者新型學科的繁榮發展中獲取權威。相應地,“性從原來飽受束縛的隱蔽處被趕出來了,開始有了話語生命,……任何一個其他類型的社會從來沒有在這么短暫的時間內出現過如此大量的有關性的話語。”福柯進一步指出有關性行為的“知識話語”主要聚焦于那些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而必須加以控制的特殊人群身上,孩子、工人階級以及女性。這種話語的細查使人們認為“性被當作一個關乎真理的問題”[5]60-61,于是整個西方社會變得格外懺悔。而這種內化了的審視和談論“性問題”的沖動被我們誤以為我們獲得了談論“真理”的自由。
福柯用這種把一種話語跟特定歷史環境下受操控的某種行為相聯系的做法提醒我們,權利的控制和規訓意志其實悄悄運作于那些被我們同進步思想聯系在一起的話語當中。按照福柯的這種解釋,我們可以做出如下推論:流行雜志上熱議的“每個女人都有強暴幻想”這樣的話語背后也隱含著一種權利“陰謀”,其隱含的思想可以包含:(1)女性是淫蕩的;(2)女性是被動的;(3)女性是享受性虐待的。究其本質而言,“女性具有強暴幻想”這個命題實際上還是弗洛伊德理論“男根嫉妒”意識的另外一種含蓄或者略顯文明的表達方式而已。這個話題產生的原因依然是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分析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來解釋女人,而是以他自己為主相對而論女人的。”[6]女性真有被強暴的幻想嗎?這個命題的提出恐怕只是因為男人有征服女性的強暴欲望而已,而女性如果不假思索地去為這個問題幻想一個答案,無疑便是一種“共謀”。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阿特伍德在《強暴幻想》中以貌似調侃的方式對兩性關系進行了另一種方式的探索。
二、文本內容分析
阿特伍德很少用控訴式的敘事語言,她的風格基本上是戲謔又戲謔,幽默又幽默。《強暴幻想》不無例外,小說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敘事,敘事者“我”一開始就用阿氏風格委婉地表達了對于充斥在各種空間的某個話題的反感態度,但她并沒有明確指出這個話題,只是稱其為“它”:“雜志上談論它的方式讓人以為這又是什么新發明,而且非常神奇,好像癌癥疫苗一樣。他們把它赫然置于雜志封面。正文部分安排了許多相關問卷,而原先經常出現的問題是你是否是個好妻子,或者你的身體構造究竟是‘內形’還是‘外形’。……上班的時候,大家都得談論這個話題,因為無論你翻開哪本雜志,它就在那里,直勾勾地盯著你的兩眼。他們在電視上也開始安排這玩意兒了。”①本文所引用的譯文部分參照發表于《外國文學》2006年第4期的譯文,部分為筆者所譯。[7]9在這樣的氛圍中,敘事者讓我們看到了某一個單位的午間休息室里的五位女性,其中桑德拉、達琳、格麗塔以及“我”——艾思黛兒邊打橋牌邊吃飯,而克莉絲在看雜志,她合上雜志,問大家:“怎么樣,各位,你們有強暴幻想嗎?”至此,我們知道“它”是指“強暴”。五位女性對此問題的反應各有不同,達琳的回答是徹底否定,格麗塔和克莉絲坦誠自己有這種幻想。并且先后講述了自己的“幻想”。“我”一直在調侃,但是也講了一個自己的幻想。不過并不是幻想被強暴,而是幻想自己如何在危險時刻使用檸檬水得以擺脫強暴危險。
午間休息結束之后,愛思考的“我”又設計了五個“強暴幻想”。敘事的主調還是阿特伍德一貫的幽默詼諧,但是透過這蠱惑的主調,我們能聽見一個更加嚴肅的聲音,表達著自己對話語特權、女性主義理論,以及理想的女性生存方式等問題的困惑與思考。首先,我們能夠明確感覺到的是作者對以媒體為代表的主流話語的質疑。“強暴”并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在這樣赤裸裸的兩性對抗中,女性由于身體原因,無疑處于極端弱勢的地位,結局恐怕只能是身體和心理的極大創傷。媒體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者,不去探索造成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相反,他們一方面宣傳“女性具有強暴幻想”,另一方面卻又自相矛盾地給女性提供一些所謂的“自衛絕招”,比如,夜晚不要獨自外出,隨身攜帶辣椒水、檸檬水,積極配合強暴者以避免更大的傷害,練習女子防身術等等一些對于真正的強暴威脅沒有多大用處的建議。敘事者“我”的“幻想”就是對這些媒體的嘲笑甚至是挑釁。首先,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黑夜的街道上。這顯然是在表明,“我”拒絕是為了所謂的自我保護而固步自封,將自己禁閉起來,重返淑女時代。而有關“我”試圖利用雜志建議的各種自衛招數保護自我的所有敘事似乎都很滑稽。其中一個“幻想”里,當“我”在黑乎乎的街道上被一個男性抓住胳膊時,便開始翻找檸檬水,可是“我居然找不到!我的包里塞滿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面巾紙、香煙、硬幣包、口紅、駕照,類似的東西;所以我讓他把手伸出來,就像這個樣子,我把所有的東西放到他的手里,最后終于在最底層找到了檸檬水,而我擰不開蓋子,所以我遞給他,他很聽話,擰開蓋子后又把它給了我,我把檸檬水噴進他的眼睛里”[7]11。這樣戲劇性的情節在現實中會有可能嗎?滑稽的描述巧妙地質疑了這種防身術的功效。而另一個“幻想”則是對“習武防身術”的直接否定。從表面來看,幻想中的“我”是個功夫高手,把“他”搡到墻邊,成功地刺瞎了對方的雙眼,但是在對這個“幻想”的敘述中,敘事者插入了一段話:□can you believe it,in real life I’m sure it would be a conk on the head and that’s that,like getting your tonsils out,you’d wake up and it would be all over except for the sore places,and you’d be lucky if your neck wasn’t broken or something,I could never even hit the volleyball in gym and a volleyball is fairly large,you know?[7]14(你相信嗎,要是在實際生活中,我敢肯定這事就像被人蒙頭一棍,然后就那樣了,就像摘除扁桃體一樣,等你醒過來時,一切結束了,只是某些部位有些疼,如果并沒有出現脖子被扭斷或者其他類似的情況,算你幸運,在體育館時我連一顆排球都拍不起來,排球可大了,是吧?)在發表于《外國文學》2006年第四期的譯文中,這段話被翻譯為“在現實中,我會馬上血暈當場,真就這么回事,就像你的扁桃腺被挖出來,你清醒過來,發現渾身麻木,只除了疼痛的地方。如果你發現脖子沒有給扭斷或類似別的情形,你就該慶幸了。”[8]筆者不太贊成這樣的翻譯,如果把“it would be a conk on the head and that’s that”翻譯為“我會馬上血暈當場,真就這么回事”,則表明“that’s that”強調了“我會血暈當場”這件事,但實際上,筆者認為,敘事者在這里用“that’s that”、“it would be all over”等很含混的詞其實表達了很犀利的判斷,她是想含蓄地強調敘事的“幻想性”與現實的殘酷性之間的對比,要是擱在現實中,由于男女兩性的體力懸殊,暴力肯定會得逞,傷害肯定難以避免,能保住一條命就算幸運了。“that’s that”其實就是指強暴的得逞。女性能從強暴中獲得快感嗎?這種問題的荒唐性在這樣的敘事中不言而喻。阿特伍德同時也在質疑媒體這種忽視問題發生的根源,而僅僅糾纏于一些貌似關心女性的嘩眾取寵的話語行為。按照福柯的解釋,媒體就是一臺生產“性話語”的機器,生產出一些貌似誘人的話語商品,而讀者們沉浸于消費話語的樂趣之中,忽略了真正隱藏于這些話語背后的政治意蘊。
八篇滑稽“幻想”中同時隱藏了作者阿特伍德對女性主義理論以及女權主義運動的一些見解。女性主義運動的結果之一在于女性的身體和性欲從幕后走到了臺前,這一點在小說開篇有明確的體現,四個本來在打橋牌的女性立刻就被克莉絲的“強暴幻想”問題攪了牌局,除了達琳和“我”之外,其他三位女性似乎對這個話題都興致勃勃,內向的桑德拉甚至都沒有機會插上嘴。格麗塔和克莉絲的形象可以代表第二階段的女性主義理論所提倡的那種女性,她們注重外表打扮,極力展示身體魅力,渴望表達性欲,是媒體“性話語”的積極消費者。“我可以看出來,這將是她倆之間的一場戲,兩位金發美女,我這個稱呼并沒有那層意思啊,不過她倆在衣著打扮上常常較勁。”[7]10雖然敘事者刻意強調稱她們為“金發美女”并無惡意,但是根據她倆講述的“強暴幻想”,我們可以判斷出這二位的確屬于“胸大無腦”型的美女。她倆的“強暴幻想”幾乎沒有什么“幻想”的成分,只是對流行雜志或者影視節目中的某個“浪漫的”幽會情節的模擬。“我”顯然對她們的這種回答是有所鄙夷的,并且對其加以嘲笑調侃,認為她倆的“強暴幻想”并非強暴幻想而是幽會想像。這樣的敘事可以讓我們感覺到阿特伍德對于第二階段女性主義理論的懷疑態度:強調女性身體欲望,解放身體并非女性解放的標志,恰恰相反,女性如果認為可以利用自己的身體來完成自我認知、獲取女性主體性,這種思想或者行為本身只能證明那種頭腦—身體、理性—感性模式的二元對立存在之合理性。女性應該明白,腦袋也是身體的一部分。關于這一點,阿特伍德在《女體》中有更加直接的表達:“每個女體中都包含一個女性的大腦。方便得很。大腦操縱全身。”[9]在《強暴幻想》中,阿特伍德的敘事重點并不是格麗塔和克莉絲這兩個對于那個根據男性話語設計的問題不假思索便直接提供膚淺答案的女性,而是“我”這個睿智、幽默、主動的女性。“我”設計的六個“幻想”根本不是所謂的強暴幻想,而是對女性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巧妙應對強暴威脅的探索。通過由“我”提供的六個或恐怖、或滑稽、或感人的幻想,阿特伍德要表明的女性力量并不在于身體魅力,而是智慧、同情心、母性,尤其是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正是憑借這些能力,“我”最終能夠擺脫困境,甚至與對方成為互相理解、互相幫助的朋友。這種設計是對“女性有強暴幻想”這類命題的巧妙否定,對弗洛伊德的“男根嫉妒”命題的詼諧嘲諷,以及對于這種僅僅根據性別特征界定女性的話語霸權的徹底抵制。
三、聚焦敘事結構
小說戲仿式的敘事結構隱藏了另一層意義。前面已經指出,小說采用第一人稱敘事,整個敘事過程中時不時會出現“讓我告訴你……”、“你知道的……”這樣的一些口語,我們會誤以為這里的“你”是敘事者對讀者的直接稱謂,但是到了倒數第二段,作者突然把敘事場景具體鎖定到了一個酒吧,我們發現原來敘事者“我”是受人邀請,跟某個人在一起喝酒,而整個故事從頭至尾就是直接講給這個人聽的。敘事沒有對這個聽者作任何的介紹,但是有些暗示讓我們可以感覺出他應該是位男性,而且“我”本身似乎也受到了來自這個人的某種誤解甚至威脅。敘事是這樣的:“比方說吧,這里的服務生都認識我,你知道的,如果有人想給我難堪……我不知道為什么要給你講這些,不過我想這應該有助于你了解一個人,尤其是可以聽聽她們在想些什么。”[7]14至此,我們發現,原來“我”在這里是用講故事的辦法讓這個聽故事的人明白,雖然“我”喜歡單獨外出,雖然我“支持婦女解放”[7]14,但是“我”毫無所謂的“強暴幻想”,不過如果“你”愿意聆聽,“我 ”很樂意與“你”交談。我們同時也發現原來這篇小說是對《一千零一夜》的一種戲仿,或者說是個現代版的“一千零一夜”。阿特伍德用一個非常古老的神話形式回答或者說否定了一個貌似十分現代的勁爆話題。在古老的阿拉伯神話里,王后因為情欲背叛了國王,于是國王要以舉國少女的性命為代價來懲罰女性,最后拯救了這些女性以及改變了這位深陷復仇欲望之中的國王的是一位會講故事的女性舍赫拉扎德(Scheherazade),她以自己的語言能力最終讓國王改變了對女性的偏見。到了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女性能與男性抗衡的似乎也只有語言能力,而且還得取決于男性愿不愿意聆聽。這究竟是對女性主義運動成果的肯定還是譏諷?
但是,阿特伍德的態度并不悲觀,她對男女兩性通過語言溝通跨過性格障礙還是充滿了希望,小說是這樣結尾的:“總之,還有一點就是,一直都有不少交談,實際上我在這些幻想中花了很多時間來想像我該說些什么,他會說些什么,我認為如果能夠開始對話,一切都會好起來。一個男人怎么會對剛剛與他有過長談的女人做出那樣的事呢?一旦你讓他們明白了你也是個人,有自己的生命,我就不相信他們還會下手,對嗎?”[7]14阿特伍德在這里流露出的觀點跟克里斯蒂娃設想的女性主義第三階段的發展模式有些吻合。即“不再強調男女的對立或一元論,而是要求性別差異的政治必須由多元化的差異來取代。她們注重女權、女性、女人的統一,使女人不再成為與男性對立的‘準男性’,而是女人成為女人,男人成為男人,消弭沖突、對抗、暴力等男性統治話語,并推進愛、溫情、友誼的新的文化政治話語”[10]。陶麗·莫伊認為克里斯蒂娃的這種設想和弗吉尼亞·伍爾夫提出的雙性同體的觀點是遙相呼應的。雙性同體是一個古老的神話原型也是女性主義批評的一個重要概念。自從伍爾夫在其《一間自己的房間》中提出這個概念之后,許多女性主義學者就這個概念做過深刻的討論,但基本上都是否定的態度。西蘇認為,伍爾夫的觀點是“傳統概念的雙性,”是“自我抹殺也吞并類型的雙性”,“它在閹割恐懼象征的碾壓之下,帶著一種‘完整’存在的幻想。”[11]蕭瓦爾特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也花了不少篇幅分析這個概念,她認為伍爾夫的這種想法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寄托”,是“不符合人性的”,“代表著一種逃避,不愿直接面對男性或者女性”[12]。克里斯蒂娃的性別理論雖然被陶麗·莫伊貼上了“雙性同體”的標簽,但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對于伍爾夫的立場也并不贊成,她認為伍爾夫的雙性同體思想其實是一種“自我壓制”,最終只能使女性“遭受阻礙和分裂”[4]157,而伍爾夫本人的結局便是最好的說明。
從這些女性主義理論家的分析來看,雙性同體似乎只能是始于神話,終于神話,永遠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理想。阿特伍德在《強暴幻想》中雖然在徹底否定女性有強暴幻想這類貌似張揚女性自由的男權話語的基礎上表達了類似于雙性同體的一種理想的兩性生存狀態,但畢竟這只是一些“幻想”。所以它所表達的也只能是一種理想或者愿望。但是別忘了,只要有理想,就會有希望。所以我們可以說,通過把自己比擬為那個講述了一千零一個神話的舍赫拉扎德,阿特伍德在《強暴幻想》中表達的絕非是一個女性的強暴幻想而是一個雙性同體的美好愿望。
致謝:感謝中國加拿大研究會及四川外語學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給本文提供的支持和幫助!
[1]Morris,Pam.Literature and Feminism[M].Oxford:Blackwell,1993:126.
[2]Kristeva,Julia.Women’s Time[C]//Toril Moi.The Kristeva Reader.Oxford:Blackwell,1986:33.
[3]Moi,Toril.Sexual/Textual Politic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Second edition,2002:13.
[4]Kristeva,Julia.About Chinese Women[C]//Toril Moi.The Kristeva Reader.Oxford:Blackwell,1986.
[5]Foucault,Michel.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Vol.1,Tr.Robert Hurley.Harmondsworth:Penguin,1981.
[6]波伏娃.第二性(第一卷)[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11.
[7]Atwood,Margaret.Rape Fantasies[C]//Norton Anthology of Short Fiction.compiled by R.V.Cassill.New York:Norton,1986.
[8]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強暴幻想[Z].柯倩婷,譯.外國文學,2006(4).
[9]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女體[C]//好骨頭.包慧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38.
[10]羅婷.克里斯特娃的詩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107.
[11]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C]//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198.
[12]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o to Lessing[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26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