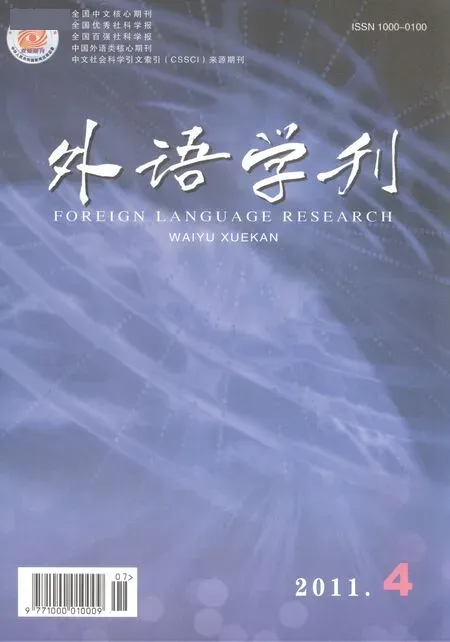透視福柯權力話語觀照下的“首爾”和“粉絲”譯語現象
孫廣治
(黑龍江大學,哈爾濱150080)
1 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
米歇爾·福柯是權力話語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法國著名哲學家,是一個后現代主義者和后結構主義者。“他創造出一種獨一無二的風格:幾乎找不到什么歷史類似物,找不到類似于他的同道,盡管在他寫作之際,他的主題完全溢出了學院的范疇,但是,在今天,他開拓的這些主題和思想幾乎全面征服了學院,變成了學院內部的時尚。”(汪民安2010:15)作為一個他所自認的“實證主義者”(Foucault 1972:125),權力、話語與知識構成了福柯所關注于這個世界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用獨特的方式加以詮釋,引領著思想的時尚,從歷史事件的具體內容升華到一種對這個世界理性上的認知。
1.1 話語中的權力
權力作為權力話語中的核心要素,在福柯看來,既不是指通常人們為追求自我的目標和利益時調配資源、作出決定、采取行動來干預事件發展進程的能力,也不是大眾概念中所說的一個為主而另一個為從,支配他人的一種能力(辛斌2006:1)。但他并沒有對權力給出明確的詞典上的那種定義,在他看來,“那東西如此神秘,可見又不可見,在場又不在場,無所不至無孔不入,這東西就叫做權力”(陸楊2000:39)。在福柯心中權力就是“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權機構、法律條文;也有無形的,如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文化傳統與習俗;也有思想、宗教的影響。這些都可以視為權力,它們是一種對人們思想行為的控制力、支配力”(呂俊 2002:108)。福柯眼中的權力內涵和外延都超出了我們日常所指。
在福柯的眼中,“權力并不屬于任何具體的個人、國家或組織,而是遍布社會實踐的各個角落。權力并不只是向下行使,也不來自一個地方,權力關系滲透于社會存在的所有層面,因而作用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辛斌2006:2)。“社會生活”體現了“權力”,“權力”彌漫于“社會生活”之中。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勾織成了一個網絡,人們生活在其中。這個網絡自然而然地限定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這如同魚和水的關系。水限定了魚的生存方式,但魚不會意識到水存在的現實,也無法擺脫水而生存。人們生活在這個網絡中,卻意識不到這個網絡的存在,但時刻被其左右、束縛和羈絆。這個無形籠罩在人們頭上的網絡也是一種權力的體現。
社會生活、網絡、權力,這些東西貌似空泛且虛無,權力實際有能體現其特質較為有形的表現物,這就是福柯所說的知識。知識就是權力。實際上培根和尼采也持有類似的觀點。知識涵蓋了有形的和無形的,涵蓋了政權機構、法律條文、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文化傳統與習俗、思想與宗教的影響等等,涵蓋了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權力和知識相互影響,如同語言和文化一樣,二者不可分割。權力影響知識,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但并不妨礙知識。“權力的作用更加深刻,因為它帶來欲望,引起快感,創造知識,以至于要從權力中脫身,是十分困難的。”(薩拉森2010:191)在另一方面,知識能將權力賦予人。占有知識就是占有權力。人們社會生活的網絡是權力的網絡,權力的體現借助的就是知識。知識反映現實社會生活中的權力關系,體現著權力。沒有知識,就沒有權力。離開權力的知識,也無法生存。
1.2 權力中的話語
福柯視野中的話語不同于索緒爾所談論的語言(language)及語言包含的言語(parole)或語言形式(langue)意義的范疇。索緒爾的言語意指個人的語言實踐或表達方式,是言語活動中受個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帶有個人發音、用詞、表達習慣等諸多特點,是語言的日常使用;語言形式則是一種抽象語法規則,是言語活動中的社會部分,它不受個人意志的支配,是社會成員共有的,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
福柯研究的話語是語言的形式和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疇的綜合(王治河1999:157)。它是“一種隱匿在人們意識之下的深層邏輯,暗中支配著各個不同群體的言語表達、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它是對某一特定的認知領域和認知活動的語言表述,是一種制約的語言應用,且體現意識形態的語義,是一種政治語義學范疇”(秦文華2001:75)。因此,福柯關注的話語不僅能夠指涉現實世界的事物、事件,而且它還能夠構建如觀世音、維納斯這樣事物,構建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哪吒鬧海這樣的事件,甚至可以構建童話世界、神話世界這樣的世界(莊琴芳2007:95)。因此,福柯所談論的話語有其獨特的所指,并非通常語言學中所論,話語體現出的是權力。
福柯所說的‘話語’與‘語言’之間是相交的關系,它與語言結構沒有關系,與言語有理性所認可層面上的相對重合,它包括了道德思考、知識與科學、談論、文本乃至傾向的表達。在福柯那里,他希望徹底擺脫傳統的語言范疇,把一切都轉向他理想中的話語途徑。
在福柯看來,話語既有書面文本,也有口頭文本,還有非言語的具體與抽象的形式。話語不僅是文獻,還是構成話語對象的實踐(莊琴芳2007:95)。話語是掌握這個世界的關鍵,它直接牽涉著知識,而更為隱蔽地牽涉著權力。福柯的“話語”實際上就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是施展權力的工具,掌握權力的關鍵,只有滿足某種條件或是從一開始就獲得資格的人才能掌控(Foucault 1984:120)。社會各階層以其特定的話語來約束和規范它們的成員以及他們的思與行。話語猶如一張網,網住了它所該籠罩的成員,使他們能夠按照一定的規矩和秩序來思考和行動(秦文華2001:75)。話語這張網的幕后推手就是權力,話語編織的網絡就是權力的網絡。因此,話語的實質是權力。
權力透過知識來加以展示,而知識的展示要更多地借助于話語。這就是它們三者相對的一種存在的關系。
2 “首爾”和“粉絲”的譯語來歷
2.1 “首爾”名稱的變遷
“首爾”的事源起現任的韓國總統、時任漢城市長的李明博在2005年1月19日召開的記者招待會。當日在會上他正式宣布政府通過決議,“漢城”一詞不再使用 ,漢語譯文改為“首爾”。韓國官方的解釋是“漢城”的英語名字是Seoul,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按英語標記的發音來稱呼韓國首都,唯獨中國人按其古代名稱將之稱為“漢城”。
翻看歷史,“首爾”因位于漢江之北,在新羅公元751年統一朝鮮后,該地得名“漢陽”。983年改名“揚州”。1067年改稱“南京”。1167年恢復“漢陽”名稱。1394年,新建立的朝鮮李氏王朝定都漢陽,改名為“漢城”,即英語的Hansung,在以后的500多年一直沿用此名,并用漢字的“漢”和“城”來書寫。在1910——1945年朝鮮半島被日本殖民者統治期間,漢城改稱“京城”。1945年朝鮮半島光復后,韓國政府將“京城”更名為韓語固有詞,用韓語文字書寫,不再恢復使用漢字書寫,羅馬字母標記為SEOUL,意為“第一城市”。2005年1月,韓國官方正式將SEOUL的漢語譯名定為“首爾”,廢棄“漢城”的用法。
筆者隨機在2010年8月11日下午三點半這個時間點利用新華網新聞全文搜索工具搜索當天零時起截止到設定的時間點在網頁上出現有關“首爾”和“漢城”詞語的新聞篇數數量結果,結果是“首爾”為1138個,“漢城”為121個。
2.2 “粉絲”內涵的演變
根據百度百科和維基百科的資料顯示,“粉絲”是一種用綠豆粉等作成的絲狀食品,故名粉絲,是國人喜食的傳統食品。但是現在,“粉絲”的含義有了極大的變化。“粉絲”變成英語單詞fan復數形式fans的音譯,表達狂熱、熱愛之意,引申為影迷、追星等意思。這個用法據考證最初源于某個南方衛視的一個大眾選秀娛樂節目,有人把英語的fans諧音譯為“粉絲”,用以指歌迷、影迷、追星族等。
筆者同樣隨機在2010年8月11日上午十點半這個時間點利用新華網新聞全文搜索工具搜索當天零時起截止到設定的時間點在網頁上出現有關“粉絲”、歌迷和影迷詞語的新聞篇數數量結果,結果是“粉絲”為5490個(意指粉絲為食品含義的數量低于總數量的2%)、歌迷為1980個、影迷為901個。
在這里,筆者想借助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對“首爾”和“粉絲”的譯語現象加以解析,通過權力話語理論提供的宏觀視角和可借助的平臺,對這一現象進行詮釋。
3 譯語問題討論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首爾”和“粉絲”譯語現象,解析這種現象看起來就有眉目了。筆者認為,“首爾”和“粉絲”譯語的背后體現的是權力和話語的問題,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話語權問題。
在權力話語中,權力、話語、知識是非常重要的三個互為關聯的點,而核心的東西是權力。權力的施展依靠的是話語和知識,而話語相對于知識有其邏輯在先性。這三者錯綜盤結,給人們編織了一張無形的網,使我們在這個網中按照一定的秩序、規則來呼吸和生存。我們不可能離開這張無形的網絡,這是魚和水的關系。
“首爾”名字的正式確立是韓國爭取話語權的具體表現,而我們熱衷“粉絲”的表達方式則是意識形態等無形權力影響下的一種延伸表現。通過上面所引用的數據,細讀一下權力話語的內容,這絕對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要知道“傳播是權力的眼睛”(陳衛星 2008:122),要知道大眾傳播的威力。
《環球時報》2010年3月16日第6版轉載刊登了英國《每日電訊報》的一篇文章,題為《漢語遭英語單詞入侵》。文中兩派觀點旗幟鮮明。國際譯聯副主席黃有義在2010年3月的兩會政協提案中建議禁止出版物使用英文名稱、地址、人名和公司名稱,而另一方面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顧曰國認為如果清除所有舶來詞匯,那么現代漢語就只剩一半了。顧先生認為借鑒使用其他語言的詞匯是全球現象。《中國日報》在2010年4月7日其網站一篇題為“央視轉播不再說英文縮略語,俄羅斯等國有先例”新聞報道中說,央視等媒體已經接到有關部門下發的通知,要求在今后的電視轉播中盡量屏蔽英文縮略詞,而是使用賽事的中文全稱。對于央視等媒體屏蔽英文縮略詞現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謝謙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樣的舉措在國外早已不是新鮮事,例如俄羅斯媒體,早已在電視臺和報紙上全面禁止出現外語單詞”。他向記者介紹,“在俄羅斯,俄語對于每個公民來說都是最優雅、最純凈的語言。強烈的民族自尊也讓他們拒絕在各類媒體上出現外語。這是捍衛民族語言純潔、維護媒體用語統一的體現”。而對于國內媒體的此次改變,在他看來也會起到相同的作用。
筆者曾論說過翻譯中雜合的適度問題。翻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和特點,在源語和目的語間翻譯問題上處于直面話語權的最前沿。我們所處的時代是進步的時代,不是倒退的時代,但是我們的精神賴以生存的文化正在接受著各種權力的種種挑戰。權力話語告訴我們話語意味著無形的、無邊的、巨大的權力,權力透過話語來施加影響。2008年12月18日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曾提到了一句北方方言“不折騰”,稍后其英語譯法激起了學者們的熱議,而“bu zheteng”的譯法,得到了相當的認可。這就是話語權的問題。翻譯中是采用歸化還是異化的策略,充其量是戰術問題,而對于話語權的考量則是戰略問題。我們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要有意識地爭取漢語的話語權,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
陳衛星.傳播的觀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菲利普·薩拉森.福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陸 揚.后現代性的文本闡釋:福柯與德里達[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呂 俊.翻譯研究:從文本理論到權力話語[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3).
秦文華.翻譯——一種雙重權力話語制約下的再創造活動[J].外語學刊,2001(3).
辛 斌.福柯的權力論與批評性語篇分析[J].外語學刊,2006(2).
汪民安.福柯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王治河.福柯[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莊琴芳.福柯后現代話語觀與中國話語建構[J].外語學刊,2007(5).
Foucault,M.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
Foucault,M.“The Order of Discourse”in Language and Politics[C].Oxford:Blackwell,1984.
Foucault,M.Resume Des Cours(1970-1982)[M].Paris:Julliard,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