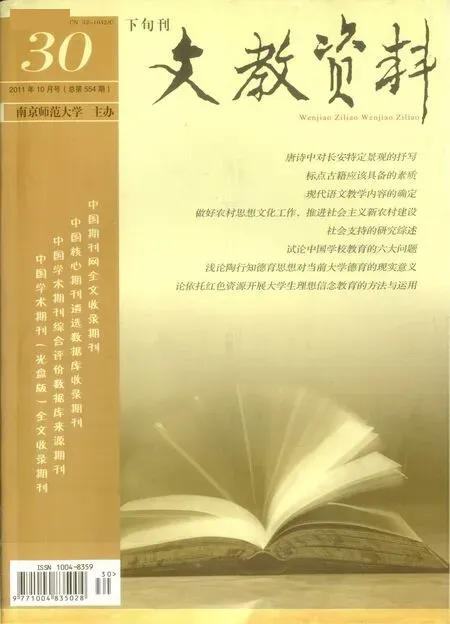現代語文教學內容的確定
王珂晨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0)
一
語文教學即母語教學,學生們從小學一年級甚至學前班就開始接觸語文,可語文到底教什么?是教教材上的那些課文?還是教大家識字免得做睜眼瞎?抑或只是為了學而教,為了考而教,為了分數而教?鑒于此,有必要探討一下今天的語文到底應該教些什么?
語文,《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語言和文字’,也指 ‘語言和文學的簡稱’。”《新華字典》的解釋是:“‘語言和文學’,也指‘語言和文章’或‘語言和文學’。”綜合看來,所謂“語文”不過就是語言、文字、文章、文學。而作為“80后”的我們從小到大對語文的印象就是:生字詞、作者簡介、段落劃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寫作文,因為我們當時的語文老師就是這樣教的,當時作為學生的我們就煞有介事地把老師所講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認認真真地記在書上,然后好好背誦,至于那些課文被我們切分之后面目全非、支離破碎,語文的工具性發揮到了極致。當我們做了語文老師了,新的課程理念出來了,要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要自主、合作、探究式學習;要知識、能力、情感三維目標,等等。至于要教什么,似乎還是沒有定論,姑且就先來說說教材里面的文章吧。
二
王榮生教授根據教材中文本的不同功能,將文本分為:“定篇”、“例文”、“樣本”和“用件”四類。
“定篇”應該是指語文課程規定的內容要素之一。教學大綱或課程標準中規定語文課程必學的篇目,這在國外也是通例。據了解,國外對“定篇”的處置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課程標準里指定作為考試的范圍,并不編進教材;一種是將部分指定篇目的主要章節編進教材。但是新的《語文課程標準》并未對小學生必學篇目做出明確規定,只是在《課程標準》后附錄推薦背誦的古詩文。“我國傳統的語文教育,教材一直代替課程,行使課程的權力。按慣例,教材的篇目,往往主要扮演著‘定篇’的角色”。在“教教材”的觀念支配下的傳統教學中,凡是選進教材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作為“定篇”來使用的,致使教學中迷信課文、過度挖掘的現象嚴重。但是有些課文例如魯迅的文章的確可以作為定篇,就是純粹的“教教材”。
“例文”是采用了夏丏尊先生的含義。夏先生提出,語文教學就是明里探討那些 “共同的法則”和 “共通的樣式”,而選文,則主要說明“共同的法則”和“共通的樣式”的“例子”。王榮生教授認為,“例文”是為相對外在于它的關于詩文和讀寫詩文的事實、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態度等服務的,成篇的“例文”,大致相當于理科教學的直觀教具,它給語文知識的學習添補經驗性的感知,并通過感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識。例文有可能是成篇的,也有可能是片段,說得更通俗一點就是“用教材教”。例如說明文教學中就可以比較廣泛地采用。在教授《南州六月荔枝丹》時,我自己講得不多,而是讓學生根據課后的圖表明晰課文脈絡,明確本文的說明對象、說明方法和寫作特色,之后滲透到作文教學中:選取一種植物或動物,查閱資料,引用詩句,寫一篇說明文。這樣學生有了參照,做起來更加得心應手,并且拓展了視野。這樣的例文就成為教學的一種憑借,一種參照,一種依據,當然前提是文章要比較通俗易懂。
至于“樣本”和“用件”更多的會出現在自讀課文或者課后的參考資料中,往往會被教者所忽視,但是如果可以好好利用的話,往往可以成為學生對定篇、例文理解的輔助。
三
但是語文教學是否只需要圍繞教材中的那些課文呢?語文是情智雙修的學科。我國語文教學界的泰斗劉國正老先生認為:語文知識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并不矛盾,“文”和“道”可以兼顧。“片面強調工具性和片面強調人文性都不可取,它們可以很好地融合”。“大語文”觀認為:語文教育,是以人獲得更好的身心發展為基點的,因此,語文教育不僅在于讓學生更好地進行語言表達,而且在于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思維方式、培養美好健康的情感與心理認知、完善和提升學生的人格與人文修養。一味地滿足于課本中的幾篇課文來進行語文教學是遠遠不夠的,課堂的語文影響力甚至遠遠比不上網絡的流行語來的影響大,所以語文教學的視野可以更開闊些,而不僅僅只是為了應付考試。
現在的學生古典文化素養普遍不高,對文言文的興趣也不高,學到文言文就頭痛,教師應重視探討語文的文化教育,讓學生們樂于學,注重讓學生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和人類高尚精神的陶冶。志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貴品格;仁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廣闊胸懷;智者“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揮灑自如;唐詩宋詞“日出江花紅勝火”的輝煌燦爛——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滋養人的精神世界、人生根基。經歷單一、思想單純、生活單調的學生正需要思想的啟迪、情感的陶冶和精神的鑄煉,亦即需要人文精神的滋養和熏陶。要使他們于潛移默化中修身化性、發育精神以終身受益,不至于在現代大眾文化的狂潮面前茫然失措而迷失自我。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十分強調學習過程中經驗的重要性,特別是學生的已有經驗及先前知識。他提倡“教育就是生活”,意思就是教育不能脫離生活內容,不能脫離解決學習者的生活問題。建構主義認為,學習是一個學習者自我認知建構的過程,知識不是被動地直接從外界輸入學習者頭腦中;它將知識的習得歸結為學習者積極主動建構的結果,而且十分強調知識是學習者自我主觀建構而成,每位學習者的建構過程與成果不盡相同。由此可見,語文教育應該教會學生在生活中學習語文,搜集各種有用的材料,應用所學的語文技巧,每天閱讀和寫作,隨時隨地把握學習語文的機會,養成生活處處皆語文的大語文學習習慣。有了這些習慣,學生就會對課本以外的自然、生活、社會等大范圍的、多角度的生活內容廣泛涉獵、獲取,必將為課堂語文學習做良好的鋪墊,從而實現從單一的語文課堂步入廣泛的社會語文空間,在學語文的同時學做人,最終實現人格的自我完善。
語文學習本質上是創造性地學習,是面向未來的學習,是把今天的學習和未來的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學習。如果語文學習僅僅被理解成文字學、語法學的鉆研,就有失偏頗。語文教師要抓住語文教學與生活相聯系的重要契機,根據學生的情感傾向、認知水平、學習心態、信息反饋、個別差異,教師因材施教,對學生進行適當的點撥指導,讓學生自己體會文章的思想美、藝術美、情感美、語言美,有選擇地模仿語句和文章的寫法,更主動地學習語文。現代語文教學的閱讀應重視“品味”,強調背誦,在“品味”中,讓語言自覺不自覺地內化為自己的東西,內化為自己的語言、語感和語用能力。這樣,既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使學生學到語文的真正本領——寫作,大大地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實現學生的三個“轉化”,即認知過程的轉化,使學生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情感過程的轉化,引導學生由不愛學到樂學;能力過程的轉化,引導學生在實際運用中形成技能技巧,由不會用到會用。
不妨拿美國的母語教育來做一番比較。看過一篇文章,講述的是一位中國家長在讓他的孩子接受了美國的小學教育。美國的孩子們可以在課堂上放聲大笑,每天在校至少玩兩個小時,下午不到三點就放學回家,而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們根本沒有教科書。作者的孩子剛入學時,作為一名中國孩子的家長他很是憂心忡忡,每天看到孩子背著空空的書包興高采烈地去上學,他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傷,甚至于懷疑自己把孩子接到美國讀書是否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然而,看到孩子會自己時常去圖書館查閱資料,看到孩子饒有興致地主動去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時,他在孩子洋溢著自信笑容的臉上找到了答案。因為他明白了美國教育關注的是:告訴孩子們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的一切努力,去贊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欲望和嘗試。而我們的課堂,學生的創造力卻在一點一點地消失,課堂舉手回答問題也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數量逐步減少。當問到一些比較開放式的問題的時候,學生往往面面相覷,站起來悶聲不吭,人云亦云,在他們心目中一直有所謂的標準答案,等著老師揭曉,他們記錄,然后背誦記憶,對付考試。因為他們從小在接受教育時就被告知要“聽話”,習慣于順從,習慣于帶著枷鎖學習,漸漸地他們懶于去思考,也不會去思考了,他們與生俱來都擁有的創造力就這樣被扼殺了。
四
創造力的培養是各國母語教育發展的總趨勢,創造性教育是各國母語教育的主旋律。我們要走出 “贏在起點,輸在終點”的困境,必須重視運用教科書培養和發展學生的創造思維能力。創造思維的基礎是豐富的知識積累,而知識的運用是關鍵。所以在課堂上應該培養學生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應給他們過多的依賴。
此外,群書教育或許是我們應該提倡的。總覺得學生閱讀面十分狹窄,比如在講到《林黛玉進賈府》這篇課文時,我讓學生說他所熟悉的紅樓人物,結果除了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就說不出別人了,不得不感慨現在學生知識的匱乏。為了讓學生拓寬知識面,我在每次課一開始的幾分鐘都請兩三位同學走上講臺說一說他們最近讀到的、聽到的文章或者故事,并談談自己的看法,適當地讓他們多讀多看,而不局限于課堂所學。
語文教育其實并不僅僅是傳統的聽說讀寫這種純粹的工具性語文的教育模式,而應該更注重人文性的發揮,并應滲透到文化領域,甚至是對學生世界觀、人生觀的初步培養,同樣也是對創造力的培養,增強學生的文化素養,拓寬閱讀的層面,所以說應該是一種大語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