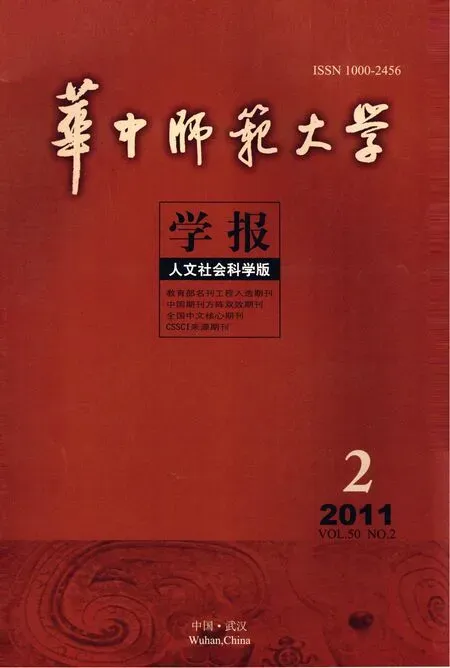民俗學的當代性建構
黃永林韓成艷
(1.華中師范大學 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9;2.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民俗學的當代性建構
黃永林1韓成艷2
(1.華中師范大學 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9;2.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傳統的民俗學將向何處去?這是民俗學界普遍關注的問題。本文認為,新時期民俗學要想走出困境,對社會和學術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必須樹立新的學術品格,對社會有所擔當。從“歷史學”轉向“當代學”,將民俗研究導入當代社會,直面當下社會的變遷;從追溯歷史、重構原型、回歸傳統,轉向關注現實、關心人生、闡釋社會、服務當今社會。讓以研究“古代遺留物”為開端的學問轉向以研究當下現實社會習俗為主的與時俱進的學問;讓以“民間文學”、“口頭傳承”為主體和“歷史考據”、“原型重構”為主要研究方法的民俗研究傳統,轉向以“當代民俗”、“現代傳媒”為主體,以“整體研究”、“綜合研究”為主要方法的新民俗研究。民俗學的這種當代性建構需要民俗學學者們具有敢于突破傳統的勇氣和不斷創新的精神。
民俗學;傳統;現代;當代性;建構
身處日新月異、豐富多彩現代生活之中的每個關心民俗學發展的學者,都不得不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傳統的民俗學將向何處去?在中國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又該有何作為?是把目光繼續停留在“古老文化的遺留物”呢,還是把目光聚焦到火熱的現實社會生活?是僅僅滿足于對民俗文化傳統的挖掘,還是直接面對并服務于現實社會生活?是把研究對象限定在口耳相傳的狹小民俗范圍,還是擴展到現代傳媒影響下形成的鮮活的新民俗?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一門學問完全無視千百萬人的現實生活,即使它有著輝煌的過去和今天,但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是不可能長期興旺發達的。民俗學只有根植于當代社會生活的沃土之中,才會有蓬勃生機和美好前程。本文從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口傳與傳媒的角度,研究當代社會變遷對民俗學的影響,并試圖從研究內容和方法兩個維度提出構建當代發展民俗學的理論體系。
一、突破“古代遺留物”范圍,直面現實生活
民俗學源于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英國“古俗”(Antiquities)和“大眾古俗”研究,當時一批從事古老知識與古物研究的學者,曾創辦有關雜志,并出版了一批相關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約翰·伯蘭德(John Brand 1744—1806)《大眾古俗之觀察》(倫敦1777年版)。在這部書的總序中特別強調“口頭傳承”(Oral Tradition)①,這個詞后來經常被用作“民俗”(狹義的)或“民間文學”的同義詞。民俗學國際用語為Folklore,它發端于19世紀50年代的英國。1846年,英國的威廉·約翰·湯姆斯(William John Thorns,1803—1885)向《雅典娜神廟》雜志寫了一封信,信中首次提出“民俗”(Folklore)這個詞,他說“貴刊發表的文章常常顯示出對于我們在英格蘭稱之為‘大眾古俗’或‘大眾文學’的那種東西的興趣,(不過,我順便提一下,與其說是一種文學,不如說它是一種知識,并且,用一個很好的撒克遜語合成詞來表示它最為恰當,這個詞就是Folklore——民眾的知識)。”②湯姆斯第一次對民俗概念、性質、內容作了界定,將古老年代的風俗、習慣、儀典、迷信、歌謠、寓言等作為民俗研究的主要內容,把Folk-lore(民俗)當作一門學問看待和一種“古代文化遺留物”體認。湯姆斯關于民俗學科的觀點,在英國得到迅速普遍的接受。1878年10月,英國民俗學會(Folk-lore Society)成立,并出版了《民俗學雜志》(The Folklore Record)。在此后近20年中,這個學科從英國及其附屬國,很快影響到美、法、德、意等西方諸國。1888年美國民俗學會成立,1890年德國柏林民俗學會成立,稍后法、意等國也接受了“民俗學”(Folk-lore)這一名稱。
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分別于1865年和1871年出版了《人類早期歷史研究》和《原始文化》。他認為野蠻人的心智現象遺存在幼稚的游戲、信仰、諺語和故事中,而這種遺存被稱為“遺留物”(Survival)。他在《原始文化》第三章“文化中的遺留物”提出“遺留物”學說,并把野蠻人的信仰和行為與現代農民的民俗聯系起來看。在他們看來,各種類型的民俗都是原始文化留存在現代社會的殘余。因此,每一個民俗事象的發現都可能有助于修復一點原始文化的本來面目。他的“遺留物”理論的要點是:在文明社會里有許多風俗不可理解,這是因為它屬于原始文化,只有通過分析與它們同時存在的神話傳說,并證之以未開化民族相應的風俗和神話傳說才能解開這些風俗的文化之謎。③
“遺留物”說在民俗學界的流行,形成了民俗研究的人類學派,他們信奉人類學家泰勒的“文化遺留物”學說,假設“原始民族”文化與歐洲農民的“遺留物”在文化史上的“同時代性”,研究對象大多是奇風異俗,即那些存在于這個時代卻在本質上不屬于這個時代、并常見于邊緣地區的文化現象。安德魯·蘭(Andrew Lang,1844-1912)在1884年出版的《風俗和神話》第一章“民俗學的方法”中說:“有一門科學,考古學,搜集并比較古代種族遺留下來的實物,如斧子和箭簇。另有一門學問,民俗學,搜集并比較古代種族的非實體的類似遺物:遺留下來的迷信和故事,以及那些見之于我們的時代卻又不具有時代性的思想觀念。準確地說,民俗學致力于研究那些極少受到教育的改造、極少取得文明上的進步的民間群體、大眾和若干階級的傳說、風俗和信仰。民俗的研究者立即就會發現這些在進化上落伍的階級仍然保留著許多野蠻人的信仰和行為方式……民俗的研究者因而被吸引去審視野蠻人的習慣、神話和思想觀念——歐洲的農民仍然保存著它們,并且,它們的形態不乏本來的樸野。”④在這里,民俗的“民”被定義為“那些極少受到教育的改造、極少取得文明上的進步的民群、大眾和若干階級”,他們是進化上的落伍者。并且,他特意把“歐洲的農民”作為代表列舉出來了。因此,野蠻人風俗和各種奇風異俗是民俗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英國的阿爾弗雷德·納特(Alfred Nutt,1856—1912)也屬于人類學派的民俗學家。他在1899年出版的《田野和民俗》中認為“這些遺留物就是民俗,就是民——社會中那部分沒有學問、又最落后的人——的知識。”文明“是城市生活的產物,民俗是鄉村生活的產物”。⑤納特認為民俗像莊稼一樣,只能生長在鄉土里,民俗是農民所特有的,而把其他職業和階層的人排除在“民”之外。這種觀點在民俗學界根深蒂固,支撐著研究奇風異俗的歷史主義學術信念。
英國民俗學家夏洛特·班尼(Charlotte Sophia Burne)在1914年出版的《民俗學手冊》中寫道:
(民俗)這個詞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公認的普通術語,它把流行于落后民族或保留于較先進民族無文字階段中的傳統信仰、習俗、故事、歌謠和俗語都概括在內。
研究這些傳承的知識,第一步就是觀察存在于現代歐洲各國低等文明居民中的大量奇異的信仰、習俗和故事,它們由一代一代的人們口頭相傳而來,本質上是社會集團中無文化落后人們的屬物。
接著,應該注意現在流行于蒙昧和野蠻民族中的與上述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信仰、習俗和故事。⑥
綜上所述,英國民俗學作為一門學科,從初創期就具有“文化遺留物”之學的性質,英國人類學家假設民俗是古代文化(原始文化)的遺留物,他們進行民俗研究旨在通過遺留物復現它們所代表的古代文化(原始文化),并透過古代文化(原始文化)理解在當時難以理解的那些民俗。因此,他們將民俗局限于文明社會中古文化的遺留物——古老年代的禮儀、風俗習慣、典禮儀式、迷信、歌謠、寓言等方面,并把奇風異俗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
英國“古文化遺留物派”的觀點,一度在學術界占有統治地位,對中國早期的民俗學理論影響極大。1923年北大風俗調查會籌備時征求會員啟事中說“風俗(民俗)為人類遺傳性與習慣性之表現,可以覘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間接即為研究文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之良好材料。”⑦如楊成志教授的《民俗學問題格》(1928年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民俗學會從書”出版)、林惠祥先生的《民俗學》(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方紀生先生的《民俗學概論》(1934講述,《民俗學資料叢刊》,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資料定印,1980年),都是以夏洛特·班尼《民俗手冊》作為理論基礎和分類依據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有學者開始認識到把民俗認定為靜止的、僵滯的“古老文化遺留物”的傳統觀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上世紀80年代,著名民俗學家鐘敬文教授在為一位日本學者的著作所作序言時寫道:“班尼女士的那種范圍比較狹隘的觀點,在我們過去學界中占著相當位置。一提到民俗學的對象,大家就只想到傳統、故事、歌謠、婚喪儀禮、年節風俗及宗教迷信等。其實,這種看待民俗學的范圍以及它所包括的項目的見解是比較陳舊的……今日世界關于民俗學的范圍和內容項目的看法差不多已發展到包括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了。”⑧鐘敬文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他強調民俗學研究“不能固守英國民俗學早期的舊框框”,要研究“現代社會中的活世態”,“拿一般民眾的‘生活相’作為直接研究的資料”⑨和對象。而且越是到80年代后期,鐘敬文的這個想法越是強烈。1994年1月鐘敬文先生在為高丙中《民俗文化與民間生活》一書所作的序中更是明確表達了這種觀點:
在最近幾年里,我在一些理論問題上花費了不少心血,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看法。關于民俗學的研究對象,可以從外延和內涵兩個方面來說。民俗研究所涉及的范圍總的來說隨著時間的發展越來越廣泛。如果說它初期在收集和研究的范圍上是比較有限的,那么,今天在有些國家里,它已經擴展到全部的社會生活、文化領域了。具體地說,如過去各種勞動的組織、操作的表現形式、技術特點和所附著的信仰;又如過去社會中,有各類團體活動像宗教的廟會,有村落和宗族的各種習慣、規例等,這些都是民俗現象。至于各地年節風俗,每人自出生到老死所奉行的誕辰、成年式、結婚、喪葬等儀禮,以及各種民間賽會、民間文學藝術活動,它們從來就被算在風俗、習尚里面,這自不必細說了。
從內涵上說,社會民俗現象雖然千差萬別,種類繁多,既涉及生產勞動、社會組織,又涉及歲時活動、人生儀禮等等,但作為一種人類社會文化現象,它們有內在的共同特點。它們首先是社會的、集體的,決不是個人有意無意的創作(即使有些本來是個人或少數人創立或發起的,但是也必須經過集體的同意和反復履行,才能成為風俗)。其次,跟集體性密切相關,這種現象的存在,不是個性的,大都是類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們在時間上是傳承的,在空間上是擴布的。在這種特點上,它們與那些一般文化史上個人的、特定的、一時或短時的文化產物和現象(例如時尚)有顯著的不同。
至于這門科學對象的時間取向,從根本上說,民俗學是“現在的”學問,而不是“歷史的”學問。拿其他學科來類比,它是像人類學、社會學那樣,以現在人類、社會的活動事象為研究對象的學問,跟古人類學、原始或古代社會史等學問是不一樣的。自然,民俗研究中也要從今溯古,或以古證今,這些都是學術活動的自然現象,也是合理現象。但這不等于說民俗學所處理的事象,主要是歷史的,它的研究資料只依靠文獻,或主要依靠文獻。應該說,民俗學的記述和研究,是以國家民族社會生活中活生生的現象為主要對象的。過去有些學者往往從古文獻上去抄輯材料,或熱衷于到歷史民俗現象中去找尋研究題目。這只是文獻民俗的整理或研究,是屬于歷史民俗學或民俗史研究的范圍,跟民俗學當然也有關系,但基本上卻不是一回事。⑩
鐘敬文先生關于民俗學是“現在的”學問的觀點和發展當代中國民俗文化學的建議,正在學術界形成共識。
對于當代民俗學來說,民俗決不僅僅只是一種具有文物價值的“古老文化遺留物”,它更是一種生生不息的文化現象。作為一個國家的傳統與習慣,它早已滲透在國人的血液之中,并鐫鑄著國人深層的心理積淀,與今日和未來都是息息相通的。正如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說過的:“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后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底源泉也。”(11)足見民俗文化與民族精神之改造關系極為密切。民俗文化既源自傳承,又在現實社會中變異,它縱向連接古今,橫向又溝通內外;它既蘊藏著民族的主體精神,又包含有外來因素的影響。當代民俗學的特征,一是表現在時代上的當代性,應充分反映當代風俗文化的新風貌;二是表現在內容上的生活性,它應當是人民群眾偉大實踐升華為學科高度的系統理論,三是形式上的傳播性,應體現文化是一個大系統,人與社會相統一的信息傳播的體系。將民俗視為文化,不僅把它看作是一種文化意識在世代流傳,而且更表現為具體、物化了的“生活相”在不斷擴布。因此,現代民俗學者應以發展的、動態的觀點來看待和研究民俗事象,把目光轉移到沸騰的社會生活,關注和研究當下生活中異彩紛呈的民俗,以科學的主人翁精神,去探求民俗文化中人的主體意識,并探尋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在傳承變異中的發展蹤跡,高揚民族精神之優長,辨析民族精神之缺失,從而更好地為現實社會服務,只有這樣,這門學問的意義才難以估量,才能獲得更好的發展。
二、突破“古老傳統”觀念,面向現代社會
隨著民俗研究日益深入,這門學科越來越重視民俗與文化傳統關系的研究。愛德文·西德厄·哈特蘭德(Edwin Sidney Hartland 1848-1927)在他1899年發表的重要論文《什么是民俗及其功用?》中說:“民俗學就是關于傳統的科學”,“作為一科學對象的傳統指未受學校教育的那些人的知識整體”。(12)法國民俗學家山狄夫(Pierre Saintyves 1870-1953)在1936年發表的《民俗概論》中明確地說,“民俗學是文明國家內民間文化傳承的科學”。他們都強調了民俗的傳統性與傳承性的特征。
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根據他在墨西哥農村小社區的研究,提出了一個理論模式:鄉民(Folk)和市民(Urban)處于對立的兩極。他認為,傳統的鄉民社會是由不與外人交流的人群構成的,他們居住在半封閉的社區里,在文化上屬于小傳統而與都市文明的大傳統相對立:“小傳統——小規模、單一性、神圣化;大傳統——大規模、多元性、世俗化。”(13)他在1947年發表的《鄉民社會》中指出:
對一般社會、特別是對我們自身的現代城市化社會的理解,可以通過考慮與我們自己的社會最不相似的社會即原始社會或鄉民社會來獲得。一切社會在某些方面都是相似的,每個社會在另一些方面與其他社會又有所不同;這里做出的進一步假定是,鄉民社會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使我們把它們看做一個類型——一個與現代城市社會形成對比的類型。
這個類型是一個理想的精神建構(mental construction)。已知的社會沒有與之恰好對應的,但是人類學家主要感興趣的那些社會最接近這一類型。實際上,對這一類型的建構要依靠有關部落族群和農民群體的特殊知識。這種理想的鄉民社會可以通過在想像中把那
些在邏輯上與現代城市中發現的特征相反的
那些特點組合起來而獲得界定,我們只有首先
對非城市民眾有了一些知識之后,才能裁定現
代城市生活特有的屬性是什么。
他在用大傳統與小傳統來界說文化的存在形態時,用民間對應他的小傳統,與少數上層精英分子所編造的大傳統不同,小傳統是大多數不識字的農民在鄉村生活中逐漸發展而成的。(14)在這里“鄉民社會”在與現代城市的對比中獲得了建構和界定。他提出的“大傳統”與“小傳統”概念在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界有較大影響。
從以上理論及闡釋中,我們可以看出,歐美學者關于民俗研究對象“民”及其“傳統性”特征的認識是他們從直觀經驗中逐步構造出來的。事實上,在1946年,美國人類學家赫斯科維茨(Me1ville J.Herskovits 1895—1963)就指出,民俗學家應該從研究“過去僵死的遺俗”——作為遺留物的風俗——轉向“關心生活現實”,而且“民”可以被看成“作為展示出可辨認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一個群體的任何社會的任何民眾或任何階層”(15)。盡管赫斯科維茨的觀點非常有見地,然而,在相當長時期,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20世紀60年代,隨著美國城市化步伐加快,人們的生活方式急遽變化,這也促使美國學者對民俗的深入思考。印第安那大學的理查德·多爾遜教授(Richard M.Dorson 1916-1981)是美國當代最著名的民俗學家之一。1973年8月28至30日,來自31個國家的民俗學家會聚在印第安納大學,研討“現代世界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問題。多爾遜在會上做了同題發言,他從“城市”、“工業與技術”、“大眾媒體”、“民族主義、政治與意識形態”四個方面論述了民俗的當代性。(16)他認為傳統民俗學對“民俗”的界定是相對于城市中心而做出的,并在分析這種定義內涵因素時,按照雷德菲爾德所用的二元模式列出了它們的對立因素。他說:“有些外人把民俗看作博古家溺愛的無聊玩意兒(這種態度經常可見),并把民俗學想象成關于過去的學問,想象成研究特別有趣但落后、衰敗的亞文化的學科。雖然我不能接受這種價值判斷,但是我承認,民俗研究從一開始確實是與古俗和‘原始的’鄉下人聯系在一起的。但是另一方面,有人從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民俗研究,使民俗研究呈現為當代性的,使他們面對‘此地’和‘現在’,面對城市中心,面對工業革命,面對時代問題和思潮。根據這種觀念,民俗存在于活動發生的地方,而根本不是死水中的一堆沉沙。……然而,這兩種觀點并非不可調和。‘Folk’不必僅指鄉下人(country folk),最好意味著趨向傳統的匿名大眾(anonymous masses)。即使鄉下人搬進城里(在過去幾十年里,鄉土人口的流入使世界大都市人口劇增),民俗學家并不喪失對他們的興趣。出生在城市里的后代也并不必然失去作為民間群體(folk groups)的屬性,因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行為、服飾、烹調、語匯和世界觀也可能由傳統力量來塑造。”(17)在1973年出版的《傳說中的美國》(America in Legend)一書中,他從理論上提出民俗的當代性(the contemporaneity)問題,并以此與民俗學的古老性(the antiquity)形成對比。他認為,“民”不必單指鄉民,而是指傳統取向的匿名大眾(anonymous masses of tradition-oriented people)。因此,他把民俗之“俗”界定為民間文化、口頭文化、傳統文化、非官方文化。多爾遜認為民俗文化是活生生的傳統,屬于它所處的時代的觀點是很精辟的,然而,他仍然把民俗限制在民間宗教等傳統的民俗觀所認定的領域里,他的所謂的傳統依然還是歷史傳統、鄉土文化的傳統。
美國民俗學家阿蘭·鄧迪斯(Alan Dundes 1934-)在1965年出版的《民俗研究》(The Study of Folklore)將民俗從有限的傳統文化轉而面向文化傳統這一整體。他說:
“民眾”這個詞,可以指“任何民眾中的某一個集團”,這個集團中的人,至少都有某種共同的因素。無論它是什么樣的連結因素,或許是一種共同的職務、語言或宗教,都沒有關系,重要的是,這個不管因何種原因組成的集團,都有一些它們自己的傳統。在理論上,一個集團必須至少由兩個人以上組成,但一般來說,大多數集團是由許多人組成的。集團中的某一個成員,不一定認識所有其他成員,但是他會懂得屬于這一集團的共同核心傳統,這些傳統使該集團有一種集體一致的感覺。(18)
鄧迪斯從傳統的共時性角度強調了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指出了傳統是群體現在共同享有和傳承的。
在《民俗、神話與傳說標準辭典》(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Mythology,and Legend)關于民俗學的多項界說中,最基本的定義是:“民俗的內容是人民——包括原始的和文明的——傳統創造。它們是運用聲音、文字以韻文和散文形式構成的,同時它還包括民間信仰或迷信、習俗和表演、舞蹈和游戲。進而,民俗學不是有關某一族群的科學,而是傳統的民間科學和民間詩學。”(19)《大英百科全書》“民俗”條目說,“民俗,是普通民眾始終保存的、未受當代知識和宗教影響的、以片段的、變動的或較為穩固的形式繼續存在至今的傳統、信仰、迷信、生活方式、習慣及儀式的總稱。”(20)
上述觀點概括起來,就是他們認為民俗學是關于傳統的科學,民俗是代表某些范圍內的文化傳統,是指與較高階層的文化相對照下的俗民的全部文化傳統,是在民間口頭講述和傳承的文化傳統。將民俗學定位為關于俗民的文化傳統當然沒有問題,但我們必須充分意識到當前正面臨著的變化迅速的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傳統的現代意義和內涵。
通常人們習慣于把“傳統”與古老的事物等同起來,即將傳統作為一個“過去”的時間概念來理解。事實上,傳統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它是在時空中延續和變異的,它存活于現在,連接著過去,同時也包蘊著未來;傳統是現代過去的凝聚,現代將是未來的傳統。以探討現代性及現代社會變遷著稱的英國社會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把我們當今生存于其中的社會表述為“后傳統”社會(Post-Traditional Society),他指出:“現代性,總是被定義為站在傳統的對立面;現代社會不一直就是‘后傳統’的嗎”?他認為,現代性在消解傳統的同時重建了傳統。(21)現代性摧毀了傳統,然而現代性未能(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傳統,或者說傳統在現代社會中依然延續著并按其原有邏輯生長著,而現代性發展的后果,即進入所謂后現代以來,社會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現出斷裂的特性,從而使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面臨著大量我們不能完全理解更無從控制的現象和過程;同時也使我們的行為陷入無常規可循的境地。這種情形或許是吉登斯將現代社會稱為“后傳統”社會的主要原因。
民俗是群體的生活文化,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民俗,有群體的地方就有民俗存在。民俗對人們生活和群體存在如此重要,是因為民俗包含著人們相處、互動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指令,包含著人生最基本的行為方式。一方面我們要注意民俗具有的傳統性和傳承性,另一方面我們更要注重它的演化和流變。作為民俗的“傳統”,常常在變化的壓力下,通過新發展以重建維持之。舊時代的民俗,有的已被淘汰,有的正在演化,新的民俗也在不斷產生。尤其是當一個民族處于歷史轉折的重要時期,經濟、文化、政治的迅速發展,必然帶來社會生活和人們心理的急劇變化,新舊民俗作為新舊文化意識的一種表現,也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如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層面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市場經濟、消費主義、大眾文化、網絡語言、虛擬空間、白領生活、小資品味、新好男人、人造美女……帶來的震驚和刺激讓人應接不暇,而與這些相關聯的人們日常生活中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的變化體現為種種可以稱為“新民俗”的現象。因此,民俗傳統不僅是一種文化承繼,更是一種文化建構。
傳統民俗研究由于受“古老傳統”觀念的影響,往往將民俗事象割裂于鮮活的現實日常生活之外,使得民俗學的當代性和現實取向難以實現。作為后現代民俗,其中的傳統是新創造出來的。我們現在應將民俗研究的社會領域擴展和延伸至錯綜復雜的現實社會關系中,一方面,擴展包含超越地區、時代、階級差異的相關領域中;另一方面,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成員的視野中,隨著持續的變異,這種擴展又凸現出不同的意義。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民俗學關于傳統的研究至少包括三個方面:前現代社會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主義文明新傳統、市場經濟對傳統改造或重構的現代傳統,這幾個維度同時構成了中國民俗研究的獨特性和學術靈感的來源。因此,民俗學要在當代社會立足,必須從歷史主義轉向現實主義,從注重歷史傳統轉向面向現實社會。
三、突破“口頭傳承”局限,注重現代傳媒
從世界民俗學早期的實踐和學科界定中,我們可以大致概括出它的主要特點:一是口述性,二是傳統性。前者是其主要的存在和表達形式,后者則旨在強調其歷史傳承特性。在人類學的用法中,“民俗”這一術語常指神話、傳說、故事、寓言、謎語、歌謠和其他以口頭語言為媒介的藝術表現形式。因而,民俗可以被界定在語言藝術范圍內。(22)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的人類學教授威廉·巴斯科姆(William R Bascom)有一句名言:“所有民俗都是口頭流傳的,但不是所有口頭流傳下來的都是民俗”。“在無文字的社會里(人類學家傳統上對這類社會有很大興趣),一切結構制度、傳統、習俗、信仰、態度和手工藝都是以言詞教導和示范作用口頭傳下來,當人類學家同意將民俗定義為口頭傳承時,他們沒有注意到,正是口頭傳承這個特點,才把民俗與文化的其他事項區別開來”。(23)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弗朗西斯·李·阿特利(Francis Lee Utley)在1916年發表的《民間文學:一個實用定義》一文中認為,為了使民俗的定義與實際民俗研究相適應,有必要采取“實用定義”,他說:
為了我自己實用便利,我采取一種非常簡單的表述,即:民間文學無論在哪里被發現,與世隔絕的原始社會也好,接近文明邊緣的社會也好,都市社會或村落社會也好,上層統治者與下層階級也好,他們都是一種口頭傳承的文學,“口頭傳承”這個關鍵詞的應用價值是很大的。(24)
在傳統社會里,民眾一般被限制在某個相對穩定和封閉的群體或村落里,生產和交往的人數、規模都十分有限,環境范圍并不很大,也并不是很復雜。這時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把握更多的是建立在“第一手信息”的基礎之上,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流主要是通過口頭來進行,人們對事物和生活的認識總是和特定的地域或地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民俗文化多屬于口傳的文化,人們通過直接的對話與交流使得本民族的民俗生活和文化傳承一次次積淀在活形態的民俗活動中。
由于傳統民俗學強調民俗的口頭性特征,因此,十分注重口述史和口述傳統的研究。口述史(oral history)與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雖然都是以口頭敘述的方式呈現,但前者受到個人生命周期的限制,主要是對個人親歷的生活事件及感受的敘述,一般關注較近之過去的經驗,而不是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記憶,它通常表現為老百姓記憶與敘述自身經歷的個人生活史、家庭史、宗族史、村落史。后者則是世代相承的口述證詞,主要指比較定型的、程式化的、在民間口耳相傳的文藝形式:包括神話、傳說、故事、民謠、諺語等文藝樣式。口述歷史最為突出的功用在于收集口述憑證,彌補文字資料的不足。而作為集體傳承的程式化了的口述傳統則是喚起民族歷史記憶,激發其自我意識,進而建構族群認同邊界的主要依據。簡而言之,口述史與口述傳統,前者是經歷,是個人敘事,而后者則是記憶,是集體記憶和表述。
然而,隨著對民俗認識的深入,民俗被認為是或者是應該是“口頭傳承”的觀點,受到到學者們的質疑。阿蘭·鄧迪斯在《什么是民俗》一文中指出:
首先,無文字的文化(人類學家稱之為“無文獻文化”)幾乎全靠口頭傳承,例如語言、狩獵技術、婚姻習俗等,都是口頭傳承的,但很少民俗學家將這類文化資料看作民俗。而且,即使在有文字的文化中,一些口傳信息,如怎樣開拖拉機,怎樣刷牙等,一般也不看作是民俗。由于口傳的東西并非全是民俗資料,所以僅憑“口頭傳承”本身,并不足以區分民俗與非民俗。
第二,某些形式的民俗與口傳形式相反,幾乎完全是以書面方式存在和流傳的。例如簽名冊上題的詩句、書籍眉批、墓志銘和傳統信件(如連鎖信)。實際上,一個職業民俗學家,決不會僅僅因為某個民間故事或民歌,在其生活史上的某個時期,曾被書寫過或印刷過,就說它不屬于民俗學研究的范圍。當然,一個民間故事或一首民歌,如果從來未經口頭流傳,他必定會聲明它不屬于民俗。它可能屬于在民間形式基礎上創作的文學作品,但它本身卻不是民間形式。自然,上述書面形式也是極少以口頭形式傳承的。
以口頭傳承為定義原則的第三個困難,是以身體動作為主的民俗形式,如民間舞蹈、游戲、姿勢等,是否經過口頭傳承還是個問題。一個孩子可以通過觀察和參加活動來學會這些動作,而不需要用語言來傳授。在民間美術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傳統的象征符號,如“卐”字符,就不是口頭傳承的。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一般說來,民俗的傳承是在個人與個人之間,通過語言和動作直接進行的。但有時也有間接性的,例如,當一位民間藝術家,模仿其他藝術家作品上的傳統設計時,他可能與那位藝術家很少個人聯系,或者甚至毫無聯系。(25)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正以日新月異的驚人速度發展,充當了社會變革的先導,從而引發了全球性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劇變,它不僅對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對社會風俗,亦即我們所說的民俗文化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尤其是新的傳播技術和傳播工具不斷出現,當代社會已成為一個以“媒介環境”為基礎的社會,現代傳媒(如因特網、電視、廣播、報紙、圖書、錄像錄音等)大量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面臨著和傳統截然不同的信息環境,現代傳媒將人們投入到一個更大的開放性的民俗生活環境中,人們運用現代傳媒改變和制約著自我。在這樣的民俗生活背景下,人們應對日常生活挑戰的能力也有所不同,現代傳媒在影響著大眾生活的同時,也以現代形式反映現代民俗生活。(26)德國民俗學家保·辛格爾對現代傳媒技術與民俗的關系作過論述,他認為,現代技術世界的發達表面上造成了許多不利于民間文化生存的條件,但在現實上現代技術世界的時間感及交通、大眾傳媒造成的跨越式的空間,以及社會分化的強化,促使民俗活動的節奏加快,為民俗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涵蓋面,使之可以通過互聯網的通訊技術傳遞到超地方的領域中,并為不同社群的認同和聯誼提供機會。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現代傳播媒介反映、影響乃至包容民俗生活及其變遷,它首先發揮其最基本的文化表述工具的功能,不斷塑造民俗主體,在民俗傳播中發揮特定的能動作用。現代發達的多媒體技術將不同的民俗跨時空轉移傳播、發展,人們可以更快捷地接觸到更多民俗文化,各地區之間的民俗也互相交融,并可能產生新的民俗。現代傳媒介入人們的民俗生活中,這時人們在活動中接受到的文化信息,已經不再是原初的自然形態的信息,而是經過加工過濾的信息。現代傳媒經常與某種民俗文化絞合在一起,形成流行文化,形成新民俗。一個是在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中誕生的現代化大眾媒體,一個是帶有傳統文化色彩的人間風情,兩者的結緣完全取決于它們本質特征的趨同性以及發展過程中的相互依存性。(27)
有學者指出:“民俗是一種社會力量,具體而言,民俗是個人社會化的一種推動力和制約力,每個社會成員個體無時不在這種力量的動態過程中力圖建立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其中,對符號以及符號創作和控制的形式及常規的掌握,也就是個體獲取在這個社會動態中把握自己的技能和工具,這里的符號形式及常規、工具等指的也就是傳播媒介,這樣,傳播媒介必然要和民俗及民俗生活發生密切的關系。因此,接觸和使用傳媒成為個人與社會交往或者說人們民俗生活的重要方式,接觸和使用傳媒的方式成為民俗生活的表現和再生的方式,規范接觸和使用傳媒的程式和常規就成為民俗生活生存和變遷的重要社會基礎。”(28)傳播媒介和民俗生活變遷,其實質也就是傳播媒介和文化變遷的問題。在“媒介環境”之下,不同地區具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借助媒介來“共享”同樣的文化。因此,民俗學應從孤立事象的研究轉向面向“生活世界”的研究,從注重“口頭傳統”轉向注重現代傳媒,立足于當今文化和民俗生活所處的時代背景,即當今一切文化均處于“媒介環境”中,并且傳媒日益成為社會和民俗生活變遷過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這—主題進行具體闡述。同時,我們還應該在全球信息傳播技術更新和全球媒介市場條件的時代背景下研究已經變化了的民俗事象,關注民俗學的未來,將我國民俗研究引入一個嶄新的境界。
四、突破“考據重構”方法,開展綜合研究
民俗學與其他學科一樣,經歷了一個發生、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開始是對原始蒙昧人進行研究,主要涉及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崇拜儀典等;后來是對本民族民俗進行研究,有的側重于民間文學的發掘、研究和利用,有的側重于環境地理與生態的研究;再后是對民俗所產生的社會心理內容進行研究,主要是解析各種心理狀態下人的行為方式。從而形成了“民俗三大學派”——人類學派、人文學派、精神分析學派。早期人文學派主要從文學和歷史的角度開拓民俗學的研究領域,其理論背景是企圖找出一個流動傳播的學說,在各民族風俗中比較異同,追溯源流;相繼而出現的人類學派,則是用社會科學的理論來檢驗民俗學的材料,通過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的分析,著重探尋人類整體行為及其與各種民俗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客觀原因,其基本理論構成了今日文化人類學的基石;此后,精神分析學派不像人類學派那樣強調功能,它強調的重點是心理因素支配下的行為模式,更加重視從人的主觀方面去解析各種心理狀態下民俗所產生的社會心理內容。當然,新的研究方法一個接著一個興起,并不意味著舊方法的壽終正寢,相反,諸種學說蜂起,形成學派林立的局面,不同學派的相互攻難,各具分歧的觀點、旨趣和準則,在民俗學的發生和發展史上,相互交叉、滲透、融會,對于民俗學的發展、繁榮和學科自身理論建設是有利的。
影響中國民俗學的西學大致可以分為人文學科傳統和早期人類學的民俗研究傳統,當代的各種民俗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一直以上述人文學科的傳統和早期人類學的遺留物研究范式為主導,民俗學的人文學科的傳統以澄清研究對象的傳播路線和演化歷史為目標,而成其為學術傳統的主要是歷史地理比較研究法,這一研究法經過神話學派、流傳學派的探索,最后在芬蘭學派的研究中得以定型。另一個遺留物研究傳統則以回溯研究對象的原型和本義為目標,他們認為民俗是種族在古老的過去創造的,現代人并不創造民俗,現代人生活中的民俗是處于野蠻時代的祖先遺留下來的,民俗在現代人中的保留程度并不相同,保留得最顯著的是那些極少受教育的群體和階級,例如農民,保留得相對最少的是受過教育的人們。正是這種觀點孕育了中國民俗學界一條主要的學術思路:首先通過采風或文獻檢索發現某種奇風異俗,然后探討它是哪一種原始文化的遺留物并推測它的原型和本義,或者推斷它有怎樣的傳播路線和演化歷史。這種重考據的歷史主義取向對于研究書面文化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對于研究作為生活文化的民俗自然很勉強。民俗學的理論范式以古典的單線進化論為前提,可是,這個前提在世界學術界早已被證明不能成立,因此,通過研究奇風異俗而重構民族原始文化的學術信念必然徹底崩潰。
當代科學的發展,已日益趨向一種完整的和系統的綜合研究,整體化過程已愈來愈成為它的主要趨勢。晚近以來,這種整體化的綜合性以空前的規模與速度指向一切傳統科學的領域。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用他自制的術語對西方科技發展的整體趨勢作出了這樣的描繪:“第二次浪潮文化強調孤立地研究事物,而第三次浪潮文化則注重研究事物的結構、關系和整體。”(29)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又是一個多層次、多序列、結構復雜的大系統。過去,民俗被狹隘地分解成民間故事、民間歌謠、民間說唱等部門,那不是事物的本質,不是民俗文化的本質。實際上,民俗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邏輯系統必須體現那一時代的全部知識體系,外來民俗和文化的沖擊或者說輸入,常常是促使傳統文化和知識結構發生變化,或按基本的知識格局作總體的轉換,或對框架作若干必要的調整和創制。
民俗學是涉及到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一個連續鏈條。如果我們研究一下民俗學的歷史發展過程,就不難發現,19世紀的民俗學從研究古老風俗學問中脫穎而出,日益分化,從而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到了20世紀,特別在當代,則表現為一種“回歸”到其他學科,與社會科學的許多學科交融、匯合,顯示出一種整體化和結合化的趨勢。20世紀上半葉,民俗學向社會科學所尋求的主要是新的認知能力。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后,這種借鑒則從尋求社會科學的一般概念轉變為方法論問題,社會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都將民俗文化作為重要的概念和課題,其研究成果都從不同角度推進了民俗文化學的發展。此外,功能主義、結構主義及“舊三論”、“新三論”等綜合科學也都為民俗文化學提出了新的視角和概念工具。民俗學與其他科學交叉的邊緣性學科也越來越多,民俗學走向民俗文化學的研究范圍及項目也擴大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研究一個村落的民居問題,就涉及到當時社會的經濟、交通、人口、生態環境、地理環境學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不是哪一個學科能單獨完成的,需要多學科知識的綜合運用,需要運用交叉科學的手段和方法,來進行更大范圍的科學的綜合。如費孝通的人類學研究為西方人類學和社會學打破彼此隔閡開了先河。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沒有拘泥于異民族,用社會人類學來研究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從原始社會推廣到文明社會。而且,這一研究還改變了社會人類學者以往那種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的單純研究者的學究面貌,樹立了一種力圖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社會改革的愛國主義變革者的新形象。某種意義上說,這是社會學、人類學和民俗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種自然結果。民俗學這種交叉和綜合研究沖破了傳統民俗學的自我封閉的體系,在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諸多學科的融合、滲透和交叉的過程中,不斷有新的分支學科和邊緣學科產生,這種新產生的分支學科和邊緣學科,不僅沒有阻塞民俗學走向新的綜合,恰恰豐富和完善了民俗學的各個側面,從而也為民俗學中重大課題的綜合研究創造了條件。
在新的歷史時期,民俗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特別需要用綜合的眼光來進行宏觀的觀照。綜合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種創造。如果說創新是發展民俗學術思想的突破口,那么兼收并蓄,善于綜合各家之長,則是打開突破口向縱深發展的正確途徑。我們認為,民俗學要走向新的綜合,必須站在宏觀的高度,透視、剖析事物整體效應的內在聯系,從而突破“思維定勢”的束縛,不斷誘發新見解、新觀點的提出。民俗學要走向新的綜合,還應當從當代社會科學最新學科和成果中汲取豐富的養料,豐富自己的理論體系,開展跨學科研究,運用社會學、民族學、歷史學、人類學、經濟學、文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沖破原先的民俗學格局,使陳舊的民俗學煥發青春。民俗學要走向新的綜合,除了更加廣泛地運用社會科學思維和方法外,尤其還要注意自然科學方法的運用。民俗學長期以來使用的以近代經驗科學為核心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僅僅靠搜集材料,對既有事物分別孤立地加以考察的方法,以搜集材料對民俗事象作分門別類的描述,即所謂定性方法。但由于民俗學研究對象存在于人類全部社會之中,尤其是當代知識容量不斷增大,前后幾代學人搜集民俗事象所積累的材料,這些對進行系統分類、保存和利用并進行新的綜合研究等,都提出了復雜的難題。舊有的思維方式與認識工具便有了相當大的局限性,僅僅是搜集材料,對既存事物分門別類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夠了,還需要引進新的思維方式和認識工具。如運用計量統計方法研究民俗則是一個創新。上述提到的民俗定性研究法注意點偏于事物對象之質的規定,而統計方法則偏于事物對象之數的規定。量的統計是質的基礎,對質的規定提供輔佐性的論據。雖然是輔佐性的,但卻往往很有力,它可以使我們對民俗事象質的分析和判斷更具科學性和說服力。在現代科學日益發達的今天,在民俗學建設中,計量分析是民俗學走向新的綜合的重要方法之一,適度地運用這個方法,可以使民俗學從封閉體系中進一步走出痛苦徘徊的“沼澤地”。
民俗學是處于動態發展之中的學問,隨著科學知識的擴展與學術的進步,民俗學必將得到不斷豐富,傳統學科的更新與新興學科的創立、崛起,不可逆轉,民俗學不僅要繼承發展民俗學的合理內核,還要吸收當代其他學科的“養料”來充實和發展自己,使自己日益飽滿和豐富起來。民俗文化學要發展,必須伸出兩手,一手要伸向社會科學,從中汲取社會科學的模式和優點;一手要伸向自然科學,引進與借鑒自然科學的方法。但是民俗學走向綜合是與其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匯合與交融。學科之間的溝通與融合是當今學術發展的重要策略,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學術界的共同努力,既要排除影響溝通與合作的非學術性障礙,又要創造兼容并包、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鼓勵和促進多樣性的學術風格和多元的研究方法,鼓勵學科間理論和方法的相互借鑒、相互融會貫通。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對民俗學進行更大程度的綜合的任務已經刻不容緩地擺在每一位有志于這門學科的學者面前。
綜上所述,新時期民俗學要想走出困境,對社會和學術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必須樹立新的學術品格,在重大的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中,民俗學研究者應該有所擔當,從“歷史學”轉向“當代學”,將民俗研究導入當代社會,直面當下社會的變遷,從追溯原型、虛構歷史,轉向關心人,關心人生,關心生活,闡釋社會、理解現實生活的意義。讓以研究“古代遺留物”為開端的學問轉向以研究當下現實社會習俗為主的與時俱進學問;讓以“民間文學”、“口頭傳承”為主體、以“歷史考據”、“原型重構”為主要研究方法的民俗研究傳統,轉向以“當代民俗”、“現代傳媒”為主體,以“整體研究”、“綜合研究”為主要方法的新民俗研究。我們深知,這種轉型需要一代又一代學人敢于超越原有的學科架構和知識體系,在不斷的反思中進行學術視野的拓展和理論創新。近年來,中國民俗研究開始從沉寂走向活躍,展現了學科振興的喜人前景,這表明我國的民俗學科正處于新的重要歷史發展的轉折關頭,并預示著必將有一個輝煌的未來。
注釋
①④⑤(12)參見多爾遜編:《農民風俗和野蠻人神話》(Richard M Dorson.Peasant Customs and Savage Myths:Selections from the British Folklorists.The Un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英文版,第1-6頁、第219頁、第257頁、第233頁;高丙中:《民俗文化與民間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頁、第14頁、第17頁、第5頁。
②登在《雅典娜之壇》周刊第982期上,1846年8月22日出版,被收入阿蘭·鄧迪斯主編的《民俗研究》(The Study of Folklore)和理查德·多爾遜編的《農民風俗和野蠻人神話》(Richard M Dorson.Peasant Customs and Savage Myths)。
③參見泰勒的《原始文化》第二章“文化遺留物”,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
⑥夏洛特·班尼(Charlotte Sophia Burne):《民俗學手冊》,程德祺等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
⑦容肇祖:《北大歌謠研究會及風俗調查會的經過》,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周刊》,第15-16、17-18期。
⑧⑨鐘敬文:《民俗學入門·序》,載《話說民間文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年,第6頁,第9頁。
⑩高丙中:《民俗文化與民間生活·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11)梁啟超:《新民說》,《梁啟超文選》上冊,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108頁。
(13)(14)參見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鄉民社會》(The Folk Society)載《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7年,第52期。
(15)轉引自戶曉輝:《現代性與民間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4年版,第51頁。另見《文化相對主義—多元文化觀》,藍天出版社(紐約),1972年。
(16)(17)理查德· 多爾遜:《現代世界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載《民俗和仿俗》(Folklore and Fakelo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第33-73頁,第 45-46頁,
(18)(23)(24)(25)阿蘭·鄧 迪 斯編:《世界 民 俗 學》,陳 建 憲、彭海斌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第42頁,第20頁,第1-2頁。
(19)(22)《民俗、神話與傳說標準大辭典》(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Mythology,and Legend),紐約,1971年,第398頁,第398頁。
(20)李揚譯著:《西方民俗學譯論集》,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頁。
(21)Anthony,Giddens.“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U.Beck,A.Giddens,S.Lash,eflexive(http://www.tecn.cn).
(26)參見黃永林:《大眾傳播與當代大眾世界——論大眾傳媒的社會功能》,《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27)參見仲富蘭:《民俗傳播學》,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447-469頁。
(28)孫信茹:《傳媒與民俗生活變遷——甘莊的個案分析》,傳媒觀察網,http://www.chuanmei.net,2002年7月4日。
(29)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第371頁。
責任編輯鄧宏炎
2011-01-16
國家教育部、發改委211項目“中華民族文化保護、創意與數字化工程”;國家社會科學
“鄉村文化建設與社區認同研究”(08BSH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