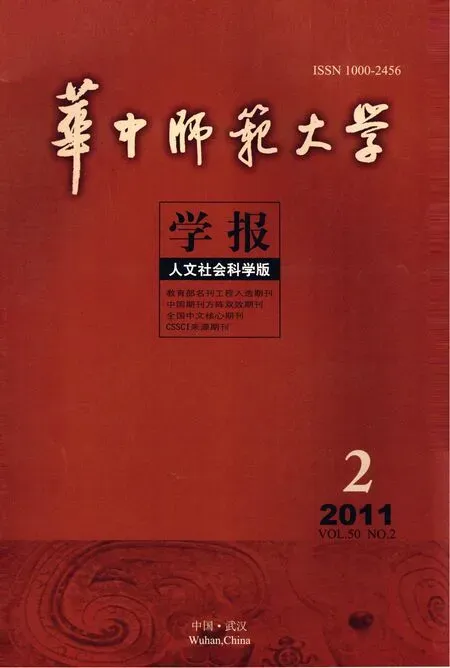當前我國中部農村貨幣化生活模式初探
——以河南省C村為例
馮 莉
(上海社會科學院 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上海200020)
當前我國中部農村貨幣化生活模式初探
——以河南省C村為例
馮 莉
(上海社會科學院 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上海200020)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農村市場的開放程度不斷加大,我國中部農村的貨幣化生活模式已經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的繁盛進一步消解了傳統文明,推動了農村社會現代化運動中物質文明的長足進步,但隨之而至的是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的被浸染、人們宗教皈依的劇增以及生活模式的貨幣化劇變。因此,積極推進貨幣文明的健康發展,是今后農村經濟社會良性運轉的關鍵。
貨幣化;中部農村;貨幣文明
一、引言
計劃經濟的解體,一方面把農村基層社會從既有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中解放出來,農村經濟在相對寬松的政策環境中獲得了勃勃生機。另一方面,隨著票制時代逐漸淡去,貨幣的一般等價物職能得以部分或全部恢復,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農村基層社會以貨幣為媒介進行消費的比例和對貨幣的需求正不斷增加。貨幣不僅覆蓋了農村的經濟交往,也全面牽系著農村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而伴隨經濟發展帶來的以高貨幣化和貨幣化貧困為典型特征的貨幣化生活模式,特別是在西部①和中部②等一些經濟相對不發達地區的農村,都相同或相似的存在著。
針對此種現象,本人于2010年6月開始,在位處華北腹地的C村,主要通過入戶訪談、街頭閑聊等方式記錄村民生產、生活等方面的言談、行為、認知和行為變化,以期對未來的鄉村研究有所裨益。之所以選擇C村作為調研對象,是因為C村的狀況具有很強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有著區別于其他自然村落的禮俗
風情,有著適于自己的話語體系和生存模式,也有著農民階層所普遍存在的優點
和劣處。同時,C村不屬于城郊,但是離城郊又咫尺之遙,其周圍交通便捷,四通八達。優越的地理位置賦予該村村民以開放和新潮的思想觀念,他們易于接受新事物,也絕少男尊女卑等封建舊識。尤其是對黨的政策等外部信息更新較快,并積極作用于各自的生活中。因此,村民的生產和生活極易受到貨幣化的沖擊和浸染,其生活貨幣化的過程也表明,C村可以稱得上是改革開放以來能夠反映我國中部鄉村基層社會生活變化的一個活標本。
二、貨幣化生活模式的表征
改革開放三十年,是我國急速貨幣化的三十年,這不僅在城市,在農村表現更加明顯,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確立,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在幾乎所有領域所向披靡,這對村民社會生活、人際交往、道德觀念和行為選擇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1)物質生活逐漸富裕,隨著在外務工人員資金回流以及鄉村經濟作物種植技術提升等因素,現在C村村民早已經吃穿無憂,鄉村超市也逐漸呈普及的態勢,村民出手不再寒酸而是愈發寬裕,在吃穿住用行各方面,想要什么,總可以方便地買到。村民L說:“現在進監獄的都能用錢再買出來,還有什么用錢買不到的。”采訪中,一位母親也對剛做了媽媽的女兒說:“放心,我去幫你帶小孩,你爸一個人在家絕對沒問題,家里啥都有,你只要給錢。”馬克思認為:“貨幣,因為它具有購買一切東西的特性,因為它具有占有一切對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對象,貨幣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貨幣的本質的萬能,因此,它被當成萬能之物。”③于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沖擊下,在C村村民看來,金錢正無所不能。至少,可以過上看似安逸舒適的生活。
(2)政治生活貨幣化趨勢明顯,以選舉為例,迄今為止,C村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選舉村干部的活動。但是,和大多數農村一樣,這樣的選舉從一開始就是不太規范的,直到最近兩次,才逐漸開始正規起來。但也正是從這兩次開始,在村民選舉過程中,用糖果、香煙等進行選票交易的行為開始浮出水面。而當越來越多的村民把選票交易當成一種生活消費而不斷得到實惠的時候,C村大部分村民對此是持認同態度的。如被問及“如果競爭村干部的這個人明顯不夠格,但是你選了他,他就給你一輛電動自行車當即騎走或者填他一張選票給100元,你會選他嗎?”得到的答案是完全肯定的,理由是,即使你不選,也有其他人選,你不選就得罪了他,他還會禍害你,而且你還得不到電動自行車或者100塊。這樣子選舉一次,就可以得到五六百,對村民而言,還是相當有誘惑力的。至于選舉以后怎么樣,就是以后的事了。村民M說:“反正現在誰當官,我就當誰的民,平頭老百姓左右不了。實在不行,下次不選他就是了。”④難怪有學者說:“對于現代民主,具體是誰掌握了權力是無所謂的……,愛誰誰,誰都差不多。”⑤
(3)社會交往與禮俗風情的貨幣化程度加劇。迎來送往在C村是常見的,只不過在大多數場合下,迎送所附加的物品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貨幣。“當然是直接給錢最便當,你拿東西,對方也同樣會現實地掂量價值多少,然后再根據估價所得判斷人情冷暖。”村民小F說,“在這里,禮錢多少是衡量關系親疏遠近的標準。”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人、任何物品的價值似乎都是由獲得貨幣的價值來決定,而且各種貨幣符號之間的相互轉化越來越便利,整個社會越來越成為一種純粹的數量關系,……人和物只能轉化為貨幣數量關系才具有真實存在的意義。”⑥這樣,貨幣的價值尺度、流通手段以及支付手段等基本職能同時發揮效用。這一點在C村的婚俗上表現尤為突出,筆者粗略統計了一下,從小見面、大見面、走親戚(成親家)到結婚,整個過程需要的花費,偏低點的6萬左右,高點的10萬都不止。很多人因為人情、面子不堪重負、甚至舉債,只待婚后再掙錢彌補。更有甚者,為了兒子娶媳婦,因為無力蓋新房或者沒有多余的房子,父母只好在兒子的新房邊上搭上兩間低矮的窩棚棲身,期待過幾年掙點錢后再做改善。由此,社會關系變成了交換關系,貨幣化的生活方式又催生了“貨幣拜物教”。
(4)高貨幣化和貨幣化貧困現象并存。貨幣化貧困是指維持基本生存之外的貨幣的貧困。貨幣化貧困現象是當前我國農村基層社會所普遍存在的。資料顯示,隨著農村經濟狀況的巨大改善,農民手頭是越來越富裕了,不過開銷也越來越大,錢越來越不經花。生產生活的全方位貨幣化使得對貨幣的需求日益旺盛,換言之,需求壓力帶來了貨幣化貧困。數據表明,C村村民年人均3500元的收入,實際上根本不夠用,日漸增強的需求壓力不僅使得自家市場交換后的經濟作物收成勉強夠本,而且還會經常吞沒外部資金比如打工得來的貨幣來源,再加上教育和醫療的需求壓力、市場交換和流動的需求壓力、現代性消費(如空調、冰箱、汽車等高消費產品已經成為村民生活改善的目標追求)的需求壓力、利益性交換的需求壓力等等,粗略統計下來,收入的增加遠遠跟不上消費的需要。“我們的年收入具體多少沒算過,也就是幾千來塊錢吧,但是一年到頭,手里落不下幾個子兒。小孩子上學,說是不交學費,可是有書本費、卷子費等等,比交學費的時候交的還多;再說合作醫療,每年每人收30元,看病可以報銷一部分,可是藥價隨之就高了,30元很快就精光,報銷也必須達到一定的消費額才能報掉那么一點,而且我們本來花的不多,結果醫院或者村衛生所上報的數目比我們實際看病支出的要高得多,也就是說,農村合作醫療絕大部分是肥了那些小診所和醫院,我們農民基本沒啥實惠。還有種田要買肥料,可是肥料價年年看漲;還要養老吧,可是我們的地大部分都被征了,給個萬把來塊錢補貼,可哪里夠維持生活,年輕人可以出去打工,我們老頭老太可怎么辦……”一次采訪中,幾個村民圍坐在一起說道。
可以發現,三十余年來,貨幣不僅在改革開放初期成功取代了票的地位,而且隨著我國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又很快積聚起自己的權威,在整個社會的所有領域,貨幣開始有了神的光環和魅力,所向披靡的貨幣不僅使鄉村基層的傳統文明失去了免疫力,變得毫無抵抗力,而且對貨幣價值的如上認識以及由此塑造出的社會語境,必然產生“貨幣拜物教”。改革開放以來,這種貨幣化的生存狀態正成為C村一種主流的選擇模式。
三、貨幣化生活模式的成因與風險
必須承認,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中部農村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生活的極大改善是形成貨幣化生活模式的直接動力。在這個過程中,村民經濟上不再捉襟見肘,生活上不再窘迫困頓。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生活模式使得村民的社會流動和對外交流變得異常的方便和快捷。沒有了票制的束縛,沒有了流通的阻滯,當代村民在奔向現代化生活的路途上變得更加開放和現代。
經濟條件的顯著提高為C村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質保障。只不過,在精神和道德力量沒有同步提升以及相關制度還不完善的前提下,我國農村基層社會的貨幣化進程就顯得非常急進,而且很多時候令人難以接受,從而為基層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了諸多社會危機。換言之,“由于目前農村的根本問題仍然是發展物質文明,生活方式的變遷缺乏足夠的關注和正確的引導,某些生活方式的變遷仍然出現滯后的現象,甚至出現了反文化的不良生活方式”。⑦深究貨幣化的成因,主要是:
一方面,國家恢復了貨幣的一般等價物職能。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最后到市場經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不斷的調適過程中,對經濟規律的把握正逐漸成熟。其中最關鍵的莫過于恢復了貨幣最基本的流通等職能。這一點恰是像C村這樣的我國非封閉農村基層社會的貨幣化運動得以開始和興盛的秘密武器。如果貨幣不能正常流通和交換,貨幣化自然無從談起。同時,市場經濟體制從體制上解決了貨幣流通的制度支持問題。從貝殼、金屬到金銀,以至金融貨幣,其背后無不與相應的機制緊密關聯,否則貨幣市場必然無序混亂。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貨幣是市場經濟得以快速正常運轉的基本元素,市場中所有的供求都必須通過貨幣或者代表貨幣的貨幣符號才能最終得以完成,因此,我國自1992年正式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加速了我國農村基層社會的貨幣化進程。
另一方面,中部農村的現代化和信息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帶來了農村生活方式的變遷。主要包括,一是全球性的現代化。全球性現代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國家政策的全局性調整,農村在調整后的政策支持下,本著“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正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這些莫不與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只不過,當前的問題是,C村的新農村建設仍只處于初步的積累財富的階段,其貨幣化的生活模式正是此階段的重要表現和必然結果。二是鄉村精英通過與外界的接觸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并在鄉村政策引導下,從而帶動農民,推動了農村的經濟增長,同時,這些社會精英自身與現代化生活方式的接軌也對周圍村民有相當的示范作用。調查中也發現,只要村里有一家或幾家率先用了空調、太陽能等現代化的消費產品,其他村民家里很快就會陸續跟上。
但是貨幣化生活模式帶來的社會風險也是巨大的:第一,加速了政治腐敗。當貨幣化程度進一步深化到讓人們相信貨幣無所不能的時候,貨幣化生存就成為生活的主流模式。而當本應局限于經濟領域的貨幣溢出自己的邊界,進入到政治領域,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腐敗、文化的低級與庸俗。通過對C村近年來選舉狀況的了解,這一點就不難明白,雖然糖果、香煙、電動車等代表的貨幣數量不多,但其所蘊含的意義和帶來的后果卻是不容樂觀的。而且最近的兩次選舉中除了被暗中“指派”的,凡是出了糖果、香煙、金錢的其他候選人都最終當選。從某種程度上說,“基層民主已經走偏了,它偏離了當初對民主選舉的設計要求,大家選當家人的目的并未達到。”C村一位村干部這樣說到。此話雖然有點苛責的意思,但是卻深切地表明,被賦予了資本意義的貨幣在政治面前必須止步,基層民主選舉要想搞好,賄選是無法回避的嚴峻話題。
第二,社會領域被侵蝕。雖然貨幣自身只是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為對個人而言的“偶然的東西”,但是卻能最終塑造出一個除了“利害關系”和現金交易,再也沒有別的任何聯系的貨幣化社會。人們的日常生活被貨幣化了,貨幣資本正在把一切社會關系轉變成為商品和貨幣,其對社會道德的沖擊必然加重基層社會的無序化。近些年來,C村及周邊村落頻繁出現的強行征地、鄰里糾紛等導致的群體性事件無一不與物質利益緊密相關,并最終只有用金錢才能擺平。這樣,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嚴重失衡。
第三、貨幣拜物教意識對人觀念的沖擊。貨幣的出現、發展是由生產能力、需求程度以及由此決定的交換規模所決定的。不可否認,最近這些年,我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改善,但是,隨著貨幣沖進政治、文化、社會領域,包括諸如買官賣官、買名收利、買命賣命等極端和不公平行為的頻發,對處于基層社會的民眾而言,其所受到的文明意識、道德規范以及人生觀等的沖擊尤其直觀和巨大。馬克思認為,觀念的沖擊、改變、解體是一切社會實踐轉型的重要前提,因此,這種沖擊帶來的更大的危害在于,其反過來對人們心理和行為的非文明塑造。“隨著財富的發展,因而也就是隨著新的力量和不斷擴大的個人交往的發展,那些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那些與共同體相適應的共同體各不同組成部分的政治關系,以理想的方式來對共同體進行直觀的宗教、個人的性格、觀點等,也都解體了。”⑧更嚴重的是,錢變成了衡量人的價值和能力高低的唯一標準。2008年,C村新一輪村干部選舉開始,包括上一級及原村干部和村民認為,要選“能人”,也就是自身經濟實力雄厚的人當村干部,才更容易解決村里的問題。其中蘊含的邏輯是:他能自己發家,說明他有致富能力,當然也能帶領大家致富。所謂的“雙致富”。結果,當老板的D被選上,1年后卻因工作不得民心而自行辭職,工作只能被臨時接替。這種“能人邏輯”思維實際上是貨幣全能觀念的另類表現。
第四,貨幣化生活方式帶來村民的退行性行為。鄭永年認為,“人畢竟是社會的產物,具有社會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貨幣化。貨幣化和反貨幣化體現在當代中國人內在的沖突。當這個沖突變得不可解決之時,各種暴力(包括對自身的暴力)就變得可不避免。”⑨而針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C村村民來說,更確切地表現是,當這個沖突不可解決,村民自然地首先選擇了退避,次之是向政府或者媒體求助,再次才會是暴力。調查顯示,近年來,C村村民對基督教的皈依趨增現象隨著村民生活的改善也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男女老少皆有,這表明并不是每一個村民都深陷貨幣化生活方式的洪流而任其擺布,對大多數人來說,貧窮和貧富差距的日趨擴大仍然是一個甩不掉的頑疾,當個人的物質生活或人生所欲難以企及相應的水平,特別是人生突遭變故,發現自己無能為力,為了心靈的安身立命或者為了“信主可以讓自家的豬長的壯、糧食產量高”之類的“承諾”,他們選擇了“萬能的主”。當然,從另一層意義上講,宗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和承擔了社會變革所帶來的巨大壓力。
四、結論
馬克思認為:“因為從貨幣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東西轉化成的,所以,一切東西,不論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轉化成貨幣。一切東西都可以買賣。流通成了巨大的社會蒸餾器,一切東西拋到里面去,再出來時都成為貨幣的結晶。連圣徒的遺骨也不能抗拒這種煉金術,更不說那些人間交易范圍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⑩于是,貨幣變得無所不能成為現代文明的最重要特征。“貨幣不僅是致富欲望的一個對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對象。”?更確切地說,過去占統治地位的一切關系,即家長的、封建的、家族的、宗教的關系,都已被迫讓位于“現金”統治的一切關系,傳統的社會秩序趨于解體之后,貨幣真正成為“人與物”的絕對中介。
因此,當前C村的貨幣化現象表明,我國中部鄉村的傳統社會秩序已經讓位于現代文明,傳統文明被邊緣化了。在C村,改革開放以前,貨幣化程度無疑是低下的,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來,C村的人們,不得不把對貨幣的追逐融化進自己的行為中,也滲透到各自的思維模式中。貨幣已經成為現實社會合法性的頂點符號,貨幣關系是各種利害關系、物質關系和象征關系的體現者和維護者。雖然“除了貨幣之外,也還存在著許多東西是社會深層中的某些存在物的影像與象征,但只有貨幣,才成為財富的化身,才擁有社會性權威并帶有強烈的拜物教性質,才能穿梭于交換的密網,并在歷史上普遍帶著被當作‘物神’來頂禮膜拜,才能成為統攝社會的物。”?
但我們不能否定貨幣化自身的意義,如果不是這個“萬能之物”的流動性、靈活性和擴張性不斷沖擊著傳統文明的邊界,使得工業革命之前存在的利益結構格局、秩序都被晃動起來,導致馬克思意義上的階級結構的深刻變化,誘發了歐洲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的變遷,進而由貨幣轉換的資本推動了聲勢浩大的工業革命,人類文明就會停止不前。貨幣化使C村村民從交易中獲得自由,從被土地束縛的狀態中解脫出來,貨幣不僅成為實現個體利益、幸福、自由的最重要工具和最重要動力,由貨幣代表的文明價值觀、貨幣化行為方式也成為社會新的重要的價值選擇。但貨幣化帶來的問題在于,在貨幣文明塑造出的更為直接、鮮明、穩固的“兩極化”結構中,純粹的貨幣化形式又完全抹煞了個體的理性、價值、希望、快樂、痛苦和罪惡。
而更深層次的危機是,隨著青壯年外出務工的日益增多和農村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日益擴大的代際繼替裂痕必將會使農村家庭養老及對孫輩的照顧與教養都將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其結果必然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的崩潰和農民的消亡。可以預見,在現代化的推動下,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以C村為代表的我國中部農村基層社會的貨幣化運動會更加繁盛,其人口結構和消費結構會繼續不斷得到調整,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限制貨幣資本溢出經濟領域,積極推進貨幣文明的健康發展。首先,要全面完善以國家、社會、輿論、公民等為主的立體監督機制及其他各項法律制度。從制度上為貨幣限定禁區;其次,努力構建符合社會主義主流價值取向的鄉村風尚,培育和諧向上的鄉村公民社會,切實維護好社會轉型期我國鄉村社會的良性發展。
注釋
①可參見張沁、陳昌文.:《西部農村家庭的需求壓力及其貨幣化貧困》,《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② 相關論文可參見趙秀玲:《我國中部農村農民負擔現狀及治理》,《南都學壇(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期;周獻德、沈新坤:《外出打工對中部農村留守家庭社會適應的影響分析》,《河北農業科學》2009年第13期等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頁。
④若無特別說明,文中所有訪談均來自此次駐村調查記錄。
⑤趙汀陽:《每個人的政治》,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44頁。
⑥李振:《貨幣文明及其批判——馬克思貨幣文明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頁。
⑦張輝金:《轉型期中國中部農村春節生活方式變遷的研究——對湖北省B村的調查》,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2007年全國優秀碩士論文。
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9頁。
⑨鄭永年:《中國的GDP主義及其道德體系的解體》,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12月29日。
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5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頁。
?栗本慎一郎:《經濟人類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07-108頁。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模式研究”(09&ZD001);上海社會科學院2010年度一般課題“轉型期鄉村選舉過程中的交換行為與心理研究”(2012)
責任編輯 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