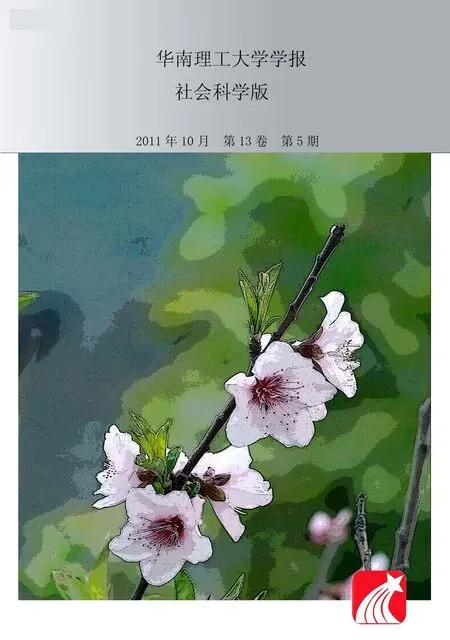先秦儒家生態思想探微*
——以孔、孟、荀為例
郭繼民
(武漢大學 哲學學院,湖北 武昌 430072)
對于生態思想,世人多從道、佛兩家入手,因道家主要關注人與自然的問題;佛家關注的雖是人生終極問題,但其眾生平等之理念卻與生態問題密切相關。故而,人們一般認為,以入世為主、以解決人與現實社會問題的儒家尤其是原始儒家似乎在生態問題上無甚表現。事實上,并非如此。
我們知道,儒家解決的固然是人之現世問題,但儒家同樣關注自然生態環境,只不過,其“生態思想”帶有隱蔽之特質:其初期表現為“依附人生”,帶有明顯的“人為萬物之靈”色彩;然而隨著人于“仁”之境界中的涵泳、悠游,最終又將人生與宇宙合二為一達到天人合一的審美境界,進而凸顯出生態觀念——此特點在孔子“仁學”思想中表達的可謂鮮明!不過,由于儒家的“天人境界”乃為一理想狀態,其生態理念多隱而不顯。當然,原始儒家的生態思想之所以隱而不彰,與中國的農耕文明有關——在以農耕文明為主的“天人和諧”的架構下,生態環境問題亦無從發生、顯現。換言之,今天的生態危機乃是以西人征服自然為核心的、絕對的“人類中心主義”之理念在歷史與現實中的邏輯展開。然而,即便如此,亦不妨礙我們去挖掘儒家的生態智慧,并且儒家“有限度的運用自然”的“中庸而務實”的“人類中心論”較道、佛“眾生絕對平等”之生態觀于今更有契合性。
本文擬選取代表先秦儒學高峰的三個人物(孔、孟、荀)為例展開,藉此對先秦儒家的生態思想做一粗淺考察,以期有資于今。
孔子:仁·尊重生命·天人境界
以“仁”為基點的“愛”的推演。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然而對于仁之確切含義,并無定論。《論語》中,有多處關于弟子問仁的記載,而孔子對仁的解答并不完全相同。此固然表明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特色,但亦透露出仁之多義性、模糊性。然而,無論仁的含義多么豐富,“仁者愛人”,卻大略為孔子仁之核心。若進一步推演、追問仁之來歷,則勢必追溯到“天”。孔子視野下的天兼有“上帝”(命)和“自然”之義,但以后者為主。“性自命出”的命題大略顯露出個中消息。明了“仁”之來源,則我們可用更為寬闊的視野來看待孔子之仁。即使孔子站在“人類中心立場”,“仁者愛人”實則是“天道愛人”,天道愛人亦可理解為天道讓人生存,即“愛生”義,因為只有首先“使人生(存)”,才能做到愛人。而做到使人生存的前提,則首先使宇宙萬物生(存)。故而,最廣泛的仁愛乃是“愛生”或“大生”,即不僅使人“生”,而且亦使“萬物生”。關于仁之生義,孔子沒有明確說出,但他卻在回答子貢的問題時,將仁之“生”義描繪出來:“天何言哉?四時運行,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這種生機盎然的生命流注于宇宙間的活潑景象乃是天德,亦即仁的深刻體現者。孔子弟子常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焉。”(《論語·公治長》)其實,孔子的“性與天道”就體現在“四時運行,百物生焉”的宇宙之生機勃勃的光景里。不過,由于原始儒家乃多傾向于“人為萬物之靈”之主張,故而自覺不自覺忽視并遮蔽了仁之“大生”之義,直到《系辭》中才明確提出“天之大德曰生”的主張,此乃歷史邏輯之自然展開歟?
按上述分析,孔子之“仁者愛人”乃縮小了的仁,是站在人本位之立場而言的,故而“馬廄失火,孔子問人,不問馬”。此亦是“愛之自然差別說”的自然流露,截然不同與墨家人與人之間無差別的兼愛,亦不同于道家人與萬物“渾然中處”的無偏私之博愛。然我們亦須對孔子帶有“差別之愛”的仁做一辯護,因為這種有差別的愛并非赤裸裸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乃是站在“中道”立場上的務實且具有“層遞”意維的仁愛立場。言其務實,在于孔子從人最根本的需要和最自然的情感出發,人類要生存勢必要利用自然(在生物鏈,人處于自然的上一層次)——但利用自然不等于破壞生態系統;人類的最基本感情是父母之愛,如不愛父母,何以愛他人,何以愛宇宙?只有立足于根本需求和自然情感之上,才可以談愛人、愛物,否則一切皆將成為空談。孔子所謂“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之主張實則建立在自然情感——“孝”的根基之上,明乎此,當不會對孔子“直”之態度再感到困惑。
言其層遞,在于孔子之“仁”乃若杜維明先生所說的“愛的同心圓”:就治國平天下而言,先修其身,進而齊家,而治國,終至平天下,其要旨乃由最基本的“孝”而逐至擴張、層遞;就愛人(物)而言,首先是愛父母,愛家人漸至愛他人,而終止于愛萬物。當然,這種推演在孔子處不甚明朗,因《論語》多處理人間世事,且以不同場景的對話展開,但在孔子后學中,此思想已得以發展:前者由《大學》格物、致知、修齊治平等層層推進;后者則由《中庸》而凸顯——“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1]P32仁的推演或曰愛的同心圓實乃孕育了生態倫理之基因,乃深層生態倫理學。
對生命的尊重。我們亦須知曉,雖然孔子仁之理念孕育著深層生態倫理思想,然而限于時代,孔子仁之思想所注重的仍然是“仁者愛人”。但是,這并不妨礙孔子對自然萬物(生態)的尊重,筆者姑且將此本然之關注稱之為“生命的真情流露”。
首先,孔子對自然生命有著一種移情之愛,此可謂仁向非人類的轉移,體現出其對生命的尊重。如“子釣而不網,戈不射宿”,人固然有在釣、射中尋找樂趣之偏好(古人亦可能以射、釣為生活來源),但卻不可一網打盡,更何況鳥同人一樣,亦有母子之情。嗷嗷待哺的小鳥等待母親的歸來,所謂“勸君莫殺枝頭鳥,子在巢中待母歸”即為仁心之外推。若用孟子的“四端”說法,此種移情當謂人之惻隱之心。事實上,孔子乃極為關心自然的儒者,他不僅要求學生學《詩經》以便“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他本人更是識辨動植物的高手,如史書上記載孔子對麒麟的辨認;又如《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對野雉雌雄之辨別——“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等等。更饒有興味的是,孔子弟子子路還向野雉拱拱手,這無疑皆表明孔子對動物的關愛和尊重,可謂仁心之推廣。
其次,孔子以自然之美的形象贊譽具有美德的君子,此體現出孔子對自然美之崇尚。“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1]P115是后人常常引用的話語,意謂君子當有松柏之堅強風骨。孔子用松柏喻君子風格,固然偏重于德,然自然之松柏在蕭條冬季表現出的油然綠意豈非宇宙增添無限生機與活力?又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拋開“時光往而不返”之寓意,難道流動之水不也是動態的生命么,不亦顯現大自然之韻律么?“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既蘊含君子德性如山(穩重),智者智慧如水(流動),亦蘊含仁者、智者對喜愛自然、崇尚自然之品質,亦算得上仁之移情。
再次,孔子所主張質樸的生活,亦隱含著對生態的保護。孔子注重“禮”,因為禮乃培養仁心極其重要的外在形式,若禮不存在,那么仁亦將難以恢復,由此可知禮之重要。然而,在《論語·八佾》中,孔子卻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并且孔子將美德與質樸、儉樸緊密的聯結起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最明顯的當屬孔子對顏回評價“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1]P87君子之道在于仁而不在于物質條件的豐厚,這實則蘊含了君子當存有儉之美德。又如《論語·述而》篇所言:“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孔子當然強調了君子仁、義的優先性,然而其中蘊含了一種淳樸、節儉的意識亦是無可否認的。無疑,此對維護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和諧有著重要的建設作用。
天人境界之理想。儒家治世歷來有大同、小康之說,那么對孔子來說,其理想的治世之極又當如何呢?《論語·先進》篇中,為后人所稱道的“曾點氣象”透射出夫子的“理想國”。(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吾與點也”,“與”的乃是一種“人與自然完美、和諧的生活場景”,此即為孔子的治世之極。也許,若孤立的看待這段描述,“曾點氣象”與道家的境界并無二致。事實上,在終極的追求上,儒道可謂殊途同歸!不同的是,道家實現理想國的路徑是退讓(退縮和不作為)的,而儒家則是進取的,并且道家的退讓(退縮)帶有太多的浪漫和幻想,相比較而言,儒家的態度則務實得多,較好的體現了可能性與現實性的統一。要言之,儒家試圖通過人的積極行為逐步將仁由“有限度的人類中心主義”推至萬物,最終開顯出人與萬物的和諧相處的天人境界(理想國):其路線大致簡略為仁——人(家、國、天下)——物——天人相融。
由此可知,儒家的理想國亦是關涉自然宇宙的,事實上,《中庸》篇中所謂的與“天地參”即為儒家所渴求的天人境界。儒家的天人之境之獲得無疑乃仁心的外推、拓展,固然摻入了諸多人為、政治等因素,然其“人為”并非純粹的機械、強制行為,表現在對自然的利用上,則是一種“合理的、有機制的實用主義”。更何況儒家追求的生活乃“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的充滿自然品質的美感生活,可謂人們當下所稱道的、真正的詩意的棲居,這種將人之價值實現、生活品質與自然美三者和諧而完美地統一起來的境界無疑較佛、道更有其現實價值,此乃為孔門之學能成為中國文化主流之要因。
孟子:仁民愛物·奉時—節用·和諧棲居
仁民愛物。殆至孟子,“仁”之義漸趨明確,孟子不但以“四端”之心豐富仁之內涵,亦將孔子的仁之外延由“仁者愛人”擴充、拓展為“仁民愛物”。如上文所述,孔子愛之主體與對象主要在人,故馬廄失火,問人不問馬。又因為“禮”為仁之根基,故孔子重禮,亦不曾因殺羊而失禮,《論語·八佾》中記載,弟子子貢試圖免去祭祀的活羊,然而孔子的回答是“爾愛吾羊,我愛其禮”。此明孔子仁愛之主旨仍在人——雖然通過其仁心之擴大可以開出天地之境界,但就現實而言,天人境界仍處于“隱”而未發的潛隱狀態。當然孔子重禮之要因在于其適逢禮樂崩壞之時,不得不靠禮來規范、約束諸多僭越、犯上的非正常關系。
孟子時期,雖然禮樂崩壞之狀并未得到實質的改善,不過,至少孟子不至于“倉皇如喪家之犬”客走他鄉,而是以較為主動的姿態出仕以推行其“仁政”理想。其仁政理想固然以愛民為主,然而治民之術亦關聯“經濟日用”,關乎“風調雨順”,或曰,關聯到“宇宙萬物”之和諧。由是,孟子之仁無論其內涵、外延皆有所深化、拓展。
就內涵而言,孟子視野下的仁具有雙重身份,既是為人之根本——即“人只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為人之根本;又是為人的最高境界——若仁能推廣、拓展乃至流布宇宙間,則無疑又是治理國家乃至達成“天人境界”的最終依據。仁的雙重地位亦可從孟子所謂的“仁的精細化”——四端顯現出來,《孟子·公孫丑》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之所以將仁放于首位,其深意亦在說明仁既為義、禮、智之發端,亦是其終結,其“仁政愛民”說無不圍繞仁而展開。
就外延而談,仁乃從惻隱之心入手,由人而及物。孟子在《盡心上》云:“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愛物”之說亦從“仁民”之層維上開出,此與孔子類同,愛物在孔子那里是隱而未顯的,而孟子將之朗現起來。其愛物之明證約略有三:一是“惻隱之心”的自覺發動。在與梁惠王談及其不忍看將釁鐘之牛的觳觫狀而引發的對動物生命的關注和尊重,雖然孟子并未阻止梁惠王以羊代牛的主張,但他仍舊將“仁愛”擴充之動物,“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儒家雖非素食主義者,亦未能達到不殺生的宗教境界,但其對生命的同情和尊重之心亦讓人感動。二是關愛之心的自然流露。孟子曾與滕文公談及治民之道,大凡涉及到對待兇猛的動物之態度時,幾凡皆用“驅”而不用“殺”,更非趕盡殺絕,如“驅龍蛇而放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等等。這種對(野生)動物生命關愛之情在孟子那里自覺不自覺的流露出來,此舉無論從敬畏生命的角度還是對保護生物的多樣性的層面皆具有重要的意義。三是其“愛物”之心不僅涉及動物,亦流注于植物等自然生態。《告子上》云:“牛木之山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是亦若彼濯濯也。”孟子用此比喻固然而說明人要善于培養其善心,但其涉及的因“過度砍伐、過度放牧所導致的濯濯童山”之描述卻透射出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對自然生命的關愛。
奉時—節用。孟子的政治主張無疑是“仁政”,而仁政之核心乃民生,民生之要害則在農事(中國乃以農立國),農事之要旨在于“無違農時”。無違農時即要“奉時”,亦即農民的耕種要符合天時——“自然規律”,“奉時”體現了孟子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孟子對自然規律的運行曾有如是主張:“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1]P297尊重并順從自然規律,不但“日月運行可以推算于掌”,更能使“仁政”落到實處,而使國泰民安,“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1]P203“不違農時”,既有其推行仁政、王道之故,亦引發愛物,維護生態系統之緣:不亂砍亂伐,不用密網捉小魚,豈非維護自然生態、尊重生命歟?由是可知,仁政與愛物乃至與自然生態便緊密的聯系起來,此非“愛的同心圓”的空洞推演,而是客觀實在的“存在”。
孟子不但尊重自然規律,而且還對自然持一種贊嘆乃至敬畏態度。在孟子與梁惠王關于“統一天下”的對話中亦涉及“時”的原則,《梁惠王》篇云:“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枯矣。天油然下雨,則苗絖然興之焉。其如是,孰能御之?”“孰能御之”,表明自然的力量是偉大不可抵御的,人們萬不可違背自然之意志(規律)。人們應順應自然,“奉天時”而動,而非相反。
孟子提倡“奉天時”、順應自然規律以求衣食充足的同時,亦倡導節儉、節約意識。《孟子·告子上》云:“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提出的“寡欲”固然從培養君子道德人格角度而言,但是,毋庸置疑,寡欲亦在愛物節用、維護生態、環境和諧等現實層面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人的欲望是無限的,如果放縱其欲望,不但造成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而最終導致人類生存的危機;而且放縱欲望的結果亦將人從萬物之靈的地位降低到禽獸的層次。在孟子視野中,人與禽獸之別在于人有“仁心”存在,仁心的獲得雖然可通過禮之約束和樂之熏染、滋養達成,但圣賢的最終達成最終須靠心的轉化而完成——由“雜亂心”向“仁心”的轉變。寡欲乃是培植圣賢仁心的關鍵點——蒙培元先生甚至認為孟子的“寡欲”帶有宗教修養的性質[2],對此,予頗有同感,因為圣賢境界無論在日常生活還是精神層面雖非凡人所“難為”,如顏回的生活世界、曾子的精神世間等等,但卻非“不能為”。人人皆具有圣賢之心,只要存養之,涵養之,則人人皆可成堯舜。這樣看來,孟子寡欲說的提出,有著雙重作用:既強調了君子內省的生活態度,促進成圣;亦通過寡欲促進節用、節儉等美德之養成,有利于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更何況,人對自然之節用、關愛亦是仁心之擴展!還須說明的是,雖然孟子提倡寡欲但并不主張禁欲,儒家提倡的是有節制的生活,這種生活態度頗值得“以享受為要,無節制地開發自然”的現代人反思。
和諧棲居。孔子的理想國乃曾點所描繪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具有浪漫色彩的“大同”之治,而孟子的仁政思想則務實了許多。針對“爭城之戰,殺人盈城;爭土之戰,殺人盈野”之現狀,孟子仁政之治反復強調的乃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1]P204這段描述,固然是孟子為當政者以仁政治天下的有效措施和途徑,且有較強的操作性——雖然即使孟子所倡導的如此和諧局面并沒有在歷史上發生過。但正所謂其主旨所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為王者,未之有也。”無疑,這種循序漸進的務實方式仍然為其最終的大一統的“理想國”服務:用“王道”一統天下,萬民和諧,實現儒家大同之治的終極理想。因此,就“理想國”的終極層面而言,孔孟并無差異,所異的無非是孟子的現實色彩更濃厚性,此既表現為孟子將“仁”進行了創造性詮釋和發揮,更表現在孟子始終針對其所處時代之痼疾而“對癥下藥”,如所謂的“五畝之宅”即如此。
“五畝之宅”在《盡心篇》中亦有論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我們姑且撇開其政治意圖,單就其描述的生活樣態而言,乃是一幅生態和諧而富有詩意的生活場景。房前有樹,樹下有雞,有蠶,有彘;田野有禾,有耕者,有自然所賦予大地的一切充滿生機的物種,此豈非陶淵明所暢想的“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之田園生活歟?西哲海德格爾所幻想的天、地、神、人四重奏的生活亦是如此,在這種節奏緩慢的生活中,流淌著生命和詩意。與海德格爾不同的是,萬物和諧并非靠“神”而是依“仁”,仁心充沛宇宙之間,則人與萬物和諧相處。詩人荷爾德林言:“人建功立業,但他詩意地棲居在這大地上”[3]按荷爾德林的說法,孟子的以仁政治理天下,即有此功效,既能建功立業而治理天下,又能讓人詩意的棲居。不過在現代工業社會,又談何容易?工業社會的“功業”多建立在對自然的過度開發之上,進而破壞了棲居的“詩意”,人又何以能“詩意的棲居”?我們依然回到孟子的根蒂處。孟子認為人皆有仁心,若能保留仁心,不但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而且還能在自然的生態中詩意的生存。由此當知,深究孟子的仁政思想,于今當有重要啟迪意義。
荀子:隆禮貴義·天行有常—與天地參·善治
隆禮貴義。孔孟之“仁”皆根植于性善說——雖然孔子未直接說出,但卻大略表達了人性善之主張。而作為先秦儒家集大成者的荀子卻一反“人性善”之見解,提出了“人性惡”的主張。無疑,持“人性善”之論,既能在邏輯上保證了“修、齊、治、平”的連貫性,亦能順理成章地開出“仁通宇宙”的天人境界。“人性惡”則似乎扼殺了“仁”的原發性,使得天下因缺少“仁的內在同質性”而難以貫通。然而,正如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所說:“人們以為,當他們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他們就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們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4]
“人性惡”看起來缺乏理想境界,但卻彰顯了人類的自我審視、自我批判意識。更何況,荀子的“人性惡”并不缺乏境界(下文敘述)。只是其境界生成之路向不同于孔孟的“內向性”的惻隱之心之喚醒,而是靠“外向性”之禮對“罪惡之心”之遏(限)制而漸次培養其仁義之心。由此,荀子提出了“隆禮貴義”之主張。
表面而言,“人性惡”似與孔孟“人性善”頗不相類,實則殊途同歸、同境界。因為在具體路徑上荀子同孔孟一樣,皆強調儒學教化之功能,荀子所謂的“化性起偽”,旨在培植人之善良德性。又由于荀子持性惡論,故益發強調外在“禮”的約束、教化乃至強制作用。追溯其禮之來源,多源于儒家經典《禮記》,且其又往往以孔孟為“榜樣”,故以繼承、融會先秦諸子百家之學的荀子雖然培養出韓非、李斯等法家之輩,但就荀子學術思想而言,仍歸于儒。
荀子視野中的“禮”,含義豐富。“禮”固然更多涉及個體生存處世的道德規范,但亦有政治法律制度義乃至“協調天地”義。《勸學》中所謂“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5]①章詩同.荀子簡注[M].上海人民出版,1974。為簡便計,以下引文出自該書者,僅注明篇目,不再一一注出。即強調了其政治法律之義。而在《禮論》中,荀子則強調了“禮”協調天地宇宙之功能,甚至“禮”朗顯為貫通宇宙人間的自然規律:“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之極,而天下莫能損益也。”由此可知,荀子這種以禮培植個體德性、以禮(法)限制、規范群體活動、以禮達到宇宙萬物和諧的功效實則暗含了禮治的三部曲:個人——社會——宇宙,而“宇宙萬物和諧”之境界又無疑使得荀子之禮與自然生態關聯起來。我們感興趣之處亦在此,那么,荀禮治視野下的自然觀又當如何呢?
天行有常——與天地參。對于天道自然,荀子截然不同于孔子“四時運行,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帶有濃厚審美色彩的體悟境界,而是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主張。在《天論》中,荀子開門見山地道:“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若要體會“天行有常”的深意,必須首先明了天地間存在著同人類一樣的倫理行為——此乃荀子生態倫理意識的集中體現。“天行有常”意味著天有一套自我運行之規律,人亦有一套運行規律。正是基于天、人自身運行之規律,所以荀子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學說。
荀子的“天人之分”理論在《天論》中有明確表述:“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此表明天事與人事界限分明——天和人的職分根本區別在于“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禮論》)對于“天”,人不可不盡人職,亦不可超越人職越俎代庖而冒犯天職,轉換為現代話語即為,人既要發揮主觀能動性,但又不可僭越自然律。用西方學者艾文荷的話講就是,荀子強調的是相分之道在于,“‘道’使得我們在宇宙的普遍計劃中各就其分,各承其運”。[6]由此可知,荀子的“天人之分”乃基于尊重“天道”——自然規律性——的基礎上。厘清人職與天職,并藉此推行其“禮治”以化性起偽,規范、教化和滋養人之自覺地職責意識,而非后人將“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誤解為“人與自然的斗爭與對立”,這是需要強調指出的。因為荀子從來沒有講過“天人相分”,他只是說“明于天人之分”,而其“分”之要義在于“職分”、“分工”,且緊隨“明于天人之分”之后,荀子提出了“不與天爭職”的觀點。在荀子看來,自然界(天)和人各有其職,各有其功用。雖然天、人各自運行,但二者亦有其“隱秘關聯”(即“與天地參”),絕非意味著“天”與“人”毫無聯系,那種將“分”理解為“相互分開”乃至“相互對立、斗爭”的觀念是不符合荀子本義的。關于這一點,荀子在《天論》言道:“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正,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無疑,圣人“知天”并不意味著在人與自然之間展開“斗爭”,“制天命而用之”亦非“制服”自然,事實上,荀子的“天行有常”已破滅了“人定勝天”的幻想。
即使從消極層面——“唯圣人為不求知天”的維度——上看,“圣人的不求知天”之境界也許在于不期然而然的順應了自然,正如《天論》所言:“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圣人為不求知天。”當然,“唯圣人為不求知天”也可解釋為圣人行為與天道有著內在節律一致性,才使得其不必“知”但卻能應和天道自然之變化:——此涉及到荀子“天人相參”之思想。
荀子的“天人相參”思想可謂《中庸》篇中“與天地參”的發展,不過,《中庸》中的“與天地參”乃是在道德層面上強調人天相融相契的“天人境界”,而荀子的“與天地參”則建立在“天人之分”的基礎之上。自邏輯而言,其“天人相參”理論乃是為“分離后的整合”,是明確了各自職分后的更高層次的交融,故其“與天地參”的理論更富有啟發性。
荀子在《天論》言道:“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愿其所參,則惑矣。”這里亦表明荀子不主張“天人相分”,將天、人、截然分開,而是主張天、地、人三者相互并存(“參”,同“叁”)、和諧共處。在解決“明于天人之分”的天、地、人如何達成“共參”的途徑上,荀子依然回歸《中庸》之“誠”。在荀子看來,“天行有常”的根基在于天地的“真誠無妄”,此“真實無妄”即“誠”,即“天德”。荀子在《不茍》中言道:“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這樣,荀子通過“天行有常”的“誠”之“天德”同君子的修身之道、政治之道(荀子在《不茍》篇中曾言:“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聯系起來,使得天人關系通過“誠”而融會貫通、彼此一體,從而實現天人合一。只有通過“誠”,“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自在自我的運行軌道上運動而達到人與宇宙的和諧。這種和諧不僅是生態的,也是審美的。同樣對于“誠”而言,既是關涉德性的,也是關乎審美的,更是關聯人與自然共同命運的大道。
關于“誠”,亞圣孟子曾有精辟論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1]P282孟子視野下,“誠”亦是仁之重要組成內容,由此可知,以“性惡”立場出發的荀子雖然強調“天人之分”,但卻終結于孔孟之“仁”,尤其是通過“誠”而達成的天人貫通、天人合一之主張更是同前輩儒學大師別無二致。
顯然,通過“誠”,通過人與天、地的相“參”,人和萬物亦有了深刻而內在的聯系,這種聯系無疑乃是“深層生態倫理”的深刻體現,尤值得當代學人重視。
善治。“天人相分”的理論無疑凸顯了人之主觀能動性,明乎此,荀子在對待自然資源及開發自然資源方面持樂觀態度也就順理成章了。《荀子·富國》中云:“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認為,天地之間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足以食人、衣人。但是,無論資源何其豐富,無論人的創造力多么強大,都并不意味著人就可以為所欲為。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荀子的主張是“制天命而用之”,意即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必須以尊重自然規律(天道)為前提,這就是荀子的“善治”思想。
善治,要遵從“時”的原則。《荀子王制》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時”的原則,實質上就是尊重自然規律,按照自然界的法則和秩序去管理,這同孟子“五畝之宅……無失其時”的原則基本一致,即要應和自然固有節律進行農事。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天論》中所謂的“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兇。”退一步而言,即使出現水災、旱災和寒暑變異的天氣也不能使饑荒、瘟疫和各種災難發生。
善治要注重對自然資源合理的開發、利用和保護,即“以時禁發”。以時禁發,既強調了開發(發),又強調了保護(禁),即言要根據自然規律,把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緊密結合起來。為達此目的,荀子還將司空、虞師等管理土木山林沼澤的官員乃如其“禮治”學說,力求從制度上保證生態保護的實施。《荀子·王制》中云:“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歲雖兇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這種主張從國家政府方面切實保證以時禁發,在當時是很有見地的。
善治,更要增強全民的(生態)道德意識。荀子號召“天下”百姓都行動起來,保護自然資源、維護生態平衡。他在《富國》說:“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谷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意即使高地不遭旱災,低洼的田地不遭水害,寒來暑往合乎節氣,五谷按時成熟,這是全體天下老百姓的事情!正如了愛國先生所言,“保護自然資源、維護生態平衡是一項‘天下’全民的系統工程,人人有責。”[7]
當然,作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修身成圣、治國平天下無疑仍然是荀子的最高理想。而達此目的,則尤其需要“一與一是為人者”的圣人,因為圣人能“上察于天,下錯于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荀子·王制》)更重要的在于,借助于圣人的教化作用,才能化性起偽,制禮樂、明法度,安排好生產和生活,保護好自然資源,使整個社會有序地發展下去,實現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當今世界生態嚴重失衡的今天,荀子“圣人之制”的生態資源愛護觀不啻是一劑難得的濟世良藥!對于“圣人之制”,荀子充滿了希望,他曾用富于詩意的語言表達了這種希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荀子·論禮》)無疑,這既是儒家渴望的平天下的“大治”,亦是人與自然、天地萬物和諧的美好圖景,即天人合一。
作為先前儒家的三個重要人物,孔、孟、荀三家思想雖然各有側重——如孔子重“仁”,孟子重“心”,荀子尚“禮”,但其最終目的乃是實現天人合一,且三者具有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展現了先秦儒家學術的發展歷程。尤其三位儒家大師在實現其“理想國”,既肯定合理的、有限度的開發、利用自然的必要性,又將“仁”與萬物共生、共融進而開發出“天人合一”的道德和美學境界;既凸顯了“深層生態倫理思想”,又不全然否定人的主體地位,真正體現了儒者的“中庸”之道。當然,他們的主張并沒有在現實中得到徹底的落實,但其體現著仁愛、和諧、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仍然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值得后人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