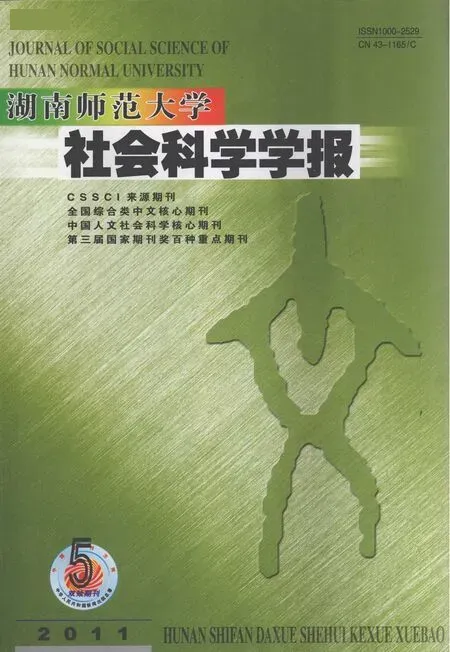從拯救現象到人的解放——論辯證法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孫云龍
(復旦大學 歷史系,上海 200433)
從拯救現象到人的解放
——論辯證法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孫云龍
(復旦大學 歷史系,上海 200433)
從辯證法的最初形態談起,簡要地回顧了觀念論辯證法在哲學史發展階段中的幾種重要樣式,以及在黑格爾哲學中的最終完成形態。上述回溯為馬克思所發動的辯證法革命提供了發生學背景,由此我們更能清晰地看到,究竟從何種意義上講,歷史唯物主義是對觀念論辯證法的倒轉,從而彰顯出這場哲學革命的深刻意義。簡要地梳理了早期馬克思哲學文本中的辯證法表述方式,主要論及《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最終以《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物質生產辯證法為最后議題,并就此展開討論,提出我們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發展道路的理解方式。
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人的解放
一、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及其使命:拯救現象
辯證法起源于古希臘文的“談話”,這個詞的詞根lek源自lego,是“說”的意思,前綴dia則是“經由”,因而“辯證法”的字面意思就是“通過談話交流看法”。針對智者派的詭辯術,蘇格拉底提出只有辯證法才能開啟人類的理性,借由矛盾分析以獲得確定性的知識,明辨是非善惡。柏拉圖繼承并發揚了蘇格拉底式的辯證法,將其進一步提煉為認識理念世界的思辨方式①。“當一個人企圖靠辯證法通過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覺,以求達到每一事物的本質,并且一直堅持到靠思想本身理解到善者的本質時,他就達到了可理知事物的頂峰了。”[1](P298)柏拉圖在晚年意識到蘇格拉底式理型論的內在困境:理念與現象的分離。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理念與理念間的分離和理念與現象的分離。如要維護理念論立場,則必須要在上述分離中重新建立聯系。晚年柏拉圖不再認為理念是獨立于現象的實存,而是存在的抽象規定性,理念與理念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這種聯系是通過辯證法建立起來的。現象是個別之物的組合,是感覺的對象,現象世界在時空中流變;理念是純粹的存在,是超越時空的自我同一,只能通過思想來把握;辯證法則是知識歸納和分類的方法,按照概念間的并列或從屬關系,將現象世界建構成為“一個概念的邏輯體系”[2](P173)。因而柏拉圖將其工作稱為“拯救現象”,救援工具就是辯證法②。柏拉圖晚期思想的發展,在辯證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既維護了蘇格拉底的理念論,又為亞里士多德的范疇學說和邏輯學開辟了道路,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辯證法的根本特性:對立統一、矛盾運動、整體決定部分等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拉圖那里,辯證法不僅是一種思維技術,它就是哲學本身。
辯證法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具有多重意義。一方面,他的形而上學是古典辯證法的集大成者,盡管相關學說并未以辯證法命名;另一方面,辯證法在亞氏那里成為邏輯學的專門術語,這一轉變對后世邏輯學的發展影響極大。因而,我們將從上述兩個方面簡要回顧亞氏的辯證法思想。
亞氏在《范疇篇》中提出實體理論,認為個別之物為第一實體,抽象的“種”和“屬”都是第二實體,以此解決理型分離論的困境。然而在《形而上學》中他推翻了上述想法,提出形式為第一實體。形式本體論的提出標志著亞氏思想的巨大轉變,開始從關注經驗中的個別之物走向探問事物背后的本質規定性[3](P736-737)。所謂本質就是由其自身而是的東西。在亞氏看來,本質是恒久不變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亦將如此。本質內在于現象卻具有更高的現實性,現象處于流變之中,本質則是現象變化的動力因和目的因。而且,本質具有普遍關聯性,部分只有在整體中才能得到規定。由此,亞氏從一般本質學說過渡到對宇宙本質的追問,亦即神學。亞氏神學乃是理性對于第一因和終極因的追問,因而也是關于宇宙本質的邏輯解釋,這里的神其實就是最高的理性精神,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遙相呼應。因而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對《形而上學》第十二卷的內容最為重視,稱其為“亞里士多德的最深刻的思辨”。
除了上述辯證法思想之外,辯證法作為專門術語在亞氏邏輯學中有著特別的用法。在《論題篇》開端亞氏將推理方法稱為辯證法。辯證法有積極與消極之分,積極的辯證法是正確的論證程序,“通過它,我們就能從普遍接受所提出的任何問題來進行推理;并且,當我們自己提出論證時,不至于說出自相矛盾的話”[3](P351)。消極的辯證法是歸謬推論,在《辯謬篇》中主要體現為檢驗和反駁的程序,主要作用是避免在知識范圍內出現荒謬的論證。辯證法的這一新增義項對于后世邏輯學影響巨大,中世紀經院哲學在邏輯學方面也沿襲了辯證法的這一用法,后來傳至德國,也就間接地影響了康德對于辯證法的理解和使用。
康德在《邏輯學講義》中提到,邏輯學分為分析論和辨證論。分析論主要研究理性思維的一般規則,忽略一切對象差別,因而也就是正確思維的形式規則。辨證論則是對邏輯誤用的批判。因為邏輯規則僅為思維的純形式法則,與對象無涉,因而不可能單獨產生知識。如果把邏輯學等同于關于對象的知識,那就會成為辨證論。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這里使用的術語“辨證論”,其德文原文為Dialektik,也就是辯證法。俞吾金教授曾撰文指出上述翻譯差異[4](P53*58)。我們認為這一問題的指正非常有意義,有助于重新建立起康德與古典辯證法之間的關聯。很顯然,康德語境中的辨證法(論)取自亞氏邏輯學中的消極含義,即對邏輯誤用的歸謬和反駁。先驗辯證論指出理性自身內在的辯證法,并為其在知識領域中的應用劃界。
黑格爾對康德哲學有著全面的批判,包括康德的辯證法思想。“康德揭示出二律背反,雖然無論如何都必須被視為對哲學認識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促進,因為這消除了知性形而上學的僵硬的獨斷論,指出了辯證的思維運動;但是同時也必須看到,康德即使在這里也是停留于物自身不可知這個單純消極的結果,而沒有達到對二律背反的真正的、積極的意義的認識。”[5](P133)在黑格爾看來,康德誤解了辯證法的意義,將辯證對象的一端絕對化、孤立化。因而,超越康德哲學之路就在于運用積極的辯證法解決二律背反。理性被黑格爾規劃為自在自為的運動過程,既是自我的絕對同一,又是自我異化和自我揚棄,是一種從自身出發、以自身為目的辯證運動。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爾的辯證法實質上是從近代辯證法向古代辯證法的復歸,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觀念論式辯證法精神的復活和自我完成。如前所述,辯證法的自在屬性被柏拉圖揭示了出來,而其自為特征則在亞氏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黑格爾則將自在與自為融為一體,將理念理解為自我異化和自我實現的過程,因而絕對精神的本性就是自由。
行文至此,我們簡要地回顧了馬克思之前的辯證法發展歷程,盡管僅選擇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爾作粗略考察,業已彰顯出辯證法在哲學史各階段所呈現出的基本樣式,以及前后相繼所形成的巨大鏈條。這根鏈條最終在黑格爾那里得到了最為清晰最為體系化的表達,貌似發展完善,但它卻在黑格爾逝世后的幾年內,轟然坍塌,為一個時代劃上了句號,也為新的時代開啟了序幕。
二、辯證法的革命:主詞—謂詞的顛倒
辯證法在觀念論者那里獲得了類似于生命的形式:獨立自持、自在自為,以自身為目的、起點和終點,全部過程都是為了自我實現。然而這里的生命卻不是真實的生命,而是生命在概念世界中的倒影。倒影與真實之間的差異,隱約地暴露出觀念論式辯證法的根本問題:以概念世界取代真實的現象世界,現象成為理念自我實現的附庸。拯救現象的任務并未真正完成。
1831年黑格爾溘然離世后,他的學說迅速陷入爭議的泥沼,首先崩潰的是宗教神學。1835年出版的《耶穌傳》揭開了論戰的序幕。大衛·施特勞斯受黑格爾啟發,把宗教的起源回溯至世俗僧侶生活,后者則植根于絕對精神。鮑威爾則提出,宗教產生于自我意識而非絕對精神。費爾巴哈敏銳地發現,“自我意識”與“絕對精神”之爭,其實質是理念與人之間的主次問題。對于黑格爾來說,人不過是絕對精神的中介,絕對精神通過人的行動把自身實現出來,因而,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絕對精神是無可爭議的主詞,而人、自然、宗教、國家等等皆為謂詞。費爾巴哈認為,辯證法的主體是現實的人,而意識、理念、宗教、國家等等皆為謂詞。哲學不應該從無限的、抽象的、普遍的絕對精神開始,而應從有限的、具體的、特定的感性生命開始[6](P115)。顯然,費爾巴哈已經找到了能夠撬動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支點,那就是顛倒絕對精神與人的主謂關系。費爾巴哈的上述觀點在《關于哲學改革的臨時綱要》(簡稱《剛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此文的發表把青年黑格爾派運動導向一個全新的領域,從宗教批判推進到顛覆黑格爾概念辯證法體系,同時還催生了馬克思的一部重要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簡稱《批判》)。
《批判》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大概創作于1843年3月中至9月底之間,其間馬克思曾認真研讀了費爾巴哈的《綱要》③。《批判》全文是以評注式文體寫成,批判對象限于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涉及國家哲學的部分。在1843年9月馬克思致盧格的信中,馬克思寫道:“意識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認清本身的意識,使它從對于自身的迷夢中驚醒過來,向它說明它自己的行動。我們的全部意圖只能是使宗教問題和政治問題具有自覺的人的形態,像費爾巴哈在批判宗教時所做的那樣”[7](P12)。它向我們明確傳達了以下信息:第一,馬克思已全面接受了費爾巴哈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方法;第二,批判必須超出宗教走向政治。
《法哲學原理》是黑格爾關于客觀精神的解釋,其中涉及法、道德和倫理,而倫理實體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馬克思找到的爆破點是國家學說。黑格爾從自然法(Natur Recht)傳統出發,將自由意志視為政治哲學的核心,個人和政治建制都是自由意志的實現工具,其中,國家作為整體高于個人。因而,他認為國家代表最高級的倫理實體,是自由意志在公共生活中的展現,也是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統一。馬克思運用費爾巴哈提供的工具,對上述思想展開了猛烈的批判。他認為黑格爾誤解了政治哲學的對象,“觀念變成了主體,而家庭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現實的關系被理解為觀念的內在想象活動。家庭和市民社會都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活動著的;而在思辨的思維中這一切卻是顛倒的”[8](P10)。顯然,馬克思認為家庭和市民社會是構成國家的基礎,而非自由意志,思辨哲學顛倒了主詞和謂詞的關系。國家的性質不能從抽象觀念中得到規定,相反,應從具體的社會群體中得到理解,這個思想后來就發展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辯證法。
后來馬克思又為這部手稿寫了一個導言,即《〈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寫于1843年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之間,1844年2月發表于《德法年鑒》。文中重復了上述觀點,并且回顧了此前的宗教批判,將其視為一切批判的前提。馬克思還指出了后觀念論辯證法的基本任務:“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想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于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8](P200)顯然,馬克思并未廢除辯證法,而是否定了辯證法在觀念論的用法。彼岸世界的“真理性”被戳穿后,辯證法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起關于現實的人的科學理論,馬克思將其稱為“人的最高本質”的研究。由此,辯證法才真正走出概念世界,進入現實生活,從“拯救現象”轉向“人的解放”。
三、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確立:人的解放
如果說《批判》是馬克思式唯物辯證法的初啼之作,那更為成熟的思想則表達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簡稱《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簡稱《形態》)。《手稿》的哲學史意義毋庸多言,我們在這里僅取與辯證法密切相關的兩個方面展開簡要討論:辯證法的起點和辯證發展圖式。
在《德法年鑒》期間,馬克思已經開始意識到,辯證法走出觀念論之后,首要的問題是如何切入現實生活。在完成了國家哲學批判之后,馬克思認識到政治經濟學是不可回避的問題領域,因而在巴黎期間他有意識地閱讀了大量的經濟學文獻。不同于國民經濟學家,馬克思并不將其視為一類專門知識,而是將經濟關系視為現實生活的基本構架,對現實的人的理解必須深入到經濟事實之中,才能得到準確的把握。辯證法擺脫純粹概念的糾纏之后,敏銳地選擇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現實生活的切入點。
馬克思受費爾巴哈的影響,將人理解為類存在物,人擁有類本質,這個類本質就是自由自覺的生產活動。勞動對于人類而言,并不僅是獲得生活資料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創造生命意義的過程。“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象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9](P97)顯然,馬克思把勞動等同于人的類本質,這里的勞動指的是有意識的自由活動。在澄清了本真的勞動之后,異化勞動的概念便呼之欲出了。所謂異化勞動,指的是喪失自主性的勞動,也就是剝奪生命意義的勞動。異化勞動的直接產物就是不平等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的感性體現就是私有財產。由此,馬克思將國民經濟學普遍承認的前提——私有財產,成功地證明為異化勞動的產物,它產生于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這一證明對于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辯證法史具有重大意義,它是辯證法用于現實生活的一次成功實驗。
基于上述異化勞動學說,馬克思在《手稿》中提供了一幅辯證歷史圖像:本真勞動——異化勞動——克服異化。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和歷史的運動有著明確的目標,這個目標不是由精神或其自由意志設定的,而是朝向類本質的全面實現,這個目標被稱為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因此,歷史的全部運動,既是這種共產主義的現實的產生活動即它的經驗存在的誕生活動,同時,對它的能思維的意識說來,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認識到的生成運動。”[9](P120)
綜上所述,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一種以“自由勞動”為核心的歷史辯證法,他揚棄了黑格爾思辨哲學中的純粹概念,保留其合理內核,改造為作為人的異化、人的認識和人的實現的勞動。
接下來,讓我們轉向《德意志意識形態》。同前面兩部手稿一樣,《形態》也是未刊稿,其中所蘊藏的哲學思想的豐富性無與倫比,堪稱馬克思哲學文獻中最重要的作品。下面我們僅就其中的物質生產辯證法單獨進行考察。
縱觀“費爾巴哈”章,馬克思關于人的研究從抽象的類本質深入到現實生活。因而在這里,辯證法的起點是具體的物質生活需要。馬克思以個體生命持存為出發點展開論述,將生活實踐的目的首先理解為基本欲望的滿足。需要的滿足過程同時也是新需要的生產過程,因而,物質生產過程同時也就是需要升級和需要擴張的過程。人類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必須聯合行動,并結成各種交往關系,這些基于生產而形成的交往關系總和就是市民社會。在生產的邏輯中,最后被制造出來的是意識,也就是說,意識是物質生產活動和市民社會的結果。但在腦體分工的條件下,意識同時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并反過來限制、支配物質生產和市民社會。最后,物質生產的發展必定會突破意識的束縛,借助社會革命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新型市民社會。人類歷史便是在上述辯證過程中不斷發展的。到此為止,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已得到基本闡明,“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規律也被揭示了出來。因而《形態》當之無愧地被認定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誕生地。
最后,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形態》辯證法的歷史目的。馬克思在《形態》中也將人類歷史的內在目的稱為共產主義。但這里的共產主義表述與《手稿》中的有所不同。在《手稿》中,馬克思主要從類本質的復歸、自主勞動的實現以及全面的人道主義等角度對共產主義加以描繪。但在《形態》中,共產主義被賦予“生產力解放”的新特征。馬克思將生產力定義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的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10](P80)。生產力作為共同活動方式,體現為一種社會力量。從表面上看,《手稿》與《形態》中的共產主義大相徑庭,后者更像是一種生產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形態,與自由勞動并無直接關系。但仔細考察文本,我們發現二者之間存在內在聯系。“各個人必須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總和,……對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質生產工具相適應的個人才能的發揮。僅僅因為這個緣故,對生產工具一定總和的占有,也就是個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總和的發揮。……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10](P129)“只有在這個階段上(注:共產主義),自主活動才同物質生活一致起來,而這又是同各個人向完全的個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相適應的。”[10](P130)上述引文明確地指出,所謂的生產力解放也就意味著勞動者對于生產工具的高效使用,這種高效并不取決于技術的提高,而是指勞動者可以更為充分地發揮個人才能,因而,生產力解放實質上也是勞動的自由解放,同樣也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的解放。到此為止,我們在《手稿》與《形態》中的兩種歷史目的間建立起了聯系。這個聯系告訴我們,從《手稿》到《形態》的辯證法發展,并非像很多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存在著跳躍和斷裂④。相反,后者進一步發揮了《手稿》中的共產主義思想,將自主性勞動的主題深化,提出生產力解放學說。而生產力解放所指向的正是人的解放,從這個角度來說,兩個文本中的歷史目的是一致的。
四、小 結
我們在本文中簡要回顧了辯證法發展的兩大階段,一是觀念論式辯證法,它最終完成在黑格爾思辨哲學體系中;另一個則是唯物辯證法,它肇始于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其基本方式是顛倒該體系中的主詞和謂詞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曾經出現過許多種不同種類的主詞:費爾巴哈選擇的是個人、類、感性生活等等;馬克思在《批判》中討論人,在《手稿》中討論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自覺勞動,而在《形態》中則討論社會化物質生產。從上述主詞的變化中,我們可以梳理出青年馬克思辯證法思想的發展軌跡,這條軌跡的基本導向是“人的解放”。
注 釋:
① 汪子嵩先生在《柏拉圖談辯證法》中詳細追溯了柏拉圖在不同思想階段中的辯證法。參見汪子嵩著.亞里士多德·理性·自由[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
② 上述思想主要體現在《智者篇》、《菲利布篇》和《巴門尼德篇》中,尤其是后者,被黑格爾奉為古典辯證法思想的最高峰。
③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顯然是一個未完成的手稿,文章多處提到“留待日后詳談”,而且對《法哲學原理》的評注僅限于第261至313節,此后的內容戛然而止。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致費爾巴哈的信中談到,要重新加工整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并已經就具體問題(如國民公會史)展開工作,準備完成該書后把它付印,《德法年鑒》停刊后,馬克思逐漸放棄了這一計劃。
④ 頗具代表性的是阿爾都塞和廣松涉的斷裂學說,他們從不同角度論證了《手稿》與《形態》的差異,忽視了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
[1]柏拉圖.理想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文德爾班.古代哲學史[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3]汪子嵩.希臘哲學史: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俞吾金.從康德到馬克思[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5]黑格爾.小邏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6]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From Phenomenon Salvation to Man’s Liberation——On the Status and Role of Dialectics in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UN Yun-long
(History Depart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This study gives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fundamental mode of dialect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ancient Greece,and the several important patterns of Idealistic Dialec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as well as its ultimate definition in Hegelism.This is to reconstruc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enesis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of the young Marx,so as to reveal clearly in which sense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is the reversion of Idealistic Dialectics,which underlines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This paper traces different demonstrations of dialectics in Marx’searly philosophicalwritings, including CritiqueofHegel’sPhilosophy ofRight, Economic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The conclusion part focuses on the dialectic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in German Ideology,provi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alectics in Marxism.
dialectics;historical materialism;man’s Liberation
B03
A
1000-2529(2011)05-0053-04
2011-05-25
孫云龍(1976-),男,山東青島人,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哲學博士。
(責任編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