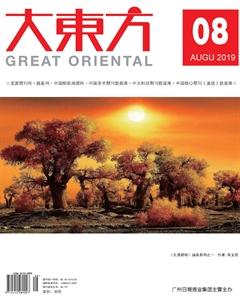藝術設計方法研究報告
侯文靜



摘 要:通過對西春街鍋爐房附近問卷調查,科學研究等方式,研究得出應該保持居民區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根據實際需求,設計出一種“萬能圈”方案,使其在社區生活中,一方面發揮環境作用,同時對于周圍居民學習元素提供機會。
關鍵詞:吸附罩;環境治理;可視化;科技化;可持續發展
1.引言
目前,由于北方取暖的需求,大量鍋爐房仍然存在于人們的生活周邊,且政府雖然一直在積極的出臺政策,予以補助,但似乎只是改變了上層的空氣,地面所存在的黑色垃圾仍然不能消解和利用,由于煤的特殊組成和特殊的地位,致使在利用煤的任一環節中,即使采用了多項先進繁榮技術,都不能確保環境不被污染。這注定我們要長久、持續的探討新技術的三廢排放,及治理技術,在最徹底的利用煤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好生態環境,尤其是用煤周邊的街道環境,做到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此次主要針對大連市西春街予以重點設計研究。
2.關于煤渣和煤炭污染
我國的能源開發和利用,尤其是以煤炭為主的能源供應,支撐了經濟的高速發展,與此同時,中國也面臨著嚴峻的資源及環境挑戰。而煤炭消費全過程與水資源緊密相關,水資源不僅受到煤炭消費全過程的顯著影響。
在消費煤炭的過程中,不能忽視的一個方面就是在運煤的過程中,撒掉的煤渣,給周邊帶來的深刻影響,比如路面,以及流過路面,和著煤渣的水流。
3.針對煤渣國家及地區給出的政策及規定
主要方面:1.關掉煤場;2.換掉燃煤鍋爐,改變為清潔能源鍋爐;3.禁止拉煤車輛運行;4.予以取締煤場;
從以上整改措施中看到,只是在徹底的關閉煤場,或者去使用其他能源的鍋爐來進行代替,這樣的措施無疑給很多商人,和國家造成了不便,因此,如何在不損害國家稅收和礦主利益的情況下,進行設計,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4.現狀
目前針對鍋爐燒煤渣和環境問題,大連市主要方式是將燃煤鍋爐拆除,或者使用清潔能源,并且對其進行資金補助的方法,但燃煤的鍋爐地區,要求原料應進行苫蓋,因此西春街的鍋爐房雖然使用的是煤渣進行供暖,但是進行苫蓋(如圖2),符合大連市政府的要求。
而政府的要求似乎只是滿足環境要求最低限,仍然忽略了在卸煤渣的過程中,對地面、路面和周邊水流造成的危害,在過程中造成的到處漆黑一片,一抹一手黑的現狀被人忽視,也對周圍的居民生活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4.1現狀調查(對人的影響)
調查顯示(居民區20人接受調查)
(1)對其產生的影響力大小 ? ? ? ? ? ?(2)對現狀的滿意程度
(3)不滿意的方面 ? ? ? ? ? ? ? ? ? ?(4)希望如何改進
4.2 煤渣所含元素及污染情況
5.設計方案
因此本次設計是在滿足了大連市政府的要求下,更加深入,并且更加符合可持續發展這一要求。方案主要解決由于燃燒鍋爐而使用的煤渣對環境造成的危害,以及進行科普等功能的產品及技術設計。
5.1設計靈感
此次設計的靈感來自于---《西游記》中孫悟空的“萬能保護圈”,孫悟空為保護師傅的安全,每次在走之前將其師傅劃定在一范圍之內,保護師傅的安全,此次涉及也由于此,為了保護環境的“真善美”從而將假惡丑關在圈里,關在罩里,并且使其“自生自滅,但又使其自身發揚光大”。
5.2設計構思
通過對西春街的實地考qa察,發現由于鍋爐燃燒煤,導致煤渣在此處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不僅在后期燃燒過后冒出的氣體,不可忽視的是他同時對周圍的路面、水流、人群、大氣等造成污染,但是一方面成為弊端的同時,也成為了優勢,所以在設計過程中,變廢為寶,將其再次利用并且搜集,運用到其他的領域,在還給自己周圍一個干凈的環境之時,讓其他人也能深受其益。
5.3理論模型
5.4具體設計及模型展示
在這個圈上的罩可以顯示出目前所卸載的物品的化學及組成物質信息,也就是說罩為一個可視化屏幕(如下圖)。同時在圈內的人也并不會感受到憋悶、不透氣,因為在其中罩的結構實際為小的見方透氣方格,其材質則運用為可以吸收其煤渣物質的材料吸附劑,并且為保證地面的清潔性,也采用靜電等科技,使其與地面不相接觸,最終都吸附在方格罩上,更好的保持了地面的清潔性。并且在罩的清洗方面,實際上是采用的一種菌類的自繁衍生物,將其植入方格內部,出現剩渣時,將剩渣“吃”入自己體內,一方面,增加生物多樣性,另一方面,也保持了罩的清潔性。因此,采用這些技術,使得不管是吸附罩,還是地面都保持了一定的清潔性。
在這樣的設計下,體現出了整個設計的可視化,可參與性,公開性和多樣性等的特點。
5.5實施步驟
6.總結
通過針對性的吸附,從而達到對資源的不浪費;通過對煤渣的可視化引導,使得人們能更直觀的看到其用途,增加科普性;通過對地面靜電科技的采用,讓地面更加的清潔,還周圍居民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
此次設計,還可運用到其他省市的運煤車輛行徑中,以及在煤礦卸載,裝載煤渣的過程中。比如山西煤炭大省。
同時通過此次設計構思過程,還可以將其運用到其他的各行各業中,比如在污水處理的過程等各種對環境造成危害,但是將其利用,又可發揮重大作用的物質,并且與人密切相關的區域之下。
(作者單位:大連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