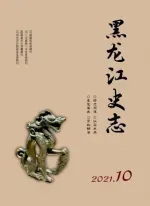館藏漢代銅鏡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研究
吳 鵬
(營(yíng)口市博物館 遼寧 營(yíng)口 115000)
銅鏡在我國(guó)古代有著悠久的歷史。銅鏡的制作和使用在兩漢時(shí)期形成第一個(gè)發(fā)展的高峰。漢代的銅鏡鑄造技術(shù)精良,類型多樣,鏡背紋飾精美,銘文內(nèi)容豐富,在中國(guó)古代銅鏡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漢代銅鏡蘊(yùn)藏著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和歷史信息,成為一種研究社會(huì)歷史和文化的重要遺產(chǎn)。
一、兩件館藏漢代銅鏡簡(jiǎn)介
營(yíng)口市博物館收藏有兩件漢代銅鏡,一件是東漢“宜子孫”鳳鳥紋銅鏡,一件是西漢連弧銘文銅鏡。東漢“宜子孫”鳳鳥紋銅鏡(公元25-220年),直徑14.5厘米,厚0.5厘米。出土于蓋州市九壟地東達(dá)營(yíng)村。圓形,大圓鈕,圓鈕座。鏡背由內(nèi)到外被凸弦紋分為七個(gè)區(qū):一區(qū)鑄“宜子孫”三字篆書銘文,間隔八個(gè)乳丁紋及云氣紋;二區(qū)飾一周短線紋;三區(qū)飾一周((()))形飾紋;四區(qū)飾六個(gè)乳丁紋間以六組鳳鳥紋;五區(qū)飾一周短線紋;六區(qū)為一周鋸齒紋;七區(qū)飾一周云氣紋,三角棱式外緣。此鏡做工精湛,紋飾精美,是東漢銅鏡中的佳品。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了營(yíng)口地區(qū)在漢代政治經(jīng)濟(jì)的繁榮狀況。

圖1 東漢“宜子孫”鳳鳥紋銅鏡
西漢連弧銘文銅鏡(公元前206-公元25年),直徑8厘米,圓形,圓鈕,圓座。鏡背由內(nèi)到外共分五區(qū),內(nèi)區(qū)飾八連弧紋,中間為銘文帶,鑄“見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篆書銘文,銘文之間以谷紋和菱形紋飾間隔。第二區(qū)和第四區(qū)為凸弦紋間以斜短線紋裝飾。此鏡主要流行于漢武帝后期至王莽時(shí)期。

圖2 西漢連弧銘文銅鏡
二、館藏漢鏡歷史文化內(nèi)涵研究
(一)館藏漢鏡所反映出的漢代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政治狀況
漢代在我國(guó)古代史中是一個(gè)國(guó)力較為強(qiáng)盛的時(shí)期,尤其是漢武帝時(shí)期經(jīng)過(guò)文景之治、修養(yǎng)生息后,國(guó)力恢復(fù),掃平匈奴形成“犯強(qiáng)漢者,雖遠(yuǎn)必誅”的雄強(qiáng)國(guó)家。同時(shí),為了對(duì)外交流,開辟了絲綢之路,使國(guó)力強(qiáng)盛程度達(dá)到了漢代的頂點(diǎn)。這一時(shí)期的銅鏡在中國(guó)銅鏡史上最突出的特點(diǎn)就是:厚厚的邊沿,凸起的銘文顯示出恢弘的氣度,透射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兇悍之氣,凜然而不可侵犯。帶有巖巖泰山之氣象和堅(jiān)實(shí)的存在感,彰顯出漢代強(qiáng)盛的國(guó)力。
此外,在漢鏡的銘文中,或明或暗地反映出一些史實(shí),把它們一概說(shuō)成是祈求富貴享樂或贊美銅鏡質(zhì)量之義是不妥的,原因是沒有考慮到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背景的緣故。例如,營(yíng)口市博物館收藏的西漢連弧銘文銅鏡鑄有“見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銘文,文義很容易被理解成祈求光明的未來(lái),其實(shí)不然。“見”即“現(xiàn)”。《廣韻》:“現(xiàn),俗見字。”師古訓(xùn)為“顯示”、“顯露”、“彰顯”等義。“日”,《廣雅·訓(xùn)詁一》日:“君也。”《續(xù)漢書·五行志》:“日者,大陽(yáng)之精,人君之象。”可見“日”自古以來(lái)就是最高統(tǒng)治者的尊稱,在漢代這個(gè)尊稱只有皇帝才有資格用。因此可知“見日之光,天下大明”的本義應(yīng)是彰顯皇帝之光,使之無(wú)所隱蔽的照耀天下;以此隱喻加強(qiáng)皇權(quán)。為什么要提出這么一個(gè)口號(hào)呢?自然是由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政治背景決定的。漢初,劉邦消滅異姓諸侯后,分封同姓為王,作為漢室藩屏。這些諸侯王各懷異心,不把皇帝放在眼中,乃至圖謀不軌,先后有濟(jì)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zhǎng)、吳王濞謀反。面對(duì)這一局面,漢政府實(shí)行削藩加強(qiáng)中央集權(quán)成為當(dāng)務(wù)之急。到景帝時(shí)晁錯(cuò)就明確地提出了削藩措施,然而這一建議實(shí)施不久便引發(fā)了吳楚七國(guó)之亂,導(dǎo)致矛盾的大爆發(fā)。于是,“見日之光”鏡銘便出現(xiàn)在歷史的舞臺(tái)上。
(二)館藏漢鏡所反映出的漢代人圓中有圓的審美觀念
古銅鏡基本制式為“圓”,應(yīng)與古代哲學(xué)觀有一定聯(lián)系:《周髀算經(jīng)》“天圓如張蓋”的“蓋天說(shuō)”之外,“圓”作為一種民族審美心理的基礎(chǔ),被推到重要的歷史地位,以至世間萬(wàn)物皆系于圓。銅鏡藝術(shù)更不例外,有無(wú)圓不成鏡之說(shuō)。“圓”作為一種幾何圖形,具有很好的對(duì)稱性,圓滿、流暢、周而復(fù)始、整體性強(qiáng),以一種旋轉(zhuǎn)律動(dòng)的翩然形式使銅鏡的造型更加豐滿,彰顯出萬(wàn)千氣象。漢代古銅鏡的鏡形基本上也是以圓形為主,其形制多數(shù)為圓中有圓,即與中心的鏡鈕構(gòu)成同心圓的基本格局,利用多層同心圓把鏡身分割成有節(jié)奏變化的多重空間群,按照需要將紋飾和銘文分別安排于各層圓環(huán)帶中。因此,漢鏡雖然尺寸不大,有著構(gòu)圖上的局限,但是圓中有圓的同心圓鏡形仍能體現(xiàn)設(shè)計(jì)者的無(wú)限遐想。這種同心圓分割的方式是漢鏡紋飾構(gòu)圖一大特色。它使得漢鏡雖然在各圓環(huán)帶中的紋飾構(gòu)成變化各異,但同心圓的造型風(fēng)格的一致性又能把它們統(tǒng)一起來(lái),充滿著和諧美。如營(yíng)口市博物館收藏的西漢連弧銘文銅鏡,圍繞中心圓形鏡鈕共有五個(gè)圓形。館藏的東漢“宜子孫”鳳鳥紋銅鏡,一共有九個(gè)大小不同奏鳴曲般的同心圓,既蘊(yùn)“九天”之意,又諧“長(zhǎng)久”之音。意在表現(xiàn)宇宙周而復(fù)始.無(wú)窮無(wú)盡。漢鏡以“圓”為基本設(shè)計(jì)元素,展現(xiàn)出時(shí)間的無(wú)極和空間的無(wú)阻,體現(xiàn)了漢代人對(duì)“圓滿無(wú)缺”境界的刻意追求。這種古老的審美觀加之“天人合一說(shuō)”宇宙觀的影響,致使?jié)h代銅鏡紋飾的這種圓中有圓的同心圓結(jié)構(gòu),蘊(yùn)含了豐富的哲理和品味不盡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
(三)館藏漢鏡所反映出的漢代人的家族觀念
漢代地主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較快,人們的家庭觀念的不斷加強(qiáng),他們力求上進(jìn),對(duì)生活充滿希望,對(duì)家族興旺、子孫蕃昌、升宮發(fā)財(cái)、富貴享樂的追求也十分強(qiáng)烈。一部分鏡子的銘文表明,在漢代銅鏡可作為女子陪嫁物,是身份地位和財(cái)富的象征。人們對(duì)銅鏡也寄予了對(duì)未來(lái)生活的美好祝福。子嗣問題,在古代是關(guān)乎宗族的命運(yùn)的大事。
如營(yíng)口市博物館收藏的東漢“宜子孫”鳳鳥紋銅鏡上“宜子孫”三字就是保佑家族興旺、子孫蕃昌的意思。出處于封建時(shí)代的兩漢時(shí)期,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對(duì)早婚、早育、早立子嗣都是十分關(guān)心的。漢武帝婚后,一直沒有得子,這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直至得子,武帝欣喜若狂,專門舉辦了規(guī)模宏大的慶祝活動(dòng)。在民間也是如此,恒譚在《新論.辯惑》中把“子孫眾多”列入“五福”之中。漢代人強(qiáng)烈的家族觀念在漢代銅鏡銘文中有大量的體現(xiàn),如“宜子孫”“長(zhǎng)宜子孫”、“長(zhǎng)生宜子”、“周復(fù)始兮八子十二孫”、“七子八孫居中央,夫妻相保如威兮”等等。如此之類,都表現(xiàn)出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家庭齊全美滿,上有父母,下有子孫,夫妻相伴相守是最幸福美滿,觀地反映了漢代人希望家族興旺,子孫蕃昌的家庭觀念。
(四)館藏漢鏡所反映出的漢代人的求仙思想
漢代的企求成仙的思想十分盛行。據(jù)《史記》和《漢書》的記載,從漢武帝到貴族官僚、地主、商人,企求成仙的思想十分嚴(yán)重。漢武帝與秦始皇一樣,企求成仙,至死不改。結(jié)果各種藝術(shù)品中均有神仙形象的出現(xiàn),從銅器、漆器到玉器的紋飾,都少不了神仙形象。到西漢后期鳳凰作為特有的神鳥,就頻繁與西王母相伴隨,并成為通向仙界的向?qū)В跔I(yíng)口市博物館收藏的“宜子孫”銅鏡上就鑄有鳳鳥紋。據(jù)說(shuō)鳳是由鳥的變異而來(lái),是一種長(zhǎng)著華麗羽毛與頭冠的理想神鳥。所以,鳳被尊為鳥中之王,是祥瑞的象征。傳說(shuō)商的始祖是玄鳥,商部族的圖騰是鳳。此外,鳳鳥也被人們當(dāng)作是風(fēng)神被崇拜。《說(shuō)文》亦稱鳳鳥“過(guò)昆侖,飲礫柱,灌羽弱水”,可見鳳鳥與西王母所在的西方世界是緊密相連的。西王母,作為一位不死仙藥的擁有者,有著與黃帝地位,當(dāng)然應(yīng)該有鳳凰的擁戴。相應(yīng)的,鳳鳥也受到了人們的推崇膜拜。在營(yíng)口市博物館收藏的“宜子孫”銅鏡上除了鑄有鳳鳥紋外,還鑄有云氣紋。所謂云氣紋即用多變的弧狀曲線來(lái)表現(xiàn)的云朵形狀,在云朵后面拖出一條氣狀的尾巴,所以稱作“云氣紋”。由于在漢代人們向往仙人披霞飲露、列子御風(fēng)而行的境界,所以,云氣紋在漢鏡中的出現(xiàn)正與漢代的求仙思想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總之,由于漢代銅鏡式樣豐富、工藝精湛、紋飾精美,使之成為中國(guó)古代工藝美術(shù)之瑰寶。同時(shí),通過(guò)漢代銅鏡精美的紋飾、銘文集中體現(xiàn)了漢代的經(jīng)濟(jì)政治狀況、人們的審美和思想觀念等歷史文化內(nèi)涵,也使后人體會(huì)到銅鏡背后所蘊(yùn)涵的中華民族上升階段所產(chǎn)生的對(duì)新思想、新追求的熱情,形成了這個(gè)時(shí)期鮮明的特點(diǎn),從而,造就了漢代銅鏡在我國(guó)銅鏡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1]孫文麗.銅鏡銘文反映的王莽改制與歷史現(xiàn)實(shí)[J].理論界,2010,(9).
[2]吳俊.廣西出土漢代銅鏡銘文的研究[J].湖北社會(huì)科學(xué),2008,(1).
[3]王小芹.中國(guó)古代銅鏡中的瑰寶——漢鏡[J].文物世界2007,(3).
[4]顧薇薇.漢鏡銘文研究.復(fù)旦大學(xué)學(xué)位論文,2004.
[5]彭亞麗,靳庚金.浙江古銅鏡裝飾紋樣藝術(shù)內(nèi)蘊(yùn)研究[J].美術(shù)大觀,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