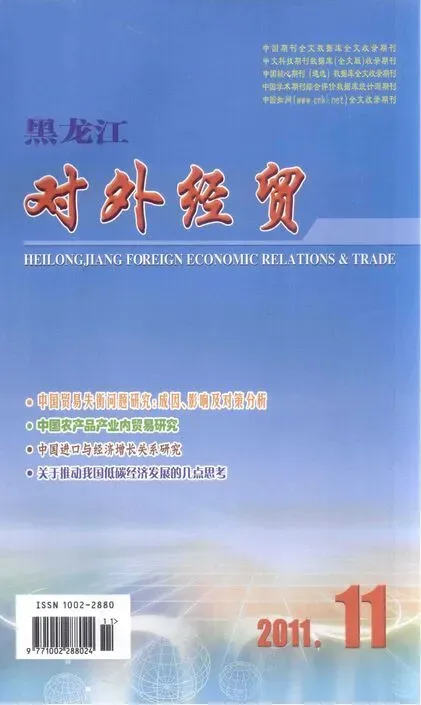中國碳排放長期趨勢及驅動因子分析
李 燕
(浙江工商大學 經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自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加導致大氣中CO2等溫室氣體濃度不斷升高,被認為是地球變暖的根本原因。2003年英國第一次提出了“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后,各國都將低碳經濟視為21世紀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我國政府在2009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提出:立足國情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把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長期任務,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這一決議表明我國已經把降低碳排放,發展低碳經濟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
二、文獻回顧
(一)碳排放和經濟增長長期趨勢研究
Schmalensee(1998)和 Galetti等(1999)驗證了 CO2排放量與人均收入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胡初枝等(2008)基于我國1990—2005年碳排放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運用庫茲涅茨曲線(EKC)模型,得出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呈“N”型關系。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9)研究發現,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碳排放的關系演化依次遵循著3個倒U型曲線規律。
(二)碳排放驅動因子研究
ZHANG(1998)最早采用對數差分方法分析中國1980—1997年碳排放增長,結果證明中國在節能減排中若沒有通過政策與技術手段降低能源強度,該階段的碳排放總量會比實際高50%。柴建等(2009)基于1992、1997、2002及2004年30部門能源投入產出表分析得出我國過去幾十年能源強度下降的主要動力來自于宏觀因素。朱勤等(2009)基于擴展的Kara恒等式建立因素分解模型,應用LMDI分解方法對能源消費碳排放進行因素分解,得出經濟產出效應對我國該階段能源消費碳排放的貢獻最大。以上的研究為碳排放驅動因子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不難發現上述分析更多地從經濟增長以及微觀結構的角度去分析碳排放因素。本文通過對碳排放和經濟增長長期趨勢分析,綜合考慮碳強度、能源強度、人口數量及碳排放效率等宏觀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進行協整、格蘭杰因果關系分析,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力求較為全面地反映各因素的動態作用并量化其貢獻率。
三、研究方法
Kara恒等式由日本教授Yoichi Kara于IPCC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是為了辨別碳強度、能源強度、經濟水平、人口數量哪種因子對碳排放影響最大。

式中:CO2、PE、GDP和POP分別代表 CO2排放量、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國內人口總量。
為了研究碳強度、能源強度、經濟水平、人口數量對碳排放的影響,筆者對Kara恒等式進行如下變換:

根據彈性的定義,碳強度、能源強度、經濟水平、人口數量每變化1%,分別引起碳排放總量變化α1%,α2%,α3%,α4%。
四、實證研究
(一)數據選擇和統計性描述
數據樣本為中國1978—2007年的年度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年鑒和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報告。沒選取1978年以前的數據是因為1978年以前我國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水平不高,能源存在嚴重浪費現象。1978年以后,我國市場經濟逐步開放,工農業迅速發展,能源消耗加快,碳排放量加速增長。

圖1 二氧化碳排放量(CO2)、人口(POP)、碳強度(CI)、能源強度(EF)、人均GDP(PG)、碳排放效率(CE)的增長率變化趨勢
(二)碳排放總量變動趨勢:“庫茲涅茲曲線”檢驗
前述文獻表明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碳排放和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但是對于中國的情況,不同的學者得出不同的結論。為了進一步檢驗我國碳排放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借鑒Galli的做法,建立碳排放與人均GDP之間的非線性模型:

其中CO2:二氧化碳排放量,PERGDP:人均GDP。由Eviews6.0計算得到以下結果:

表1 碳排放效率與人均GDP回歸結果
從表1中得出,人均GDP一次項系數顯著為正,在1%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二次項系數顯著為負,在1%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我國碳排放量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關系,結論與Schmalensee(1998)和Galetti等(1999)一致。
結合圖1,2002—2004年碳排放效率增長率為負,說明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惡化的趨勢。根據我國碳排放量特征分析,我國碳排放量的“拐點”在人均GDP非常高的位置,遠高于國外水平。說明我國在含碳能源利用上存在大量的粗放型消費。
(三)二氧化碳排放量(CO2),碳強度(CI),能源強度(EE),人均GDP(PG),人口(POP)協整性分析
自從Engle和Granger提出協整理論以來,就一直被認為是處理非平穩時間序列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波動的有力工具。在進行協整之前,先對數列進行平穩性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單階整數。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常用ADF檢驗:


表2 各變量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
由表2可知,CO2、EE、PG、POP及 CI為2階同階單整,滿足協整分析的條件。
本文用恩格爾和格蘭杰兩步法對協整關系進行檢驗和估計分析結果見表3。

表3 各時間序列之間協整檢驗
可知 lnCO2和 lnCI,lnEE,lnPG,lnPOP 存在協整關系,說明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碳強度、能源強度、人均GDP、人口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說明在長期這些因子對二氧化碳的排放存在一定的影響。
(四)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因果關系是變量之間的依賴性,原因變量的變化引起結果變量的變化。

表4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注:滯后期按照p值的最小值進行選擇。
表4顯示:惟獨lnPOP和lnCO2互為因果,說明人口和碳排放量之間具有相關性;lnCI是lnCO2的原因,這說明碳能源的消費結構對二氧化碳的排放存在影響;lnCO2是lnEE的原因,即二氧化碳的變化會改變能源強度;Ln-PG和lnCO2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即二氧化碳和人均GDP相互獨立,但是格蘭杰因果檢驗只是相互關系表示一個方面。綜上可知,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GDP(經濟增長)存在倒U曲線關系。
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除了人均GDP外,別的驅動因子對二氧化碳都有因果關系影響,由此可知我國碳排放驅動因子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提出節能減排政策建議提供依據。
(五)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Engle和Granger已經證明,如果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均衡誤差將顯著影響變量之間的短期動態關系。先建立長期均衡模型。

從模型來看,碳強度、能源強度、人均GDP、人口都對碳排放量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符合實際情況。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碳強度、能源強度、人均GDP、人口每變化1%,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變化0.80%、1.06%、0.97%、1.38%。對二氧化碳的影響:人口>能源強度>人均GDP>碳強度。
再建立短期均衡模型 lnCIt-1,lnEEt-1,lnPGt-1,ln-POPt-1無法通過t顯著性檢驗,舍去。通過顯著性檢驗和擬合優度標準后得到以下模型:

從以上誤差修正模型來看,在短期內,碳強度、能源強度、人均GDP、人口都對碳排放量存在顯著的正影響。具體來說,在短期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碳強度、能源強度、人均GDP、人口每變動1%,CO2平均變動1.02%,1.03%,0.99%和1.19%。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人口>能源強度>碳強度>人均GDP。相對于長期而言,短期碳強度的影響比人均GDP影響更大。誤差修正項ECM的系數大小反映了短期對偏離產期均衡的調整程度。由模型可知,誤差修正系數為負,滿足反向調整的事實。上一期短期對于上期均衡的偏離,將在本期得到32.89%的調整,說明在宏觀調控下,我國每年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調整力度適中。
五、研究結論及建議
上述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與人均GDP存在“能源庫茲涅茲關系”,說明隨著經濟增長,我國碳排放總量經過“拐點”后會逐年下降。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碳排放量與人口數量存在互為因果關系,碳排放量的變化是能源強度變化的原因,是碳強度變化的結果。碳排放驅動因子長期均衡和短期誤差修正模型表明無論長期還是短期,對于我國碳排放影響最大的兩個因素是人口數量和能源強度,碳排放和人口數量在長期和短期內影響大小不同,長期人均GDP影響更強,短期則碳強度占優。由誤差修正項可知碳排放量短期對長期均衡的偏離有32.89%得到調整,說明我國在二氧化碳排放宏觀調控產生的成效一般。從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看,人均GDP對碳排放的彈性系數較大,表明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高投入、高能源消耗的產業拉動。據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從低碳生產來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與能源強度彈性系數約為1,說明提高能源效率,能同比例減少我國碳排放量。能源強度主要受到產業結構、市場化程度和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做到降低生產的碳排放量,首先應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經濟轉型,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入。其次應積極推進市場化改革,制定有效的碳權交易市場機制,利用價格機制提高碳排放效率。同時還應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提高清潔能源對碳能源的替代率,減少我國碳排放總量。第二,從低碳生活來看,碳強度因子在短期相對于長期效果較為明顯,這說明在短期內碳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升級會有效降低碳排放量。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城市化、機動化的大力推進,生活碳排放將進入快速增長期。政府應倡導低碳消費理念、引導低碳生活方式,建立起一種以低碳為導向的共生型消費方式。構建低碳消費生活方式關鍵是消費結構低碳化,減少城鎮居民生活的碳密集行為,實現由高碳消費向低碳消費的轉變。通過低碳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引導低碳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降低我國的碳排放量。第三,從控制人口增長來看,在我國碳排放驅動因子分析中,人口因素影響最為顯著。我國本來人口基數就大,人口數量微小的變動,都會引起能源需求、碳排放量的巨大變動,人口數量對碳排放量的影響具有長期滯后效應。所以從長期來看,積極有效控制人口增長,能減少我國碳排放量,減輕能源供求壓力,有利于低碳經濟的發展。
[1]Keeling C D,Whorf T P,Wahlen M,.Inter annual ex-tremens in the rate of rise of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since[J].Nature,1995,375:666-670.
[2]孫敬水.中級計量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