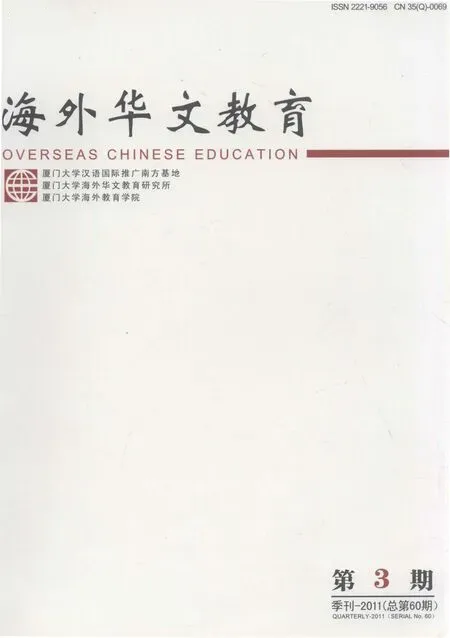論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組織
寇志暉,張善培
(1.香港中文大學雅禮語文研習所;2.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中國 香港999077)
一、前 言
李泉(2006)認為,對外漢語教學應該結合教學模式的設計和研究、結合漢語漢字的特點、結合不同的教學對象及其漢語學習需求、乃至于結合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進行漢語教學等,來進一步研究漢語作為外語教學的課程設置及其內在相互關系的研究。(李泉,2006年:14)漢語國際化教育的發展和推廣,亦要求對外漢語教學的專家和學者在關注漢語語言本體研究(字、詞、句等)的同時也關注相應的課程、大綱和教學模式。李泉(2006)還指出,課程規范的提出和研究對教學實踐有著重要的、直接的指導作用。筆者認為,對外漢語課程的規范具體涉及課程、教學過程等的設計,也涉及合理組織和安排對外漢語教學中各項因素,使之達至合理化教學,從而提高教學質量。其中,漢語教學不同階段的課程組織及其組織取向,應為對外漢語教學發展的關注點之一。
課程設計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需要構思不同的課程要素,并將它們組織在一起成為一個連貫的系統。(張善培,2004:29)課程組織并非單一而是復雜的決定和執行過程,基于不同的課程取向,課程便有相應的組織,以達至所欲的課程目標。(林智中等 ,2006:44)張善培(2004)認為,課程設計者的課程取向是一組信念(beliefs),影響課程目標、內容、教學法和評量的設計。課程設計大致可分為五種取向:學術取向、認知過程取向、社會取向、人文取向、科技取向。張善培(2004)以科學課程為背景說明了課程組織各種取向的特征。筆者將之應用到對外漢語教學之中,認為就漢語課程組織而言,與之相關的應為學術取向、認知過程取向、社會取向和人文取向。
衡量學生交際范圍的大小、言語技能和水平等級的高低,都是根據不同的教學階段而言的,在不同的教學階段我們的教學目標也就相應地有所不同。(陳昌來,2005:123)因此,要對各個課程進行科學合理的安排,其中重要的一環還包括對各課程的教學階段進行科學合理的組織和規劃。因此,我們有必要關注對外漢語教學課程不同學習階段的課程組織形式和取向。筆者將以所執教的不同學習階段的漢語課程(初級、中級等)為例,考察其不同學習階段的漢語課程組織形式和取向的差異。本文將嘗試回答兩個問題:(一)對外漢語教學的主要課程取向是什么?(二)不同教學階段的課程取向有何不同?
對以上問題的探討和論述,有助于對外漢語課程人員和教師在設計和組織不同類型和級別的漢語課程時,能使用確切的、相應的課程組織取向,使漢語課程的各個教學要素更有機地結合起來,利于教學的實施并有效地達到教學目的,同時滿足對外漢語的各項教學原則的要求。(趙金銘,2008)此外,對所實施課程之組織取向的了解,也有助于了解和對比課程人員和任課教師的課程設計的信念,從而為學生創造更有利的學習條件。(張善培,2004:30;林智中等,2006:44)
二、文獻與分析
(一)課程組織的組織原則
李子建、黃顯華(2002)基于課程組織的分類為何,原則為何,課程取向和課程組織形式的關系為何等三個問題,探討了課程組織的性質和基本概念。他們指出,課程組織分為垂直組織(vertical organization)和水平組織(horizontal organization)兩種。垂直組織是指課程或教材的先后關系,水平組織指的是課程或教材相互間的關系。
課程組織的共同要素中,以繼續性(continuity)、順序性(sequence)和統整性(integration)的概念發展得最早。由于課程的不斷發展,課程組織的要素也有一定的更新,除了以上沿用的要素外,還有范疇(scope)、銜接性(articulation)和均衡性(balance)等。(林智中等,2006:8)
總結專家學者(李子建等,2002;林智中等,2006)對課程組織五項組織原則所列述的要點,可見繼續性指的對課程中包含的主要因素的直線式的重復敘述;順序性是指學習經驗的逐層深入;統整性指的是指課程各因素的橫向聯系,將所學重點加以統一、連貫并應用;銜接性則是課程不同階段之間的相關性和連續性,教學過程中應關注學生的個性差異和特征,使其順利過渡課程的不同階段,獲得更有效的學習;課程組織的范疇則是課程內容的范圍,也指該課程的深度和廣度。對外漢語教學界也有專家和學者(崔永華,2008;陳昌來,2005)從課程組織的角度探討了漢語課程設計和組織的特征,分析和描述漢語課程及教材編寫的組織方式和編寫。
(二)對外漢語課程組織的取向
張善培(2004)指出,就校本課程發展而言,教師的課程取向會嚴重影響校本課程質素。教師的課程設計信念、教師的教學行為和教師為學生選取的學習活動有著緊密的關系。根據張善培(2000a、2000b)的觀點,課程取向是指決定學校課程意圖、內容、組織、教學法和評估策略的信念系統(黃素蘭等,2002:138)。就課程組織的不同取向林智中等(2006)有以下闡述:認知發展的課程是以學生的認知發展過程為主的課程組織,重在發展學生的認知能力,重視學習的過程而非教學的內容;(林智中等,2006:31)人本主義課程主張以培養個人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及“自我引領”(self-directed)為課程的關鍵,相信人的內在潛力和自發的學習動機,一旦啟動了這些動力,便會自動地走向完善之路。(林智中等,2006:32)
基于對外漢語教學的特點和教學原則,筆者認為其課程組織應涉及四個取向:學術、認知、人文和社會取向。劉珣(2010)指出,語言教學中當然包含一定的語言知識和語言規律的教學。筆者認為,對外漢語教學課程組織的學術取向涉及漢字、語音、語法等語言本體的學習內容;對外漢語教學的認知取向關注的是語言學習的過程。語言習得的認知因素主要包括智力、學能、學習策略和交際策略以及認知方式;(劉珣,2010:210)社會取向在漢語學習中應體現為學校、社會等對學生漢語學習結果的要求,即社會、文化、專業考核(如漢語水平測試等)對學生的語言水平及其使用等的具體要求。劉珣(2010)論及語言學習的環境時論述了社會環境對目的語學習的影響。他認為社會環境為學習者提供了自然習得目的語及相關文化因素的社會背景,也提供了運用目的語進行交際并獲得反饋的真實活動場景;(劉珣,2010:227-228)崔永華(2008)在探討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習理論時提到人本主義學習理論,論述了學生個人參與、自發性、學生自我評價自己的學習等因素的重要性。本文所提及的人文取向即人本主義取向主要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設計和教學過程,即所實施的教學內容、方法等,都是照顧學生語言學習的背景和學習差異的,同時也是關注學生的學習興趣、工作及生活的實際需要的。如是,就對外漢語教學而言,語言學習的過程就是一個發展學生語言習得的認知過程。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動力對語言的習得過程都有很大的影響。社會的需要和發展對學生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要求也在不斷地改變,學校和教學機構在課程組織上也要有相應的安排。
(三)從不同層面分析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組織
1.基于課程類型的分析
趙金銘(2008)指出,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類型實際上是指課程內容的性質或課程功能,包含課程和課型兩個不同層次。主要有以下幾個類型:(1)綜合課;(2)專項技能課;(3)專項目標課;(4)語言知識課;(5)翻譯課;(6)其它課程。趙金銘(2008)對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設置的論述,實際上也是從課程組織的層面進行的。他總結了三個要點:(1)對外漢語教學具有明顯的課程整合性特點。大多數的教學形式均以漢語綜合課為主干核心,以專項技能課為重點,采用分技能設課的方式。各課程之間具有較明顯的橫向聯系。(2)對外漢語教學也體現出螺旋式組合的順序性特點,重復課程內容并逐漸擴大范圍和加深程度,照顧語言學習和認知的特點。(3)對外漢語也注重課程內容的直線性連續性,尤其是一些知識類課程,在不同的教學階段組成邏輯上的前后聯系的直線,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復。
筆者認為對應于課程組織取向來看,以上三個要點主要是針對學術取向(漢語語言知識)和認知取向(照顧認知的特點)下的課程組織的論述,主要是對不同的漢語課型在這兩個組織取向下的教學安排的分析。有鑒于此,課程設計者在設計同一學習階段的不同課程類型的漢語課時,需要有統整的概念,注意課與課之間的橫向聯系,在教學內容和難度上要關注持續和遞增的需要。以筆者執教的初級漢語課為例,包括口語聽力課和詞匯語法課兩門課。學生需要同時修讀這兩門平行課。這兩門課使用的教材在詞匯、語言點的量和難度上都是相若的。教學進度的設計也是同步的。只是練習和測試的形式存在注重聽說和讀寫的分別。這兩門課是相輔相成、互相支持和影響的。教學的設計和組織者對不同課型在橫向聯系和縱向發展上的關注,有利于教學的實施并實現教學目標。
2.基于教學內容及其組織方式的分析
傳統上一般把語言教學內容分為兩大類: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崔永華2008:70)《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列述了對外漢語教學的五級目標和內容。其學習內容包括語言知識(語音、字詞、語法、功能、話題、語篇等)、語言技能(綜合技能、聽、說、讀、寫)、策略(情感策略、學習策略、交際策略、資源策略、跨學科策略等)、文化意識(文化知識、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識、國際視野等)。崔永華(2008)基于教學內容組織編排的兩種主張“螺旋式”和“直線式”,探討了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組織。筆者對之進行總結并分析其所對應的課程組織取向(見表1)。

表1 對外漢語教學“螺旋式”、“直線式”課程組織及其取向
由此可見,對外漢語教學課程除了漢語語言形式之外,在對待交際、文化、功能等課程教學內容的組織和設計上亦需遵從螺旋、循環式的規則。在照顧學生認知能力的情況下,逐步提高對學生漢語習得和交際水平的要求。
3.基于不同教學階段課程組織的分析
陳昌來(2005)提到了對外漢語教學過程論。就教學過程來看,對外漢語是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過程,而不僅僅單指課程教學活動(陳昌來,2005,頁84)。在探討對外漢語教學階段論時他引述了泰勒(Tyler)指出的“任何科學的教學過程都必須具有連續性(continuity)、順序性(sequence)和整合性(integration)”,并且從這三個方面對對外漢語教學進行了分析。那么,對外漢語的不同學習階段(如:初級漢語、中級漢語和高級漢語)的課程組織有何不同呢?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學內容包括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語用、漢字等要素及相關的文化知識,以及使用漢語的技能。這些內容被分成不同的等級,最后被落實到相應的教學階段。(陳昌來,2005)
一般來說,對外漢語不同教學階段教學內容的組織都會體現出語言形式上的遞增和文化背景上的深化。初級課程多為綜合形式的基礎課程教學,較注重語言形式的習得,越往高級,對專項課目和文化背景的兼顧越顯重要。相應地,對交際范圍和交際能力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組織取向主要涉及學術取向、人文取向、認知取向和社會取向。
對外漢語不同階段的教學內容顯示出對漢語語言知識的掌握和應用是逐步加深的。初、中、高三個階段的教學原則基本上是相同的,體現出不同教學階段都將注重“學生中心”的教學原則。不同階段都對學生的交際能力和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提出了要求。不同階段的課程組織取向也都分別涉及學術取向、人文取向、認知取向和社會取向。筆者認為,在對外漢語教學的三個不同教學階段中,課程組織的四個取向的側重點將是不同的。筆者假設,就對外漢語教學而言,初級階段是對漢語語言知識的初步了解和積累,對學習者的交際及社會參與能力的要求相對較低,其課程組織的社會取向相對較弱,主要涉及學術取向、人文取向、認知取向的等。以此類推,隨著語言知識的不斷積累和交際能力的提高,中、高級階段課程組織在兼顧學術取向、認知取向和人文取向的同時,其社會取向也應越發顯得重要。
三、總結與探討
(一)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組織和取向
對外漢語教學在語言知識教學的組織上是直線式結合螺旋式的排列,是由淺至深的組織安排。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組織具有直線性、順序性和整合性的特征。漢語語言知識(字、詞、句、語法等)明顯地是按照由淺至深的直線性排列,具有連續性;對外漢語教學也體現出螺旋式組合的順序性特點,要求已學習內容的復現率。在重復課程內容的同時逐漸擴大學習范圍并加深程度;對外漢語教學課程以綜合性課程(語音、語法、功能、文化等)為核心,其它專項技能(聽、說、讀、寫)和專業范疇(商貿、新聞等)為重點,在此組織形式下融會貫通,課程具有明顯的整合性特征;對外漢語教學的范疇涉及漢語語言知識、語言技能、文化等等。隨著漢語學習程度和級別的增加,學習內容的深度也相應增加。因此,筆者認為,相應的課程組織取向也會隨著學習階段和漢語語言水平的的遞增而有所調整。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組織具有學術、認知、人文等組織取向,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不同教學階段中所存在的社會取向。
劉珣(2010)指出,以需求分析而論,要深入了解社會對學習者的需求和學習者本身的需求。社會的需求主要表現在對學習者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的要求。(劉珣,2010:299)因此,筆者認為,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組織,尤其是在中、高級漢語課程中,結合社會取向的設計是課程組織趨向綜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不同教學階段的課程取向存在差異
對外漢語總教學原則包括:以學生為中心;以交際能力的培養為核心;以結構、功能、文化相結合為框架等原則。(趙金銘,2008:100-103)筆者認為,對外漢語的課程組織形式和取向也應基于這些原則將漢語教學的各個要素有機地結合起來,并有效地達到教學目的。結合文獻回顧及自身漢語教學的經驗,筆者認為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組織取向會因不同的學習程度、學習階段、教學目標和內容而有所不同。如:初級漢語的課程組織偏向學術、認知等取向,中、高級則更注重人文、社會取向與學術、認知取向的結合。不同教學目的和不同內容的課程,如商貿、文化與交際等中高級普通話課程,也會由于本身的學習內容和程度的不同,而在課程組織取向上各有側重。
筆者嘗試對一些所執教課程的組織形式、組織取向進行分析,考察現有的對外漢語之課程組織及取向定位。將以初級漢語課程和中級漢語課程為例,基于課程的四項組織原則進行對比和分析(見表2)。
四、結 論
目前,對外漢語教學的課程組織、取向和教學原則之間的配合還有一些不確定之處。比如說,對外漢語教學的各個階段都非常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這一教學原則,然而,初級階段的人文取向并未如專家期望那般得以表現。課堂教學還是“以教師為中心”。筆者認為,漢語語言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漢字、拼音、詞匯、語法等的特殊性),初級對外漢語教學過程中,學生的語言習得主要體現為記憶、模仿等認知過程,既定的基礎階段的教學內容,直接限制了對學習目標的認定。因此,相對來說,此階段課程組織中“人文取向”表現得并不明顯,這需要教師在課程組織和教學實施過程中進行平衡。例如實行教學法的多樣化,增加課堂互動等,結合學習者的不同背景,適當地增加“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元素。
從課程組織的角度來看,中、高級漢語教學具有教學內容豐富、教學范疇廣、統整性和實踐性強等特點,較偏重人文、認知和社會等課程組織取向,同時也適當配合學術取向。筆者認為,此階段學習者的漢語學習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基于不同的學習目標,學習者可以嘗試自學相關的漢語語言知識,教師也可以有的放矢地給予輔助和支持。學習者可以從課堂和社會兩個方面實現對漢語交際文化的學習和實踐。教師給予的支持也在于課堂教學法的多樣化,基于社會對漢語學習者的要
求和考核方式設計教學內容并輔以適當的教學法。另外,社會性的語言實踐取決于學生所處的語言環境以及學生對語言實踐的主動性。

表2 對外漢語教學初級、中級課程組織及其取向比較
筆者認為,漢語教學在不同階段所體現的課程組織取向不同,越高級階段的漢語教學越注重課程組織的人文和社會取向。然而,學生差異、教師對課程組織信念的差異等都會對課程組織的形式和取向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因此,在課程設計和實施中,我們在遵循一般的課程組織形式和取向的基礎上,還要兼顧學生和教師自身兩個因素。另外,課程組織取向也不應是單一的,應該呈現綜合性的趨勢,需要根據客觀條件的不同而對各種取向有所側重。這需要從事對外漢語的教學單位、教師等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根據自身的課程目標和特點,依據課程組織原則,結合對外漢語教學原則,對課程做出適當的定位。在課程的組織安排方面也需要做出適當的統籌和安排。
陳昌來:《對外漢語教學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崔永華:《對外漢語教學設計導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8年。
黃素蘭、張善培:《香港美術科教師的課程取向》,《教育研究學報》2002年第17卷第1期,香港:香港教育研究學會。
黃政杰:《課程設計》,臺北:五南出版社,1991年。
李泉:《對外漢語課程》、《大綱與教學模式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李子建、黃顯華:《課程范式、取向和設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2年第2版。
林智中、陳健生、張爽:《課程組織》,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年。
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0年。
楊龍立:《課程組織原則之探討》,《編譯館館刊》32卷第1期,臺北,2004年。
張善培:《課程取向的再概念化》,邁向課程新紀元(十七):第六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臺北:教材研究發展學會編印,2004年。
趙金銘主編:《對外漢語教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周小兵、李海鷗等:《對外漢語教學入門》,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
Cheung,D.Measuring teachers’meta-orientations to curriculum:Application of hierarchica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68(2),149-165.2000a.
Cheung,D.Analyzing the Hong Kong junior secondary science syllabus using the conceptof curriculum orientations.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15(1),67-94.2000b.
Cheung,D.& Ng,P.H.Science teachers'beliefs about curriculum design.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30(4):357-375.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