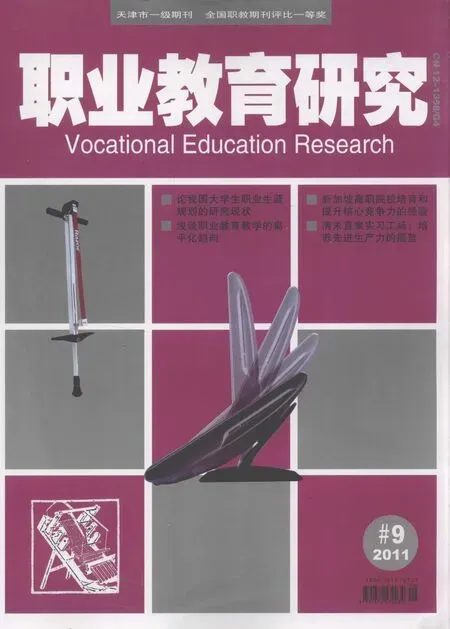對TOPRA模型的實證研究
丁潔(天津現代職業技術學院 天津 300222)
對TOPRA模型的實證研究
丁潔
(天津現代職業技術學院 天津 300222)
以60名高職學生為研究對象,在語義加工與非語義加工兩種條件下進行新英語單詞學習的實驗。研究結果表明:學習者對第二語言新詞匯語義的深層加工對其學習詞匯的結構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這種負面作用在短期和長期內都存在。實驗結果支持Barcroft提出的“資源加工類型的分配(TOPRA)”模型一說。
TOPRA模型;詞匯學習;結構加工;語義加工
語義加工是指在對一項語言輸入的加工過程中,大腦的加工資源定向于對其意義特征的深入分析與加工。比如寫出英語單詞happy的近意詞,或用lazy造句,都是不同形式的語義加工任務。與語義加工相對應的是結構加工,如指出intelligent中有幾個元音字母。語義學習是指學習那些結構已知詞匯的新意義,如學習第一語言中已知詞匯的新意義;而結構學習是指對那些已知其意義但未掌握其結構的詞匯的學習,如學習第二語言中的新單詞。
認知心理學家從信息加工的角度就詞匯學習與語義加工之間的關系進行大量研究。這些研究結果顯示:人類的信息加工系統與一般信息加工系統一樣,其內部存在各種各樣用于加工外界信息的資源,這些資源在數量上是有限的。這種資源上的有限性導致人們注意分配上的有限性。當兩個或多個任務同時被操作的情況下,會造成系統對有限資源的競爭(Miller,1956;Broadhent,1958;Wickens,1984)。
語義加工與詞匯學習研究綜述
Craik和Lockhart以第一語言中的已知詞匯為實驗材料進行研究,并提出 “加工水平說 (levels of processing,LOP theory)”。其實驗結果表明:語義加工促進詞匯的學習。LOP學說認為:“作用于人的刺激要經受一系列不同水平的分析,從表淺的感覺分析開始,到較深、較復雜的抽象分析和語義分析。加工深度愈深,則有愈多的認知加工和語義加工。語義的任務要比語音、結構的任務更能使加工達到更深的水平;記憶痕跡的持久性是加工深度的直接函數。那些受到深入分析參與精細聯想的信息產生較強的記憶痕跡,并持續較長的時間,而那些只受到表淺分析的信息則產生較弱的記憶痕跡,并持續較短的時間。”支持加工水平說的還有Reitman和Bower,Schulaman,Craik和Tulving,Rogers等人。
其他學者以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中的新詞匯為實驗材料研究語義加工與詞匯學習之間的關系,得出不同的實驗結果。其中,支持語義加工對新詞匯結構學習具有促進作用的有Crist 和Petrone,Coomber,Ramstad和Sheets,Brown和Perry等人;認為語義加工對新詞匯結構學習沒有顯著性作用的有Pressley,Levin和Miller,Levin,Pressley等人;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語義加工對新詞匯結構學習具有阻礙作用,如Pressley,Levin和Miller,Prince,Barcroft等人。
Morris,Bransford和 Franks曾提出“遷移適當加工(transfer appropriate processing,TAP)效應”,認為“一項側重于語義加工的任務會促進學習者在側重于檢測語義知識的測試中的表現,而一項側重于結構加工的任務則會促進其在側重于檢測結構知識的測試中的表現。即測試任務的本質與加工任務的性質(語義、語音、結構)一致時,學習效果更好。”
語言學家VanPatten根據人腦加工資源有限這一前提,指出“當第二語言作為一項輸入被大腦加工時,學習者對其意義的加工與對其結構的加工成反比例關系。”
Barcroft在TAP效應以及VanPatten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資源加工類型的分配(TOPRA)”模型。此模型詳細闡述了語義加工、結構加工與詞匯學習之間的關系。TOPRA模型指出:“對詞匯語義加工的增強,會促進對該詞匯的語義特征的學習,與此同時降低對該詞匯結構特征的學習效果”。如圖1所示,外邊界的兩條粗線不可移動,表明學習者大腦中可用來加工外界信息的資源是有限的。對學習者來說,對一項詞匯輸入既要加工它的語義,同時又要加工它的結構,是非常困難的。當學習者對某一項詞匯輸入的語義加工增強時,圖中央的分隔線就會向右偏移,與此同時降低對該詞匯結構特征的學習效果。反之,當學習者對某一項詞匯輸入的結構加工增強時,圖中央的分隔線會向左偏移,與此同時降低對該詞匯語義特征的學習效果。

圖1 資源加工類型的分配模型圖
研究方法和工具
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母語為漢語、第二語言為英語的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新詞匯時是否支持“資源加工類型的分配”模型。實驗采用“造句法”作為語義加工任務,著重討論以下兩個問題:(1)語義加工是否會對學習第二語言新詞匯的結構產生一定影響?(2)這種影響是否長期存在?
研究對象 本實驗選取某高職學院一年級的學生60名(男30名,女30名)作為被試對象。所有被試滿足以下條件:(1)被試的母語是漢語。(2)被試對除漢語以外的其他語言沒有較高水平的掌握。(3)被試的第二語言是英語,不使用英語進行日常交流。(4)被試基本屬于中等偏下水平的英語學習者。
實驗設計 在本實驗中,被試分為兩組,每組30人。對實驗單詞采用兩種呈現順序。被試組一采用呈現順序一,他們在學習實驗單詞(1~12)時,用每個單詞完成一項造句任務;在學習實驗單詞(13~24)時,觀看四遍實驗單詞的拼寫及其對應的圖片。被試組二采用呈現順序二。在學習實驗單詞(1~12)時,觀看四遍實驗單詞的拼寫及其對應的圖片;在學習實驗單詞(13~24)時,用每個單詞完成一項造句任務。刺激結束后,對被試進行四次測試(立即測試、兩天后測試、一星期后測試和一個月后測試)。測試結果將根據“音節評分法”進行評分,運用SPSS軟件對數據進行方差分析。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實驗單詞的呈現時間和次數。為了使實驗操作在現實的第二語言學習條件下進行,在“+造句”和“-造句”兩種條件下實驗單詞所呈現的時間和次數是不同的。在“+造句”條件下,每個實驗單詞的圖片及其拼寫在被試面前呈現一次,持續48秒,被試要在48秒內完成一項造句任務。而在“-造句”條件下,每個實驗單詞的圖片及其拼寫在被試面前呈現4次,每次持續6秒。
實驗字表 24個實驗單詞是根據以下標準選取的:(1)實驗單詞必須是實意名詞,能夠用圖片的形式明確地將其意義表現出來。(2)被試在實驗前不認識這些單詞。為了最大限度減小實驗字組I(1~12)和實驗字組II(13~24)之間的難度差異,兩個實驗字組中單詞的長度、音節數目都保持一致。分別選取2個單音節、8個雙音節和2個三音節單詞作為實驗單詞。
測試結果評估 測試結果將通過“音節評分法”進行評分。如“umbrella”這個單詞,寫出 “um”得1分,寫出“umbre”得2分,完整寫出 “umbrella”得3分。評分結束后,對實驗字組I和實驗字組II的得分分別進行總分合計,然后對“+造句”和“-造句”兩種條件下的成績分別進行總分合計。
數據收集與分析 對測試成績運用SPSS軟件進行方差分析。其中學習條件和測試時間為自變量,音節評分成績為因變量。值設為.05。從表1可以看出:在本實驗的四次測試中,在“-造句”條件下學習的單詞的平均分明顯高于在“+造句”條件下的得分。總體來說,“-造句”條件下所學習的單詞的平均分是8.61分,而在“+造句”條件下學習的單詞的平均分是4.07分。表2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總體來說,在“+造句”和“-造句”兩種條件下的學習效果具有顯著性差異[F(1,472)=134.02,P<.001]。

表1 兩種學習條件下的平均得分表

表2 以學習條件為變量的方差分析表
實驗結果還表明,盡管隨著時間推移,被試對實驗單詞有一定程度的遺忘,但在不同學習條件下詞匯學習效果的顯著性差異依然存在(見圖2)。
研究結論
用第二語言的新單詞造句這種語義加工活動對學習者學習新單詞的結構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并且這種負面作用在短期和長期內都會存在 從認知心理學信息加工的角度來分析,人腦可用于加工外界信息的資源是有限的,當一個學習者正在對新單詞的結構進行編碼時,一項涉及較多語義加工的活動迫使學習者把加工資源分配給定向于語義加工的任務。這種語義加工的任務耗費了較多的加工資源,大腦中就剩下相對較少的資源供學習者去加工這個單詞的結構。實驗結果支持TOPRA模型(Barcroft,2000),因為“造句法”這種涉及大量語義加工的活動降低了學習者對新單詞結構的學習效果。

圖2 “+造句”和“-造句”條件下學習詞匯的差異圖
本研究的結果不完全支持“加工水平說(levels of processing,LOP theory)” 因為當實驗單詞為第二語言的新詞匯時,“造句法”這種被認為是深層語義加工的任務并沒有比不造句這種淺層語義加工的任務產生更好的記憶效果。
小結
第二語言學習者應該認識到,當我們的大腦對某一個新單詞輸入進行加工時,大腦中可供加工這個單詞的資源是有限的,對新單詞語義的加工會消耗對新單詞結構加工的資源,從而降低學習詞匯結構的效果(如對新單詞的拼寫)。因此,明確某一階段的詞匯學習目標尤為重要,即學習者是要記住新單詞的意義還是新單詞的結構,并根據詞匯學習目標設計相應的加工活動來增強詞匯記憶的效果。
許多語言教師在LOP學說的影響下普遍認為深層的語義加工活動必然會產生更好的學習效果。然而,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事實并非總是如此。語言教師在評價一項語言加工任務對于詞匯學習的效果時,應該區分是針對詞匯結構的學習還是針對詞匯意義的學習。
[1]Barcroft J.Processing Resources and L2 Lexical Acquisition in Three Writing Tasks [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1999,(5).
[2]Craik F I M,Lockhart R S.Levels of Processing:A Framework for Memory Research [J].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72,(11).
[3]Morris C D.Bransford,J.D.and Franks,J.J.Levels of Processing vs.TransferAppropriate Processing [J].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77,(16).
[4]VanPattern B.Attending to Content and Form in the Input[J].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90,(12).
[5]Wickens C D.Varieties of Attention [M].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4.
[6]卜元.影響英語單詞記憶效果的三因素[J].外語與外語教學,1992,(5).
[7]陳琦.當代教育心理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8]陳曉湘,羅京鵬.負極詞的極端敏感性及允準條件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5,(4).
[9]桂詩春.新編心理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10]汪安圣.認知心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G712
A
1672-5727(2011)09-0016-02
丁潔(1977—),女,陜西漢中人,碩士,天津現代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應用語言學與英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