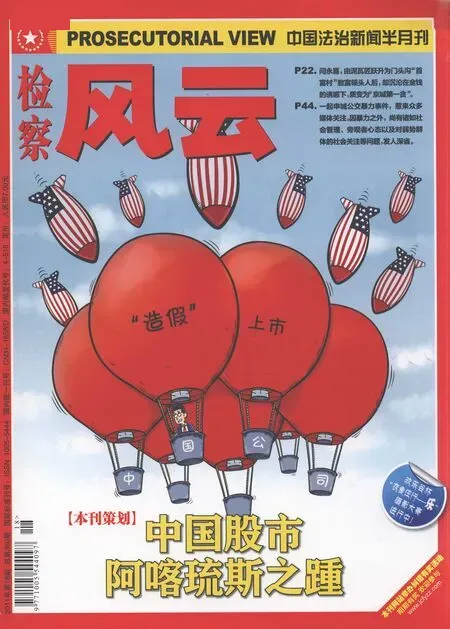申城公交暴力襲擊案偵查始末
攝影/曹 參 文/成 韻
申城公交暴力襲擊案偵查始末
攝影/曹 參 文/成 韻
“當乘客們意識到危險已經遠去,便不愿再陷入另一種危險狀態了。”但是我們應該相信,無論是誰不愿伸手,抑或是誰猶豫不決,這個社會始終存在一股力量,不驕不躁,不餒不棄,只為完成一種名為“責任”或“正義”的東西。
正義感并非與生俱來,需正面引導和倡行
毆打事件發生后,不少媒體登載了相關新聞報道,字里行間不乏對車上乘客袖手旁觀的痛心和憤怒。在這些報道中,突出點很明確,即在毆打司機的“血色3分鐘”里,車上后部座位上中青年男子約占一半,卻沒有一個伸出援手,而整車唯一上前勸阻的老年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車上有40多名乘客,沒一個人站出來阻止,那個光頭(打人者)才越來越囂張……”116路女司機周衛琴在接受一些媒體采訪時,圍著頸托躺在病床上嘆氣。
2011年6月,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陳衛國等探望和慰問了正在住院接受治療的周衛琴,對其在遭受暴力時,為保全車上乘客安全而采取的第一時間停車行為,表示贊揚和敬佩。并且,寶山區人民檢察院還多次聯系公安機關,希望找到在錄像中看到的一直勸阻施暴者的那位老伯,對其面對危險仍堅持化解糾紛、伸張正義的行為予以表揚和嘉獎。
陳衛國副檢察長對本刊記者說,“本案中那位上前制止、從旁勸阻的老伯,其行為弘揚了一種社會正氣,而且也是個體承擔救助風險的典型表現,因此,應當對他進行嘉獎。此外,在毆打行為結束后,撥打110報案之人,也應予以表揚和鼓勵,以正面宣揚幫助被害人的行為,希望對動員社會人士發揚正義感并采取各種相關行動起到正面積極的導向作用。”
可喜的是,近日,那位挺身而出的“呵斥伯”(媒體尊稱)已被好心人找到,74歲的老先生名為徐宗林,退休前曾是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員。每天,“呵斥伯”都會乘坐116路去護理院看老伴,那天,當他看到歹徒對女司機動手時,立即站起身來大聲阻止:“你不能打人的!”
日前,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已決定向徐老伯所在的江浦路街道眾和居委會發“檢察建議書”,建議表彰這種見義勇為的行為,并將擇日登門拜訪徐老伯。
8月10日,寶山區人民檢察院特邀法學家和社會學家對116路打人事件從法律和社會學的角度予以探討。其中,上海市社會學會副秘書長、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鐘汝解析了本案中乘客袖手旁觀的幾大原因。張教授認為,導致本案乘客不愿伸手救助的原因可大致分為三種:一種是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另一種是怕引火燒身。畢竟時下總有一些“好心沒好報,救人反遭殃”的負面新聞流傳,使得不少人心有余悸,從而對是否救助產生猶豫;而第三種則是看客心態,純粹湊個熱鬧。從該案發生時的錄像可以看到,在司機遭受毆打時,有不少路過的摩托車主停車圍觀,卻沒有一人支援或者報警,在沒有任何威脅輻射的情況下,這種看客心態和行為是最不道德的。

作案前后,沈博曾多次自傷,用煙頭灼燙手腕留下的傷痕。

犯罪嫌疑人沈博是一名抑郁癥患者
“而司機在遭遇危險時所表現的臨危不亂和當機立斷卻值得稱道。”張教授指出,“正是這種職業素養和責任意識,保障了車上乘客的安全。”遺憾的是,這也導致了乘客們在判斷危險遠離后,對與己無關的另一種危險狀態的主觀排斥和躲閃,從而影響了他們對正義救助的積極思考和參與。
不過,在被一些媒體問及“如果再遇到同樣情況,你會怎么做?”時,被害人周衛琴的話依然令人欣慰:“我還是把乘客安危放第一位,不管乘客愿不愿伸援手幫我。”
看來,我們應該相信,無論是誰不愿伸手,抑或是誰猶豫不決,這個社會始終存在一股力量,不驕不躁,不餒不棄,只為完成一種名為“責任”或是“正義”的東西。
案情一覽:
5月13日,一名二三十歲身材高大的男子乘上了116路公交車,他的打扮有點另類,黑色蝎子的圖案映在臉龐和手臂上。他本想于張華浜站下車,然因該車屬于116路高架車,不停靠張華浜站,引起男子沈博的不滿,對正在駕駛車輛的被害人周衛琴抽了一記耳光。周衛琴當機立斷,將車停在吳淞大橋下后,便遭到來自沈博的拳打腳踢,從車上打到車下,之后便揚長而去。
沈博的毆打行為導致周衛琴身上多處受傷,經上海市公安局損傷傷殘鑒定中心鑒定,構成輕傷。
而沈博在被逮捕后,經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司法鑒定中心鑒定,確認其為抑郁癥患者,屬“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范圍。
本案雖情節簡單,但由于在5月13日案發當天,116路公交車廂毆打錄像即在上海某電視臺播出,影響極為惡劣,市民要求嚴懲犯罪分子的呼聲高漲,甚至,針對此案該如何定罪都在網上引起了熱議。
寶山區人民檢察院承辦人員清楚知道該案所承載的輿論壓力,為此,從6月15日批捕犯罪嫌疑人沈博后,即從調查取證、犯罪定性到提起公訴、提出檢察建議等各個環節加固把關。
根據調取的幾段涉案監控錄像、犯罪嫌疑人沈博的供述、被害人周衛琴的陳述,以及多名目擊證人的證言等,寶山區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沈博的行為特征符合法律規定的“尋釁滋事罪”,并以此于8月11日向寶山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檢方認為,犯罪嫌疑人沈博實施毆打行為的起因、對象及方式均具有明顯的隨意性,最終造成一人輕傷的后果,符合尋釁滋事罪“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情形。而其因較小的理由對司機暴力相向,從車上打到車下的行為,盡顯其無視法規、恣意妄為的滋事故意,嚴重危害社會秩序。
然而,對于該案的定性,社會上出現了不同聲音,即認為犯罪嫌疑人沈博在行駛中的公交車上對控制車輛的駕駛員實施毆打,這已經使車上乘客置身危險,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條件。
對此,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劉憲權認為,由于女司機在受到攻擊后,迅即將車停在吳淞大橋下,使事件發展過程中,車輛處于停駛狀態,而毆打的主要行為也是在這段時間內發生的,“這樣,并不能引起導致危害公共安全后果的危險狀態出現,因此該案的犯罪行為不宜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更符合‘尋釁滋事罪’的犯罪特征。
鑒于犯罪嫌疑人具有抑郁癥患者(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的身份,劉教授指出,根據《刑法》第18條第3款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雖然看上去,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實施行為時的辨認控制能力并不低,但是畢竟他身患抑郁癥,屬于精神病患者,再考慮到他的到案表現和悔罪態度,可以對其從輕處罰,這也算合理,且符合法律規定。”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偵監處處長居廣鑒與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陳衛國探望病床上的女司機周衛琴(圖/寶檢提供)
關愛和寬容,請適時向弱勢群體開放
8月10日上午,《檢察風云》雜志社記者前往寶山區看守所對犯罪嫌疑人沈博進行采訪。審訊室的門被推開了,幾個人一前一后進入,為首的是女檢察官,排在最后進入的記者看到彈簧門正掃向自己,便準備出手推擋,此時,門卻停住了,記者抬頭,觸目可及的是一雙戴著鐐銬的手,點綴著深深淺淺的傷疤,這雙手的主人便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沈博。
“家里很臟很亂,看守所雖然許多人住一間,但是衛生打掃得很干凈,很干凈,家里母親生病,父親只管自己,生活也沒有什么秩序,不太想家。”當被記者問及“是否想家”時,沈博帶著茫然的表情緩緩開口,語氣中透出一種倦怠和疲憊。
而對于記者問到的家庭環境和成長經歷,沈博的回答顯得有點凌亂,仿佛沉浸在個人世界般自言自語,“父親住一間,我和母親一間,父親幾乎不管我,我也沒人說。”“朋友本來有,但很少,2003年辭職后就都不聯系了。”“我中考成績挺好的,不過想早點工作,為母親看病,就填了那個中專”“母親時好時壞,經常會和奶奶吵架,關系不好,家里很悶很亂。而且不能向母親提起讓她吃藥的事,她會翻臉。”
“從1998年有點懷疑自己……到2003年真正吃藥,晚了5年,拖得太久了……后來感覺好點就不吃了,而且怕被母親看到,不能讓她看到。”沈博的反應令記者覺得,也許采訪可以到此為止了。不過他手上深淺不一的大小傷疤卻令記者暗驚,“你手上的傷疤是怎么弄的?”“用煙燙的。”“打人前燙的?”“前后都有。”
“如今,類似的精神疾病、心理疾病患者犯案數量不少,而對這些弱勢群體的專業診療和心理疏導還太少而且不夠健全。”承辦該案的女檢察官如此說道。
在沈博被批捕后,考慮到其精神狀況,寶山區人民檢察院特意安排了一位“較有耐心且態度溫和”的女檢察官承辦此案,并讓一位具有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資格的檢察官參與審訊。該案的承辦女檢察官對記者表示,沈博“1998年發現自己有抑郁癥傾向后,先后跑了5家醫院看病,診斷的結論各不相同,從而延誤了治療;在毆打事件發生的前晚,他吃了母親給的另一種藥(精神疾病方面的藥)。”
毫無疑問,對沈博這樣一位毆打事件中的施害者,咬牙切齒的人有之,橫眉冷對的人有之,甚至,如果無需擔負法律責任的話,想要拳腳相向的人亦有之,盡管沈博已被專業機構鑒定為抑郁癥患者,屬“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控制能力”的“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但這不會改變他在人們心目中形成的毆打女司機的暴力形象。
不過恰恰是這樣一個人們眼中的“暴力分子”,卻在即將被起訴前,收到了一份他想都沒想過的“禮物”。“首先,被害人在了解了你的整體情況后,她已經從內心原諒你了,并且她說考慮到你的實際情況,不會提出過分的金額賠償要求。”聽到女檢察官認真地傳遞著這樣的信息,這個給人以“沉靜斯文”第一印象的犯罪嫌疑人低著頭,沉默不語。
當整起事件的唯一受害者,沈博暴力相向的源頭向他釋放了原諒,這種善意和寬容不啻為一種救贖,尤其是對弱勢群體而言。此時,我們作為旁觀的人群,不妨也放下責備,關注一下,聆聽一下:在這個社會的各處陰影中、許多角落里,是否正傳出一種聲音,郁郁寡歡的,渴望關懷的……
關注民眾訴求,社會管理應更人性化
其實,116路毆打事件除了涉及法律和社會學方面的一些問題外,還隱隱透出兩個社會管理方面的民眾訴求:一是對弱勢群體的長效援助機制應不斷完善;二是城市識別方面的便民元素需得到強化,并形成一種社會管理共識。
對于116路毆打事件所折射的社會管理層面問題,社會學教授張鐘汝直言不諱:“其實,從社會管理角度而言,精神上患有疾病的犯罪嫌疑人當屬社會弱勢群體,而如今,有類似疾病或者承受壓抑、郁悶等情緒又無處表達的心理亞健康者并不少見,此次的事件也該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加強在這方面的工作,關注這類對象,建立健全心理疏導渠道,這樣既能為這些需要關心者的心理健康提供積極導向,并且也可預防一些由于心理亞健康甚至精神疾病所引發的社會糾紛甚至刑事案件。”
《檢察風云》記者在此案研討會后,單獨訪問了張鐘汝教授。
記者:我們在采訪中注意到,犯罪嫌疑人長期處于較為壓抑、郁悶的狀態,而且無處宣泄,使其成為一顆不定時炸彈。如今戾氣爆發后的獲刑暴露了嫌疑人一直掩蓋較好的疾病問題,那么等他出獄后,該如何面對社會,他的家庭該如何面對鄰里,如果還是沒有合適的渠道為他提供幫助,而他和家庭又因疾病問題被鄰里躲避甚至孤立,那是否會加大犯罪嫌疑人內心的郁結以及不定時爆炸以致再次犯案的可能性?
張鐘汝:沒錯,確有這種可能。現在許多街道都設有社工組織等相關專業組織,一些諸如貧困階層、問題青少年、心理疾病患者等特定人群已被納入其長期關心和幫助的對象范圍。而像該案的沈博,待其刑滿釋放,回歸社會后,也應被作為這些相關組織的工作對象,對其就業、生活、病情發展等進行關注和跟進,這樣不論對他還是對社會都有積極的意義。
此外,對本案隱約有所牽連的城市識別問題,我們也希望通過報道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改進。
據了解,引發犯罪嫌疑人沈博不滿而揮拳的原因竟然只是他所乘的這輛116路公交車線路與其了解的有所出入,沒有其需要下車的站點。案發后,檢察機關查明:116路確有兩條行車線路,一條為地面車,標識為116;另一條為高架車,標識為116B。而這樣的區別卻并不顯示在一目了然的位置上,使得一些不經常搭乘的乘客產生錯認。從便于市民出行的角度出發,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對公交公司也提出了相應的口頭建議,希望能對此進行改善,便于市民出行辨識,避免不必要的口角和紛爭。
而對于城市識別方面的其他弊端,寶山區人民檢察院也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其中,該院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崔海龍提出:“在社會進步,城市發展的今天,城市標識已成為城市的名片,為便于市民出行,應強調易于辨識的圖案或文字,而非強調個性化、創意性等元素,比如現今男女廁所的標識沒有統一標準,女性廁所的標識從高跟鞋、裙子到娃娃圖案等分門別類,男性也各式各樣,固然能傳達一定趣意,但是其主體功能性的傳達則被削弱了,而這對市民的出行而言是極為不便的。”
不管怎樣,116公交車毆打事件能走到今天施害方悔罪,受害方原諒的地步,已經算是某種程度上的周全了,只是里面總有一些牽引我們心神的地方,比如在發生諸如此類的事情時,人們的袖手旁觀如何能進一步轉換為積極救助?
也許,張鐘汝教授提出的“風險分擔理論”能為我們醒醒神,即如果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面對緊急事件時采取邊觀望邊判斷的猶豫態度或者干脆袖手旁觀,這樣必將影響公共整體安全,最終這也會反過來投射到作為社會一份子的每一個人身上,由此,日趨上升的公共安全風險也將由每一個人來承擔……而事實上,誰都可能碰到需要別人援助的一天。
編輯:靳偉華 jinweihua101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