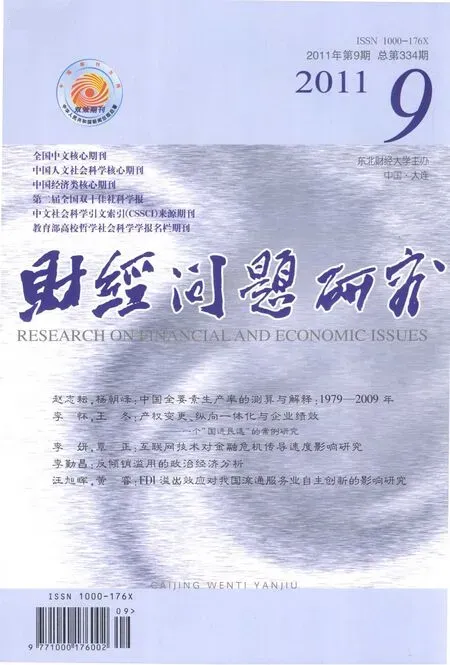中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測(cè)算與解釋:1979—2009年
趙志耘,楊朝峰
(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一、引 言
自從索洛提出全要素生產(chǎn)率概念以來,經(jīng)過不斷發(fā)展和擴(kuò)充,全要素生產(chǎn)率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問題最為流行的研究領(lǐng)域之一。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對(du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研究始于20世紀(jì)80年代初。Krugman認(rèn)為,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東亞新興工業(yè)化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zhǎng)主要是依靠大量使用資本和勞動(dòng),而不是依靠技術(shù)進(jìn)步的作用,并且這種投入驅(qū)動(dòng)的高速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是不可持續(xù)的[1]。Krugman對(duì)東亞增長(zhǎng)奇跡的質(zhì)疑以及1997年東南亞經(jīng)濟(jì)危機(jī)的爆發(fā),掀起了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對(du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和經(jīng)濟(jì)可持續(xù)增長(zhǎng)的研究熱潮。從研究對(duì)象上,大體可以把這些研究成果分為兩大部分:對(duì)區(qū)域經(jīng)濟(j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估算和對(duì)生產(chǎn)部門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估算。對(duì)區(qū)域經(jīng)濟(j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估算代表性的研究有張軍和施少華、樊綱和王小魯、顏鵬飛和王兵、郭慶旺和賈俊雪、鄭京海和胡鞍鋼、李賓和曾志雄等[2]-[7]。這些研究通過估算中國(guó)整體經(jīng)濟(jì)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和省際區(qū)域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來分析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源泉,判斷中國(guó)整體和區(qū)域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是否具有可持續(xù)性。還有一些研究是針對(duì)某一生產(chǎn)部門或者行業(yè)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估算,分析生產(chǎn)部門或者行業(yè)的技術(shù)進(jìn)步情況[8-9]。不可否認(rèn),這些研究對(duì)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的制定與調(diào)整都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但是我們也應(yīng)看到,國(guó)內(nèi)全要素生產(chǎn)率研究還存在一些薄弱環(huán)節(jié),即大部分研究關(guān)注的是全要素生產(chǎn)率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問題,而對(duì)于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構(gòu)成僅限于一些理論上的分析和分解 (如非參數(shù)方法可將全要素生產(chǎn)率分解為技術(shù)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缺少對(du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影響因素的實(shí)證分析。
本文試圖利用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改變以上的狀況,通過構(gòu)造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來衡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uó)經(jīng)濟(jì)體制的變遷,同時(shí)用R&D投入和國(guó)外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分別衡量自主創(chuàng)新和技術(shù)引進(jìn),對(du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進(jìn)行新的解釋,定量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變動(dòng)原因。
二、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測(cè)算方法
目前,對(du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測(cè)算主要有兩大類方法:參數(shù)方法和非參數(shù)方法。參數(shù)方法包括索羅殘差法、隱性變量法和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法。
1.索羅殘差法。Solow提出全要素生產(chǎn)率表示為產(chǎn)出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扣除勞動(dòng)和資本貢獻(xiàn)之后的余額[10]。設(shè)總量生產(chǎn)函數(shù)為C-D生產(chǎn)函數(shù):

其中,Yt為實(shí)際產(chǎn)出,Lt為勞動(dòng)投入,Kt為資本存量,α、β分別為平均資本產(chǎn)出份額和平均勞動(dòng)力產(chǎn)出份額。在規(guī)模收益不變和中性技術(shù)假設(shè)下,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zhǎng)率為:

為估計(jì)出平均資本產(chǎn)出份額和平均勞動(dòng)力產(chǎn)出份額,對(duì)方程 (1)兩邊同時(shí)取自然對(duì)數(shù)有:

在規(guī)模收益不變的約束條件α+β=1下有:

估計(jì)出平均資本產(chǎn)出份額α和平均勞動(dòng)力產(chǎn)出份額β后,帶入方程 (2)可以得到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
索洛殘差法避開了生產(chǎn)函數(shù)具體形式的討論,而關(guān)注函數(shù)的相關(guān)性質(zhì),使得基于這一模型的技術(shù)進(jìn)步度量方法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加之索洛殘差法計(jì)算方法簡(jiǎn)便、直觀,該模型實(shí)用性也很強(qiáng)。但索洛殘差法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在索洛模型中,技術(shù)進(jìn)步的貢獻(xiàn)只是產(chǎn)出增長(zhǎng)扣除勞動(dòng)力和資本貢獻(xiàn)份額之后的“余值”,該“余值”反映了任何導(dǎo)致生產(chǎn)函數(shù)變動(dòng)的因素。但是實(shí)際上,并非勞動(dòng)和資本兩種投入以外任何導(dǎo)致產(chǎn)出增加的因素都是技術(shù)進(jìn)步。由于索洛殘差所包含的因素過于寬泛,所以不能真實(shí)反映現(xiàn)實(shí)的技術(shù)進(jìn)步貢獻(xiàn),特別是對(duì)于中國(guó)這樣一個(gè)轉(zhuǎn)型經(jīng)濟(jì)更是如此。
2.隱性變量法。隱性變量法將全要素生產(chǎn)率看做為一個(gè)不可觀測(cè)的變量,在檢驗(yàn)數(shù)據(jù)平穩(wěn)性和協(xié)整性的基礎(chǔ)上,利用狀態(tài)空間模型做極大似然估計(jì)來估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采用C-D生產(chǎn)函數(shù),且假設(shè)規(guī)模收益不變,則有如下觀測(cè)方程:

式中,ln(TFPt)為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假設(shè)ln(TFPt)為一個(gè)隱性變量,且遵循一階自回歸即AR(1)過程,則有如下狀態(tài)方程:

其中,ρ為自回歸系數(shù),滿足|ρ|<1,ut為白噪聲。這樣,利用狀態(tài)空間模型,通過極大似然估計(jì)同時(shí)估算出觀測(cè)方程和狀態(tài)方程,從而得到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的估算值。
隱性變量法將全要素生產(chǎn)率看做一個(gè)獨(dú)立的狀態(tài)變量,并從殘差中分離出來,更為精確地估算了全要素生產(chǎn)率。但是,這種方法僅僅是從計(jì)量方法上對(duì)用最小二乘法估計(j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較小改進(jìn),在理論上仍然是建立在新古典基礎(chǔ)上的,仍然采用規(guī)模報(bào)酬不變假定和C-D生產(chǎn)函數(shù)形式。
3.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法。Fare等認(rèn)為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來源于投入要素增長(zhǎng)、技術(shù)進(jìn)步和技術(shù)效率提高[11]。這樣就等于把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分解為技術(shù)進(jìn)步率和技術(shù)效率兩部分。技術(shù)效率測(cè)度的是短期內(nèi)對(duì)現(xiàn)有生產(chǎn)能力的利用程度,反映的是現(xiàn)實(shí)經(jīng)濟(jì)的生產(chǎn)技術(shù)效率。技術(shù)進(jìn)步率是較長(zhǎng)期內(nèi)測(cè)算技術(shù)效率的參照物,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正是測(cè)度這個(gè)參照物的有用工具。因此,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法成為測(cè)度及分解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好方法。但它的缺點(diǎn)也很明顯,主要體現(xiàn)在它是建立在產(chǎn)出缺口估算基礎(chǔ)上,而無論用何種方法估算產(chǎn)出缺口,都會(huì)存在估算誤差,從而導(dǎo)致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估算偏差[12]。
估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非參數(shù)方法包括Malmquist指數(shù)方法和HMB指數(shù)方法。非參數(shù)方法要求樣本必須是面板數(shù)據(jù),不能對(duì)一個(gè)孤立的國(guó)家或地區(qū)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進(jìn)行測(cè)算,而我們的數(shù)據(jù)均為時(shí)間序列,因此,這種方法不適合我們的研究。我們的研究目的是測(cè)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并進(jìn)行解釋,要求測(cè)算出來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不含誤差項(xiàng),隱性變量法在測(cè)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時(shí)排除了誤差項(xiàng)的干擾,似乎比索洛殘差法更適合本文的研究,但經(jīng)過我們的實(shí)際測(cè)算后發(fā)現(xiàn),因?yàn)殡[性變量法假設(sh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zhǎng)率遵循一階自回歸,使得測(cè)算結(jié)果波動(dòng)很小 (幾乎就是一條水平線)。我們認(rèn)為,正是隱性變量法這個(gè)假設(shè)使得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動(dòng)的大量信息被“平滑掉了”,導(dǎo)致信息丟失很嚴(yán)重,測(cè)算出來的結(jié)果與實(shí)際情況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我們還是采用傳統(tǒng)的索洛殘差法來測(cè)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雖然該方法不能像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法和非參數(shù)方法一樣對(duì)全要素進(jìn)行分解,但這并不影響我們的研究。
三、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測(cè)算
計(jì)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所需的真實(shí)產(chǎn)出和勞動(dòng)投入序列可以方便地從現(xiàn)有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中直接獲得,但資本存量序列需要在統(tǒng)計(jì)資料的數(shù)據(jù)基礎(chǔ)上進(jìn)行估算。
測(cè)算資本存量的基本方法是由Goldsmith于1951年開創(chuàng)的永續(xù)盤存法[13],現(xiàn)在被OECD國(guó)家所廣泛采用,它的基本公式為:
其中,It是t期以當(dāng)期價(jià)格計(jì)價(jià)的投資額,Pt是t期的價(jià)格指數(shù),δ是折舊率。此式含義是,t期的資本存量Kt是從上一期留存下來的資本存量 (1-δ)Kt-1與t期的實(shí)際投資It/Pt之和。容易看出,估算資本存量涉及到四個(gè)方面的工作:對(duì)基期資本存量K0的猜測(cè)、歷年投資流量指標(biāo)的選取、價(jià)格指數(shù)的選取或構(gòu)造和折舊率的設(shè)定。現(xiàn)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永續(xù)盤存法的基礎(chǔ)上來進(jìn)行的,但是在處理細(xì)節(jié)上卻有很大差異,比較有代表性的如表1所示。

表1 資本存量估算方法對(duì)比
從表1中可以看出,各方在四個(gè)方面的處理方法也同樣有很大差異。
基期資本存量基本上都是按某個(gè)比例推算出來的 (如全國(guó)基期資本存量與上海市基期資本存量的比例、與工業(yè)企業(yè)的基期資本存量比例、與國(guó)民收入的比例等)。哪種算法較好,我們無法做出評(píng)價(jià)。比較一致的看法是,K0僅對(duì)期初之后幾年里的資本存量估算影響較大,隨著K0的逐漸折舊,后期的資本存量估算會(huì)越來越準(zhǔn)確。我們的基期資本存量按國(guó)際常用方法計(jì)算,即K0=I0/(g+δ),其中,g是樣本期真實(shí)投資的年平均增長(zhǎng)率,δ是綜合折舊率。
投資流量指標(biāo)的選取集中在積累額、全社會(huì)固定資產(chǎn)投資、新增固定資產(chǎn)投資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四個(gè)指標(biāo)。因中國(guó)統(tǒng)計(jì)體系自1993年起不再公布積累額之類的指標(biāo),故張軍和章元[16]以及Chow[14]的方法不適于沿用。全社會(huì)固定資本投資是在MPS和SNA體系下都公布的一個(gè)投資指標(biāo),它的主要問題是與SNA的統(tǒng)計(jì)體系不相容,是中國(guó)投資統(tǒng)計(jì)特有的指標(biāo)。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不包括存貨的投資流量,它與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中通常所指的投資具有一致的含義,同時(shí)也是和國(guó)際上通常用的固定資產(chǎn)投資基本一致的指標(biāo)。新增固定資產(chǎn)投資實(shí)際上是對(duì)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進(jìn)行一定程度的扣除后得到的一個(gè)指標(biāo),但在實(shí)際操作過程中,扣除的理由和標(biāo)準(zhǔn)不一,隨意性較大。綜上所述,我們?cè)诒疚闹胁捎玫漠?dāng)年投資指標(biāo)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并且認(rèn)為它是衡量當(dāng)年投資的合理指標(biāo)。
用什么價(jià)格指數(shù)來平減當(dāng)期的投資流量,是估算中的重要一環(huán)。統(tǒng)計(jì)年鑒自1991年起,開始公布固定資產(chǎn)投資價(jià)格指數(shù)。這基本被一致認(rèn)為是最合適的指標(biāo),但它只從1991年才開始有,1990年以前用什么指標(biāo)呢?從表1可見,研究者們大多是用其它的價(jià)格指數(shù)指標(biāo)進(jìn)行替代。常見的替代指標(biāo)是工業(yè)品出廠價(jià)格指數(shù)、上海市固定資產(chǎn)投資價(jià)格指數(shù)等。另一種辦法是從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及固定資本形成指數(shù)來構(gòu)造投資隱含平減價(jià)格指數(shù)。何楓等[17]、Holz[18]就是這么處理的。我們認(rèn)為既然投資流量指標(biāo)的選取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而2007年《中國(guó)國(guó)內(nèi)生產(chǎn)總值核算歷史資料 (1952—2004)》的發(fā)布,為推算固定資本形成平減指數(shù)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那么用該指數(shù)來平減當(dāng)期的投資流量是最合適的。
根據(jù)《中國(guó)國(guó)內(nèi)生產(chǎn)總值核算歷史資料 (1952—2004)》公布的數(shù)據(jù),我們只有截止于2004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指數(shù)。這樣,我們便無法直接把我國(guó)2004—2009年間的用當(dāng)年價(jià)格給出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折算成以2000年價(jià)格表示的數(shù)據(jù)。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構(gòu)造指數(shù)來間接實(shí)現(xiàn)這個(gè)目的。經(jīng)過分析,我們選擇了通過擬合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平減指數(shù)與GDP平減指數(shù)在1978—2004年間的關(guān)系來估算2005—2009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平減指數(shù) (2000年=1),以推算我國(guó)2004—2009年間以2000年價(jià)格表示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具體構(gòu)造關(guān)系如下:

調(diào)整后的R2=0.996
其中,IDt為所構(gòu)造的第t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平減指數(shù),GDPDt第t年的GDP平減指數(shù),共計(jì)27個(gè)觀測(cè)值。
至于折舊,目前沒有公認(rèn)的合適處理辦法。即便是2009年的統(tǒng)計(jì)年鑒,它也提到目前我國(guó)尚不具備對(duì)全社會(huì)固定資產(chǎn)進(jìn)行重估價(jià)的基礎(chǔ),只能按照規(guī)定的固定資產(chǎn)折舊率的方法來提取固定資產(chǎn)折舊。因此,我們不對(duì)各方處理方法的優(yōu)劣進(jìn)行判斷。根據(jù)我國(guó)的情況,一般采用綜合折舊率為5%。
確定了基期資本存量、投資流量指標(biāo)、價(jià)格指數(shù)指標(biāo)和折舊率后,通過方程 (7)可以估算出1978—2009年我國(guó)的資本存量。計(jì)算全要素生產(chǎn)率所需的其它兩個(gè)序列可從統(tǒng)計(jì)年鑒中獲得。對(duì)于與生產(chǎn)函數(shù)設(shè)定中變量L相對(duì)應(yīng)的現(xiàn)實(shí)數(shù)據(jù),國(guó)外文獻(xiàn)通常使用工作小時(shí)數(shù),但我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中沒有提供這個(gè)指標(biāo),故選取歷年的就業(yè)人員數(shù)。另外,注意到指標(biāo)給出的是年底數(shù),為與GDP流量的含義相一致,將前后兩年的就業(yè)人員數(shù)進(jìn)行算術(shù)平均,獲得年中的就業(yè)數(shù)。1978—2009年我國(guó)真實(shí)產(chǎn)出、資本存量和勞動(dòng)投入數(shù)據(jù)見表2所示。

表2 推算我國(guó)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
由表2中的數(shù)據(jù)對(duì)方程 (4)進(jìn)行OLS估計(jì),結(jié)果如下:

調(diào)整后的R2=0.997

圖1 1979—2009年中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動(dòng)
由此得到α=0.711,β=0.289,再分別計(jì)算出實(shí)際產(chǎn)出、就業(yè)人數(shù)和資本存量的逐年增長(zhǎng)率,一并代入方程 (4),可以得到我國(guó)1979—2009年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結(jié)果見表2所示。1979—2009年中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動(dòng)情況如圖1所示。
本文測(cè)算出來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與郭慶旺和賈俊雪[5]測(cè)算出來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大體趨勢(shì)是一致的,但是存在一定的偏差。除了資本存量估算方法不一樣外,資本和勞動(dòng)力要素投入數(shù)據(jù)處理方法不一樣也是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本文使用資本和勞動(dòng)力要素投入都是年中數(shù),而郭慶旺和賈俊雪使用的是年末數(shù)。本文認(rèn)為,年中數(shù)能更準(zhǔn)確地反映要素投入的真實(shí)情況。從圖1中可以看出,1994年以前,中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動(dòng)主要受自身制度改革的影響,隨著政策措施的變化而大起大落,在1992年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達(dá)到歷史最高點(diǎn)7.189%。1992年后,對(duì)外開放度的逐步加大,使得外部因素 (比如東南亞金融危機(jī))對(duì)中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影響力上升。在加入WTO后,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動(dòng)進(jìn)入穩(wěn)定增長(zhǎng)的狀態(tài),但這種穩(wěn)定增長(zhǎng)狀態(tài)隨后又被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fēng)暴所打斷,中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在2007年達(dá)到一個(gè)波峰后迅速跌落至2009年的-0.402%,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我國(guó)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育在趨向成熟,影響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主要因素從政策因素已經(jīng)轉(zhuǎn)向市場(chǎng)因素。
四、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解釋
全要素生產(chǎn)率是指扣除了資本投入和勞動(dòng)投入的貢獻(xiàn)以外,其他所有能夠?qū)崿F(xiàn)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因素貢獻(xiàn)的總和。這個(gè)總和的來源包括技術(shù)進(jìn)步、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主要體現(xiàn)為體制的不斷完善)和隨機(jī)因素等。因此,理論上我們所計(jì)算出來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主要包含兩個(gè)方面的因素:一個(gè)是技術(shù)進(jìn)步,另一個(gè)就是體制完善 (主要是經(jīng)濟(jì)體制的完善)。在實(shí)證環(huán)節(jié)上,只要能對(duì)技術(shù)進(jìn)步和經(jīng)濟(jì)體制的完善進(jìn)行量化,就能定量測(cè)算技術(shù)進(jìn)步和體制改進(jìn)這兩個(gè)主要因素對(du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貢獻(xiàn)。一般認(rèn)為,技術(shù)引進(jìn)和自主創(chuàng)新是發(fā)展中國(guó)家實(shí)現(xiàn)技術(shù)進(jìn)步的最基本的方式。基于以上考慮,我們建立如下模型對(du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變動(dòng)情況進(jìn)行實(shí)證分析:①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的自相關(guān)檢驗(yàn)結(jié)果表明該時(shí)間序列存在自相關(guān)性,且其自相關(guān)系數(shù)在第1期后迅速趨于0,因此我們?cè)谀P椭屑尤肫湟黄跍箜?xiàng)作為解釋變量。

其中,Mindt為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用來衡量經(jīng)濟(jì)體制的改進(jìn);Timpt為國(guó)外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用來衡量技術(shù)進(jìn)步中的技術(shù)引進(jìn)因素;Rdt為研發(fā)經(jīng)費(fèi)投入,用來衡量技術(shù)進(jìn)步中的自主創(chuàng)新因素,lnTFPt-1為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的一期滯后項(xiàng);α0為常數(shù)項(xiàng),α1、α2、α3和α4分別為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對(duì)經(jīng)濟(jì)體制的改進(jìn)、國(guó)外技術(shù)引進(jìn)、自主創(chuàng)新投入和滯后項(xiàng)的彈性系數(shù);εt為白噪音。
方程 (10)中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率序列已經(jīng)在前文中估算出來了,國(guó)外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和研發(fā)經(jīng)費(fèi)投入數(shù)據(jù)可以從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中直接獲得,只有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需要我們建立指標(biāo)體系進(jìn)行測(cè)算。
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guó)是一個(gè)封閉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國(guó)家,在1978年后才從計(jì)劃經(jīng)濟(jì)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因此,以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作為我國(guó)經(jīng)濟(jì)制度變遷不失為一個(gè)不錯(cuò)的選擇。改革開放以后,我國(guó)由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轉(zhuǎn)型總體上是從四個(gè)方面展開的:即政府與市場(chǎng)關(guān)系的理順、非國(guó)有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經(jīng)濟(jì)對(duì)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和產(chǎn)品市場(chǎng)的培育。我們從中國(guó)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的這四個(gè)方面入手構(gòu)造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指標(biāo)體系 (見表3所示),在指標(biāo)體系設(shè)計(jì)上借鑒并綜合了陳宗勝等、金玉國(guó)、易綱等和康繼軍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19]-[22],與這些已有的研究相比,我們?cè)诋a(chǎn)品市場(chǎng)培育程度方面指標(biāo)體系設(shè)計(jì)上做了較大的改進(jìn),同時(shí)對(duì)其他方面的指標(biāo)體系和數(shù)據(jù)處理做了進(jìn)一步的改進(jìn)和完善。

表3 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指標(biāo)體系
各方面指標(biāo)體系建立以后,我們采用“相對(duì)比較法”將各二級(jí)指標(biāo)數(shù)據(jù)轉(zhuǎn)化為指數(shù)值,即指標(biāo)的評(píng)分表示了該年度該方面指標(biāo)在整個(gè)樣本區(qū)間時(shí)間序列上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的相對(duì)位置。根據(jù)指標(biāo)數(shù)值高低與市場(chǎng)化程度高低的理論關(guān)系,計(jì)算指標(biāo)得分的公式可分為兩大類:正指標(biāo)和負(fù)指標(biāo)。正指標(biāo)是與市場(chǎng)化程度高低正相關(guān)的指標(biāo),這些指標(biāo)的得分采用下列公式計(jì)算:
第 i個(gè)指標(biāo)得分= (vi-vmin)/(vmax-vmin)×100
其中,vi是第i個(gè)指標(biāo)的原始數(shù)據(jù),vmax和vmin為樣本區(qū)間 (1978—2009年)內(nèi)指標(biāo)原始數(shù)據(jù)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當(dāng)指標(biāo)數(shù)值高低與市場(chǎng)化程度高低負(fù)相關(guān)時(shí)稱這些指標(biāo)為負(fù)指標(biāo),負(fù)指標(biāo)的得分采用下列公式計(jì)算:
第 i個(gè)指標(biāo)得分= (vmax-vi)/(vmax-vmin)×100
經(jīng)過上述處理,各項(xiàng)得分均與市場(chǎng)化程度正相關(guān),即:得分越高,市場(chǎng)化程度越高;反之市場(chǎng)化程度越低。
在多因素分析中,權(quán)重的選取是個(gè)難點(diǎn)。其中,定性的方法與定量的方法都有廣泛的應(yīng)用。由于市場(chǎng)化是一個(gè)抽象概念,其各組成方面的重要程度很難從經(jīng)濟(jì)理論或定性的方面加以判斷。為避免主觀隨機(jī)因素的干擾,本文選擇變異系數(shù)法來確定指標(biāo)權(quán)重。變異系數(shù)法以指標(biāo)的均值和方差為基礎(chǔ),根據(jù)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特征值之間的變異程度對(duì)指標(biāo)進(jìn)行賦權(quán),對(duì)不同評(píng)價(jià)對(duì)象之間區(qū)別比較大的指標(biāo)賦予較大的權(quán)重,而對(duì)沒明顯差異的指標(biāo)賦予較小的權(quán)重。我們認(rèn)為,市場(chǎng)化指標(biāo)的權(quán)重不應(yīng)該是固定不變的,應(yīng)該隨著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的變化而變化。變異系數(shù)法隨著數(shù)據(jù)的不同,測(cè)算得出不同的權(quán)重,較好地體現(xiàn)了指標(biāo)權(quán)重的動(dòng)態(tài)性。
從圖2中可以看出,中國(guó)的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以1994年為界,分成兩個(gè)階段。第一階段中國(guó)的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進(jìn)展迅速,從1978年的0.5229直線上升到1994年的76.81,年均增長(zhǎng)36.59%。經(jīng)過這一階段的發(fā)展,我國(guó)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第二階段中國(guó)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建設(shè)進(jìn)入一個(gè)逐漸完善的階段。這一階段中國(guó)的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則表現(xiàn)為穩(wěn)步推進(jìn),從1995年的74.86逐漸上升到2007年的歷史最高點(diǎn)86.50。之后,由于全球金融危機(jī)的爆發(fā),我國(guó)推出4萬億元經(jīng)濟(jì)刺激計(jì)劃,這些資金大部分流向國(guó)有企業(yè),使得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出現(xiàn)了小幅下降。經(jīng)過這一階段的發(fā)展,我國(guó)已經(jīng)是相對(duì)成熟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了。
在中國(guó)科技統(tǒng)計(jì)年鑒僅公布了從1987年以來歷年的R&D經(jīng)費(fèi)數(shù)據(jù)。對(duì)于1978—1986年的R&D投入,本文擬通過自回歸趨勢(shì)模型外推獲得。根據(jù)AIC,SC最小化原則,發(fā)現(xiàn)最優(yōu)的滯后期為1。對(duì)自回歸趨勢(shì)模型回歸得到:

調(diào)整后的R2=0.996
利用上式,可以外推得到1978—1986年的R&D投入。改革開放以來歷年的技術(shù)引進(jìn)數(shù)據(jù)來自商務(wù)部。1978—2009年中國(guó)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和R&D經(jīng)費(fèi)投入見圖3所示。從圖3中可以看出,在1994年以前,無論是國(guó)外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還是R&D經(jīng)費(fèi)投入都比較少,從1994年開始,無論國(guó)外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還是R&D經(jīng)費(fèi)投入都開始大幅增加,但在2000年以前,我國(guó)國(guó)外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在大多數(shù)年份都高于R&D經(jīng)費(fèi)投入,說明我國(guó)在2000年以前具有很強(qiáng)的“重引進(jìn)、輕消化和創(chuàng)新”傾向。2000年以后我國(guó)越來越重視自主創(chuàng)新,R&D經(jīng)費(fèi)投入年均增長(zhǎng)速度達(dá)到16.27%,R&D經(jīng)費(fèi)投入強(qiáng)度從2000年的0.9%增長(zhǎng)到2009年的1.7%,增加近一倍。
從理論上講,技術(shù)引進(jìn)對(du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具有影響,反過來,由于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水平提高,從而提高對(duì)新技術(shù)吸收能力,進(jìn)而有助于技術(shù)引進(jìn),從而導(dǎo)致所謂內(nèi)生性問題,產(chǎn)生有偏、非一致的估計(jì)量。因此,在對(duì)方程(10)進(jìn)行估計(jì)之前,還需檢驗(yàn)變量的內(nèi)生性。我們利用Hausman檢驗(yàn)直接比較普通最小二乘 (OLS)和兩階段最小二乘 (2SLS)估計(jì)值,判斷其差異是否在統(tǒng)計(jì)上顯著[23]。因?yàn)樗薪忉屪兞慷际峭馍鷷r(shí),OLS和2SLS都是一致估計(jì)量,如果差異顯著,則可以判定有內(nèi)生性變量。
我們選取lnTimpt-1作為lnTimpt的工具變量。用待檢驗(yàn)變量lnTimpt對(duì)方程 (10)的全部外生變量 lnMindt、lnRdt、lnTFPt-1和選定的工具變量 lnTimpt-1進(jìn)行回歸:

用OLS法對(duì)方程 (12)進(jìn)行回歸,并求殘差。將所求的殘差作為附加變量加入到方程 (10)中,得到:

對(duì)方程 (13)進(jìn)行OLS回歸,如果α5是顯著的,則α0、α1、α2、α3和α4不具有一致性,說明lnTimpt是內(nèi)生變量。
檢驗(yàn)結(jié)果是vt的系數(shù)值為-0.08,P值為0.06,表明系數(shù)不顯著,可以在統(tǒng)計(jì)上排除變量ln-Timpt的內(nèi)生性。因此,我們可以認(rèn)為方程 (10)的OLS估計(jì)結(jié)果是無偏、一致的。
前文的分析表明,無論是從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還是從R&D經(jīng)費(fèi)和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來看,1994年似乎都是一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這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可能會(huì)對(du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影響因素模型的穩(wěn)定性產(chǎn)生影響。因此在對(duì)方程(10)進(jìn)行OLS估計(jì)后,還需進(jìn)行拐點(diǎn)的檢驗(yàn),以確認(rèn)拐點(diǎn)的存在。本文采用Chow檢驗(yàn)來判斷1994年是否是一個(gè)拐點(diǎn),①Chow檢驗(yàn)法是鄒至莊提出的,用于判斷結(jié)構(gòu)在預(yù)先給定的時(shí)點(diǎn)是否發(fā)生了變化的一種方法。檢驗(yàn)結(jié)果見表4所示。

圖3 1978—2009年中國(guó)R&D經(jīng)費(fèi)和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

表4 拐點(diǎn) (1994年)檢驗(yàn)結(jié)果
無論是從F統(tǒng)計(jì)量還是從對(duì)數(shù)似然比LR統(tǒng)計(jì)量的檢驗(yàn)結(jié)果都表明,在考察期內(nèi)全要素生產(chǎn)率和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guān)系在1994年發(fā)生了機(jī)制轉(zhuǎn)變,那么在整個(gè)考察期內(nèi)全要素生產(chǎn)率影響因素模型的參數(shù)應(yīng)該是不固定的,因此,我們?cè)谶M(jìn)行模型回歸時(shí),先以1994年為界將樣本分為兩部分進(jìn)行分段回歸,隨后再進(jìn)行全樣本的回歸。方程 (10)的OLS回歸結(jié)果見表5所示。

表5 全要素生產(chǎn)率影響因素模型回歸結(jié)果
1979—2009年的全樣本回歸結(jié)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受其自身上一期滯后值的影響最大,說明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存在著較大的慣性,靈敏度較低。除此之外,技術(shù)引進(jìn)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的主要原因 (國(guó)外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每增加一個(gè)百分點(diǎn),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0.0131個(gè)百分點(diǎn)),制度變遷和自主創(chuàng)新對(du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的影響不明顯。
1979—1994年的子樣本回歸結(jié)果表明,制度變遷和自主創(chuàng)新對(duì)這段時(shí)間內(nèi)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影響都不明顯,技術(shù)引進(jìn)是1979—1994年間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的主要原因,而且其影響較整個(gè)樣本期間內(nèi)要高0.003個(gè)百分點(diǎn)。一般認(rèn)為,制度變遷會(huì)導(dǎo)致資本、勞動(dòng)和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zhǎng),進(jìn)而促使經(jīng)濟(jì)的增長(zhǎng)。我們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1979—1994年期間,我國(guó)制度變遷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推動(dòng)更多的是通過促進(jìn)資本、勞動(dòng)增長(zhǎng) (進(jìn)而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的增長(zhǎng))這一方式來進(jìn)行的,而不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 (進(jìn)而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的增長(zhǎng))來進(jìn)行的。
1995—2009年的子樣本回歸結(jié)果表明,制度變遷是這段時(shí)期內(nèi)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zhǎng)的主要原因,市場(chǎng)化每增加一個(gè)百分點(diǎn),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0.0824個(gè)百分點(diǎn),這說明我國(guó)在初步建立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之后,我國(guó)制度變遷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作用才從推動(dòng)資本、勞動(dòng)增長(zhǎng)轉(zhuǎn)到推動(dòng)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zhǎng)上來。技術(shù)引進(jìn)在這段時(shí)期內(nèi)對(duì)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作用不明顯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由于20世紀(jì)80年代我國(guó)技術(shù)水平遠(yuǎn)落后于發(fā)達(dá)國(guó)家,差距比較大,通過引進(jìn)國(guó)外成熟技術(shù)也能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當(dāng)差距縮小后,發(fā)達(dá)國(guó)家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愿意轉(zhuǎn)讓先進(jìn)技術(shù),通過技術(shù)引進(jìn)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效果自然會(huì)變差。回歸結(jié)果還表明,盡管近年來我國(guó)的R&D經(jīng)費(fèi)投入增長(zhǎng)迅速,但這些R&D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我國(guó)技術(shù)知識(shí)存量,并沒有有效地轉(zhuǎn)化為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提高。
五、結(jié) 語
本文首先利用索洛殘差法對(du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進(jìn)行了估算,隨后通過構(gòu)造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來衡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uó)經(jīng)濟(jì)體制的變遷,同時(shí)用R&D投入和國(guó)外技術(shù)引進(jìn)經(jīng)費(fèi)分別衡量自主創(chuàng)新和技術(shù)引進(jìn),對(du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動(dòng)的原因進(jìn)行定量的考察。分析表明:(1)技術(shù)引進(jìn)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化的主要原因。(2)1994年以后我國(guó)制度變遷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作用才從推動(dòng)資本、勞動(dòng)增長(zhǎng)轉(zhuǎn)到推動(dòng)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增長(zhǎng)上來。(3)雖然改革開放以來R&D經(jīng)費(fèi)投入增長(zhǎng)迅速,但這些R&D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我國(guó)技術(shù)知識(shí)存量,并沒有有效地轉(zhuǎn)化為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提高。
中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變化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不同,不是因?yàn)镽&D工作取得了很大進(jìn)展,而是因?yàn)楦母?市場(chǎng)化)和開放 (技術(shù)引進(jìn))效應(yīng),但是這些效應(yīng)正在逐漸減弱,同時(shí),中國(guó)還需要從低就業(yè)增長(zhǎng)轉(zhuǎn)向高就業(yè)增長(zhǎng);從不公平增長(zhǎng)轉(zhuǎn)向公平增長(zhǎng);從不可持續(xù)增長(zhǎng)轉(zhuǎn)向可持續(xù)增長(zhǎng)。在這種情況下,很顯然,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式將難以為繼。因此,能否真正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式的轉(zhuǎn)變是未來中國(guó)能不能保持穩(wěn)定較快增長(zhǎng)的關(guān)鍵所在。
[1]Krugman,P.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1994,73(6):62-78.
[2]張軍,施少華.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動(dòng):1952—1998[J].世界經(jīng)濟(jì)文匯,2003,(2):17-24.
[3]樊綱,王小魯.中國(guó)各地區(qū)市場(chǎng)化相對(duì)進(jìn)程報(bào)告[J].經(jīng)濟(jì)研究,2003,(3):9-18.
[4]顏鵬飛,王兵.技術(shù)效率、技術(shù)進(jìn)步與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基于DEA的實(shí)證分析[J].經(jīng)濟(jì)研究,2004,(12):55-65.
[5]郭慶旺,賈俊雪.中國(guó)潛在產(chǎn)出與產(chǎn)出缺口的估算[J].經(jīng)濟(jì)研究,2004,(5):31-39.
[6]鄭京海,胡鞍鋼.中國(guó)改革時(shí)期省際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變化的實(shí)證分析(1979—2001年)[J].經(jīng)濟(jì)學(xué)(季刊),2005,(2).
[7]李賓,曾志雄.中國(guó)全要素生產(chǎn)率變動(dòng)的再測(cè)算:1978—2007年[J].數(shù)量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研究,2009,(3):1-14.
[8]謝千里,羅斯基,鄭玉歆.改革以來中國(guó)工業(yè)生產(chǎn)率變動(dòng)趨勢(shì)的估計(jì)及其可靠性分析[J].經(jīng)濟(jì)研究,1995,(12).
[9]鄭玉歆.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測(cè)度及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方式的“階段性”規(guī)律——由東亞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方式的爭(zhēng)論談起[J].經(jīng)濟(jì)研究,1999,(5):55-60.
[10]Solow,R.M.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312-320.
[11]Fare,R.,Grosskopf,S.,Norris,M.,Zhang,Z.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66-83.
[12]劉光嶺,盧寧.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測(cè)算與分解:研究述評(píng)[J].經(jīng)濟(jì)學(xué)動(dòng)態(tài),2008,(10):78-82.
[13]Goldsmith,R.W.A Perpetual Inventory of National Wealth,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R].New York:NBER,1951.
[14]Chow,G.C.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
[15]王小魯,樊綱.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可持續(xù)性——跨世紀(jì)的回顧與展望[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00.
[16]張軍,章元.對(duì)中國(guó)資本存量K的再估計(jì)[J].經(jīng)濟(jì)研究,2003,(7):35-43.
[17]何楓,陳榮,何林.我國(guó)資本存量的估算及其相關(guān)分析[J].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03,(5):29-35.
[18]Holz,C.A.New Capital Estimates for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6,17(2):142-185.
[19]陳宗勝,吳浙,謝思全,等.中國(guó)經(jīng)濟(jì)體制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0]金玉國(guó).宏觀制度變遷對(d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J].財(cái)經(jīng)科學(xué),2001,(2):24-28.
[21]易綱,樊綱,李巖.關(guān)于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與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理論思考[J].經(jīng)濟(jì)研究,2003,(8):13-20.
[22]康繼軍,張宗益,傅蘊(yùn)英.中國(guó)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與增長(zhǎng)[J].管理世界,2007,(1):7-17.
[23]Hausman,J.A.Specification Tests in Econometrics[J].Econometrica,1978,46(6):1251-1271.
- 財(cái)經(jīng)問題研究的其它文章
- 轉(zhuǎn)變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式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與地區(qū)間差異分析——以遼寧省為例
- 分位數(shù)上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支出的決定
- 大型零售超市帕累托效應(yīng)解析與客類營(yíng)銷研究
- 物流金融參與主體間聯(lián)合最優(yōu)決策分析
- FDI溢出效應(yīng)對(duì)我國(guó)流通服務(wù)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的影響研究
- 我國(guó)利用技術(shù)溢出的新貿(mào)易方式分析——基于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的跨行業(yè)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