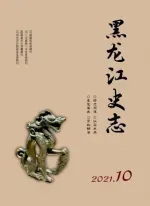簡論兩宋軍力弱化的原因
聶遠(yuǎn)鑫
(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社會與歷史學(xué)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兩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可謂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個巔峰時期,對外戰(zhàn)爭卻屢屢失敗,經(jīng)濟(jì)軍事反差之大令人錯愕。宋代軍力不振不能不引起后人反思,這不僅是一項(xiàng)求真求實(shí)的工作,在祖國蓬勃發(fā)展國際局勢波濤譎涌的今天更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既有歷史的繼承性也有自身的時代特點(diǎn),其軍事概況也與此相近,筆者認(rèn)為宋代國防的“積弱”無法回避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力懲唐末五代藩鎮(zhèn)割據(jù)積弊的消極后果。“杯酒釋兵權(quán)”后,“更戍法”、“將從中御”等軍事制度,大大地限制了軍隊(duì)的機(jī)動性與靈活性,使宋軍喪失了國防的主動權(quán),陷入軍力弱化的泥潭。宿將兵權(quán)被剝奪,軍官悉用資望較淺容易駕馭的人物充任,目的只為防止藩鎮(zhèn)割據(jù)的重演,使宋避免成為短命王朝。“更戍法”使“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固然消除了藩鎮(zhèn)割據(jù)的隱患,但卻造成將領(lǐng)與部隊(duì)的離心,遇有戰(zhàn)事,往往釀成災(zāi)難性的后果。如慶歷元年(1041)好水川之戰(zhàn),戰(zhàn)前“任福在慶州,番漢漸各信服,士卒亦諳練”。臨戰(zhàn),任福突然被調(diào)至涇原擔(dān)任主將,“麾下隊(duì)兵逐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1](卷一百三十二,慶歷元年五月甲戌)最后為西夏所敗,任福也槍中左頜而死。宋朝后代皇帝們因循僵化地繼承了宋初明顯帶有時限性的政策,如打仗時要依據(jù)欽命“陣圖”作戰(zhàn),宋太祖出身軍旅,所制“陣圖”尚能與戰(zhàn)場實(shí)際相符,后代皇帝們長于深宮,卻要遙控前線作戰(zhàn),所授陣圖與前線戰(zhàn)況往往廖之千里。如太平興國四年(979)的滿城之戰(zhàn),宋太宗對將領(lǐng)們預(yù)先“賜陣圖,分為八陣,俾以從事”。[2](卷二百七十一,《趙延進(jìn)傳》)殿前都虞侯崔翰依圖布陣,右龍武將軍趙延進(jìn)冒違詔改陣之罪,建議集中兵力對敵。監(jiān)軍李繼隆也說“事應(yīng)有變,安可預(yù)定,設(shè)獲違詔之罪,請獨(dú)當(dāng)也”。[2](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崔翰在二人堅(jiān)持下才改八陣為二陣,最后大敗遼軍,這是一場違反“將從中御”而獲勝的戰(zhàn)斗。宋神宗“每當(dāng)用兵,或終夜不寢”,“手札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雖千里外,上自節(jié)制”[1](卷三百五十三,元豐八年三月戊戌),結(jié)果招致靈州和永樂兩次戰(zhàn)役大敗。高宗時,由宰執(zhí)大臣草擬皇帝手詔,指揮前線軍事。如劉錡在順昌府遭兀術(shù)主力騎兵圍攻,若棄城退遁,必被迫殲,秦檜為高宗所起草的御札卻令他“擇利班師”。[3](卷一百三十六,紹興十年六月乙卯)
二、宋開國以來“崇文抑武”國策,造成整個社會尚武風(fēng)氣日衰。宋太祖時明確提倡“興文教,抑武事”,廣開科舉文選,科舉的成功勝過任何軍功,以至于有“狀元登第,雖將兵十萬,恢復(fù)幽薊,逐強(qiáng)虜于窮漠,凱歌勞還,獻(xiàn)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4](《儒林公議》卷上,明刻本)的說法。于是讀書成了逐取功名和獲得社會承認(rèn)的主要途徑。宋朝雖設(shè)有武舉,卻以試策高低為去留,如仁宗天圣八年(1030)開武舉:“武舉發(fā),先閱射騎,而試之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5](卷三十八,《宋紀(jì)》三十八)這樣造成了對武士選拔的重文輕武。在官職授予上,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職,多由科舉出身的文官擔(dān)任,甚至掌握全國軍權(quán)的樞密使,州縣軍隊(duì)指揮,都委以文官。即使有武官擔(dān)任要職也常受文人的排擠和壓制,如名將狄青雖官至樞密使,卻因出身行伍而備受歧視,共事的韓琦對他多次羞辱,狄青慨嘆“韓樞密功業(yè)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進(jìn)士及第耳”。[2](卷二百九十,《狄青傳》)在文臣們的誣陷排斥之下,狄青最后被貶知陳州,含恨而死。武舉官職低微,地位低下,不足以激發(fā)其持干戈以衛(wèi)社稷、建功立業(yè)的雄心。正如蘇紳所言“擇將帥,漢制,邊防有敬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員外、郎中以上為刺史,團(tuán)練防御,觀察節(jié)度等使,皆是養(yǎng)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比年設(shè)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jiān)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2](卷二百九十四,《蘇紳傳》)南宋武舉授官較北宋稍高,地位也有所上升,卻舉非所用,“皆任以榷酤征商之事”。[1](卷一百三十八,淳熙十年九月壬午)赳赳武士不馳騁沙場,卻務(wù)商理財(cái)。宋代的重文抑武,武人地位低下,待遇不公,與此相映成彰的是宋軍對外戰(zhàn)爭中的不堪一擊。
三、宋朝奉行“攘外必先安內(nèi)”觀念,長期忽視軍備,士兵得不到正規(guī)而有效的訓(xùn)練,軍隊(duì)經(jīng)營商業(yè),武器質(zhì)量低劣,導(dǎo)致戰(zhàn)斗力低下。宋軍訓(xùn)練只注重形式而不關(guān)心實(shí)效。如射箭,則“惟務(wù)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只看重拉弓弩者力氣的大小,卻不問能否射中目標(biāo)。弓弩手是宋軍的主要組成部分,當(dāng)時身居西北戰(zhàn)區(qū)的尹洙指出,馬軍中十分之八是弓箭手,步軍中十分之七是弩手,雖各帶劍一口,卻不在教練之列,因而宋軍不利于近戰(zhàn)。[6](卷二十)“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其左右斫、腰射、射腦、一綽子放數(shù)箭之類,乃軍中之戲”,成了與戰(zhàn)斗無關(guān)的軍事雜耍。這樣訓(xùn)練出來的軍隊(duì),其戰(zhàn)斗力可想而知。“時邊任多紈绔子弟”,“軍從,娼婦多從之”。[2](卷一百三十七,慶歷二年六月已未)如此將官,如此軍隊(duì),與驍勇善戰(zhàn)的馬背上的民族交戰(zhàn),焉能不敗。宋代軍隊(duì)經(jīng)商泛濫無度嚴(yán)重地腐化了軍中風(fēng)氣,沿邊武將以朝廷專拔的軍資庫錢物、公用錢等官錢作本,經(jīng)營商業(yè)、借貸業(yè),違禁販運(yùn)鹽、酒、茶等,營私舞弊。上至將領(lǐng),下至士卒,都沉浸在追末逐利的風(fēng)氣中,嚴(yán)重影響了戰(zhàn)斗力。仁宗時,范仲淹“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將回易利息“充隨軍公用支使”。[7](《范文正公奏議·奏雪滕宗諒張亢》)南宋時,這種贏利經(jīng)營活動導(dǎo)致將帥貪污腐化,軍事訓(xùn)練松弛,將成庸將,兵不類兵,戰(zhàn)斗力嚴(yán)重下降,在敵人面前一觸即潰。宋軍使用的武器質(zhì)量低劣,“長短小大,多不中度”,“鐵刃不鋼”,弓弩“勁膠不固”。官府武器造作之所,但務(wù)充數(shù)而根本不考慮使用,主管官員也不檢查武器的質(zhì)量,以至“有器械只虛名,而無器械之使用”。[2](卷一百三十六,慶歷二年五月甲寅)
總之,整個宋代,抑制武官,防范武臣是宋朝政治的重要特點(diǎn),也是其重要弱點(diǎn),畸形的軍事指揮和管理體制,對武人階層的輕視,軍備的荒廢,國防上的消極防御令宋朝軍力消弱,國力不振,這又勢必造成對外妥協(xié)茍安,而茍安的政策又繼續(xù)弱化軍力,由此宋代軍事陷入了惡性的循環(huán)。所以盡管宋朝經(jīng)濟(jì)繁榮,但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和文明成果卻沒有轉(zhuǎn)化為軍事實(shí)力,從裝備到戰(zhàn)法較前朝非但沒有根本的改變和提高,反而在戰(zhàn)斗力上出現(xiàn)了嚴(yán)重的倒退,進(jìn)而加劇了宋朝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與軍事實(shí)力的失衡,最終被后起的元朝所滅。
[1]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2]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3]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8.
[4]田況.儒林公議.卷上,明刻本.
[5]畢沅.續(xù)資治通鑒.中華書局校點(diǎn)本.
[6]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Z].商務(wù)印書館.
[7]范仲淹.范文正公奏議·奏雪滕宗諒張亢.[Z].上海涵芬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