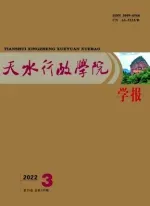淺析古希臘政治思維的特點及其現代意義
寇大偉
(福建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淺析古希臘政治思維的特點及其現代意義
寇大偉
(福建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古希臘城邦具有政治意義,“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即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古希臘公私領域的區分,城邦生活的原則即正義以及求善的制度安排即政體,都充分體現出了古希臘政治思維的特點。古希臘政治思想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源頭活水。現在的社群主義、新共和主義都不同程度地把他們的思想返回到古希臘的政治思維,從古希臘的政治思維中尋求有價值的思想源泉。
古希臘;政治思維;特點;現代意義
一、古希臘政治思維的特點
(一)城邦的政治意義
城邦具有保護性和共享性。城邦制是希臘人跨入文明時,替代以氏族制度為基礎的原始公社組織的一種新型的社會與政治單位。它的產生既由于古希臘特殊的地理環境及進入文明時獨特的歷史發展條件,同時也是希臘人為適應生存環境而做出的明智抉擇,是希臘人的制度創新。希臘文明從本質上說就是城邦文明,這不僅在于城邦貫穿希臘文明的始終,也在于它孕育與造就出絢麗的古希臘政治文化。作為西方歷史上第一代國家形態,城邦的組織結構和治理方式對后世西方制度建設頗具影響力。城邦制度的多元化和多樣性,雅典政治的民主化和自治化,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等眾多希臘賢哲對城邦生活的考察和探究所形成的政治思想與理論,希臘普通公民的政治認知方式、政治參與意識和行為模式等,都成了西方政治制度與思想的重要“基
因”,深埋于西方文化的傳統之中。
(二)“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即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
1.“人”(公民)的概念。它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概念,而是從“偶然成為的人”到“認識了自己的本性后可能成為的人”的動態概念。人的本性在于德性,古希臘四主德是智慧、勇敢、節制、正義。人的天性趨向是追求卓異。人只有在城邦政治領域——公共領域才能得以實現和完善,政治使人成為人。
2.私人領域。城邦生活中的公民有兩個明確區別的生活領域:以家庭為中心的私人領域和以城邦為中心的公共領域。
在家庭中,人處于物質必然性的世界,人受物質需求和生理欲望驅動,追求個人的生存利益。家庭的運作由一系列隸屬關系所組成,即女子從屬于男子,子女從屬于父母,奴隸從屬于主人。因此,家庭是一個自然共同體,是一個受物質必然性支配的自然領域,在這里沒有自由可言,人在這一領域的活動不是人的本質活動。柏拉圖甚至認為,忙于解決衣食住行的城邦只是豬的城邦,而不是人的城邦。
3.公共領域。男青年在成年以后,就開始走出家庭,步入廣場。在這里他超越了他的自然需求進入了公共領域,為實踐他的德性而擔負起公共責任,在公共活動中充分發展和展現他的德性,創立使他得以永恒的功業并達到至善的境界。所以,亞里士多德說,城邦的目標是追求至善。
城邦公民的政治活動方式:行動——對話。有德性的公民之間唯一合理的政治關系只能是說服,所以,政治行動是一種運用語言和通過語言的行動,而不是暴力。訴諸暴力是動物活動,人雖然也是動物,也使用暴力,但真正屬于人類的政治行動,或者說真正的政治行動,只能是“說服”。由說服達成一致,形成法律,并共同遵循法律。
因此,古希臘的政治意味著:在組織內部服從法律,在成員之間去除暴力;只有在政治領域中,人才能追求卓異,人的德性和能力才能得以完滿實現,才能獲得超越本能的自由,超越個人物質有限性獲得此岸永生性。
(三)正義:城邦生活的原則
理想國中的“正義”就是完全以人性的等級差異性為基礎的——人內在靈魂的等級劃分與城邦居民的等級劃分。正義就是以這種天然的等級秩序為基礎的和諧,“各得其所”、“名正言順”,比如蘇格拉底說:這個城邦之所以被認為是正義的,乃是因為城邦里天然生成的三種人各自履行其職能。還有,城邦之所以擁有節制、勇敢和智慧,也是由于這三種人擁有這些情感和習慣。
本質上說,這里的核心是將自然地、社會地形成的等級差異確認為一種不變的秩序,遵循這種秩序,不違背這種“天然”就是正義的。
(四)政體:求善的制度安排
亞氏把政體分為三類,即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此三種為正宗政體,與之對應的變態政體分別是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不同政體的要素不同,君主政體的要素是才德,貴族政體的要素是財富,共和政體的要素是多數和自由身份。
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三種單一因素的政體形式皆非優良政體。君主政體的好處在于重視榮譽,但是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公共立法和協議之外,即使君主非常公正、明智,這樣的國家仍不值得追求,因為它僅由一個人的意志和權力支配。事實上,要找到一個公正、明智的君主來統治國家也是不現實的。
貴族政體的好處在于讓社會中的有產階級、一批優秀的頭腦能夠統治這個社會,但壞處是可能變成寡頭統治,少數人專斷地對社會進行統治。民眾很難享受他們的那份自由,因為在權力上和審議共同福利上他們都被排除在外。即使由一些選民選舉出來的具備較高才德的杰出公民非常公正地治理,但由于人民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仍類似于奴隸,這樣的政體仍不值得追求。此外,貴族政體最根本的特征是“賢良”、“守法”,但這樣的貴族是很難找到的,即使找到了也難保證他們不腐化,因此,亞氏對貴族政體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共和政體,又常出現多數人的暴政以及政府運行的低效能,即使一切事情均由人民討論決定,但由于他們沒有一定的地位等級,國家仍然無法穩定。同時,直接民主的共和制只能在小國范圍內實行。特別是少數的野心家往往會操縱公民大會,作出有損于城邦的決定,將自己的政見和意志強加給盟邦,從而招致盟國的不滿和嫉恨,最后引發城邦的矛盾甚至會導致大規模的混戰——伯羅奔尼撒戰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柏拉圖和亞氏均認為純民主的共和政體是最不理想的政體。
正因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三種政體各自的固有缺陷,它們都會以特定的方式蛻化變質。王權一開始時由有才能的領袖建立,但其繼承人往往容易腐敗,致使“王權”退化為“專制”;于是貴族挑頭,帶領民眾推翻“專制”,建立“少數人的統治”即“貴族制”,然而,貴族的后代玩世不恭,致使“貴族制”退化為“寡頭制”,這就引發平民奮起推翻“貴族制”建立“共和制”,但是,“共和制”下的群眾漸漸互不尊重,“無政府狀態”逐步出現,最終被恢復秩序的“王權”取代。新一輪的“王權——貴族——共和”的循環開始了。單一因素政體的不穩定性是所有政體最不能容忍的先天缺陷,因而有必要尋求一種較具穩定性的政體形式。
什么樣的政體才能擺脫上述循環往復的厄運呢?亞氏認為唯有兼備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因素的混合政體才能防止這種腐敗蛻化。所謂混合政體,就是將三種正宗政體的特點集中在一起,使各種政體要素調整為和諧、平衡狀態的政體。即融合某些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的因素和優點,把君主政體的強有力的政府與共和政體的民眾自由相互結合的政體形式。因為混合政體中任何一種要素都不占優勢,便可以避免單一因素政體形式固有的弊病。同時,混合政體中各種要素互相制約,也就不致于偏重某種要素或倒向某個方面。
二、古希臘政治思維的現代意義
(一) 關于正義
進入現代,啟蒙理性顛覆了等級的差異性人性概念,實質是抽象掉了人生存中事實上的差異性、具體性,以一種抽象的“同質性”人本概念為基礎,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正義,認為維護等級特權是“不義”。“生而平等”、“生而自由”等成為基本原則,我們可以從大量的著作中找到相關論述。到了當代(思想上的后現代主義時期),人的差異性又被充分強調,突出人的身份、欲望、地位等所有方面的多樣性,以此種“多元性”為基礎,強調寬容才是正義的原則,批判權利、理性、道德、經濟等對人的禁錮和束縛。
古代強調縱向的等級差異,將事實提升為思想和政治的不變原則,現代則批判這種等級差異,確立抽象的平等原則,構成一次巨大解放。但它抽象掉了事實上的差異性,只是形式正義。后現代再次批判了這兩種形而上學的人性概念,批判不變的等級差異和抽象的形式平等,而強調人實際生活中的差異性、多樣性和歷史性。但是,這時的差異性已經是一種水平上的差異性,由此,既批判現代的抽象平等性,也批判了古代的等級差異性,同時批判了二者共同的不變的人性概念,是一次新的解放,也是更高層次上的“螺旋式上升”。
(二)關于社群主義
社群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后產生的當代最有影響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社群主義的哲學基礎是新集體主義。它反對新自由主義把自我和個人當作理解和分析社會政治現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變量,而認為個人及其自我最終是由他或他所在的社群決定的。用公益政治學代替權利政治學是社群主義的根本主張。也可以理解為,社群主義是要求返回到古希臘的政治思想。“社群主義”的主要代表有桑德爾、麥金太爾和沃爾策等。
桑德爾從共同體主義的立場出發,認為共同體相對于個體是邏輯在先的。他提出“構成性自我”的概念,認為任何自我、個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社會、民族、傳統等各種觀念、價值和習俗的影響,我們應該把自己看做某一家庭、社區、民族或國家的成員,看做是歷史的承傳者,是某場革命的子女,是某一特定共和國的公民。社會的歸屬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并先在于個體。因此,共同體的善、公共善相對于個人利益而言具有邏輯的先在性關系。
桑德爾反對那種認為正義的思考方式就是接受任何特定共同體之大多數成員在任何特定時刻持有的觀點,反對那種認為任何一項政策只要得到大多數人贊成就應該加以實施的主張。由此,他反對“多數至上主義”和此種意義上的共同體主義。因為多數至上主義僅僅涉及人數的多少,而沒有涉及政策的道德合理性。在桑德爾看來,如果一味地強調集體、公眾對于個體的優先性,那么,人們之間將不存在朋友與陌生人的差別,我們對于朋友的特殊關心將會成為一種對他人的或集體的歧視。因為我們必須服從于集體的意志和利益,并為了達成公益、形成一致的共同體,個體之間就必須保證高度的透明性,彼此之間沒有差別,只有共同的意志和利益。
(三)關于新共和主義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公民共和主義復興運動在西方學術界掀起了陣陣波瀾,出現了一大批“新共和主義者”。他們從各個角度重新回歸、闡釋和發展傳統共和主義中的核心觀念,解構了自由主義與共同體主義之爭,提供了超越自由主義與共同體主義兩分視閾的另一種可能和第三條理論進路。
共和主義思想在當代的重新闡釋和運用及其對共和主義傳統的反思和批判,對當代國家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思想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而有學者認為,共和主義在當代的發展前景是非常樂觀的。
然而,由于時代的差異以及傳統共和主義思想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共和主義在當代的地位也是比較尷尬的。一方面,古典共和主義傳統面臨著來自現代社會的外部壓力。另一方面,古典共和主義思想本身存在著理論缺陷。
D091.2
A
1009-6566(2011)01-0038-03
2010-10-13
寇大偉(1984—),女,河北滄州人,福建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