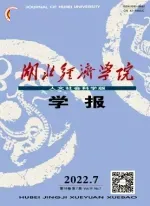論國際化刑事審判機構的管轄權
黃維彬
(河北經貿大學 法學院,河北 石家莊050061)
論國際化刑事審判機構的管轄權
黃維彬
(河北經貿大學 法學院,河北 石家莊050061)
在《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正式生效之后,其常設性國際性刑事審判機構——國際刑事法院也于2002年在荷蘭海牙正式成立。標志著國際刑事司法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它的建立必將對懲治國際犯罪的格局產生重大影響。本文以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其在各方面所涉及國際法問題進行詳細分析。同時,我國雖然沒有加入《羅馬規約》,但應以開放的態度看待國際刑事法院,為在將來適當的時候加入規約做準備。
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羅馬規約
經過國際社會的長期努力,國際刑事法院這一人類歷史上首個常設性的、獨立的國際刑事審判機構于2002年在荷蘭海牙正式成立,國際社會終于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全人類共同利益方面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從人類歷史上首次審判國際犯罪的嘗試到國際刑事法院這一常設、獨立的國際刑事司法機關的最終成立,這中間同樣經歷了復雜而漫長的過程。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與運作,對于懲治與威懾那些危害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嚴重國際犯罪、建立公正而高效的國際刑事審判機制、推動國際社會的進一步法治化以及促進相關的國際法、國際刑法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一、國際刑事審判機構的建立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國際性特設刑事法庭的形式追究戰爭罪犯刑事責任的設想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一戰結束后,戰勝國根據《凡爾塞和約》指控德皇威廉二世犯有違反國際道德與條約義務的嚴重戰爭犯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前蘇聯、美國與英國簽署了《關于起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并以此為依據開始了起訴,審判納粹德國戰爭罪犯的工作。1946年1月19日,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發布 《盟軍最高統帥部通告宣布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懲處日本戰犯。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在國際法與國際刑法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1994年,國際法委員會完成了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起草工作。在1998年6月15日至7月11日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外交大會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得以順利通過并開放簽字。2002年4月11日,隨著第60個國家批準加入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根據規約第126條關于生效的規定,《羅馬規約》于20似年7月11日正式生效,國際刑事法院也于荷蘭海牙正式開始運作。這標志著一個嶄新的國際刑事司法機構的誕生,其對當代國際政治,國際法特別是國際刑法的發展均將帶來深遠的影響。[1]
二、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的涵義及其意義
要同國際犯罪作斗爭,僅有各國國內刑法上刑事管轄權是遠遠不夠的。因此,通過國際法確立起國際刑事管轄權的原則和體系對于有效地同國際犯罪作斗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它是當事國請求引渡的必備條件。在涉及引渡的問題上,國際法要求引渡的請求國必須對案件具有管轄權。如果請求國在沒有管轄權的情況下,徑直被請求國提出引渡請求,一旦被請求國查清事實后,便有權拒絕請求國的引渡求。
第二,它是國際偵查協助中請求國請求偵查協助的必要前提。對一項國際犯案件,一國給予另一國調查取證、采取強制措施等方面的偵查協助,前提是要求請求國對被調查事項或被采取強制措施的人,享有國際法所承認的國際刑平管轄權。
第三,它是保障國家間刑事判決承認與執行的重要條件。作為國際刑事合作一種重要形式,無論是承認還是執行外國刑事判決,都要求判刑國必須享有相應的國際刑事管轄權,否則便無法要求他國承認和執行其判決。
第四,它使國際社會同國際犯罪作斗爭更加快捷有效。通過協調各國刑事管權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國際社會中形成一套統一而完整的管轄體系,可以彌補各國國內刑事管轄在同國際犯罪作斗爭時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從而提高同國際犯罪作斗爭的效率。
三、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的內容
(一)屬時管轄權:國際刑事法院的屬時管轄權,是指國際刑事法院啟用國際刑事法律規范審判嚴重危害國際社會的犯罪行為的時間。依照國際慣例,法律規范的時間效力一般是指法律規范在時間上的有效性,其中包括生效時間、失效時間、變更期間的效力以及法律規范是否溯及既往的問題。[2]
(二)屬地管轄權:國際刑事法院的屬地管轄權也稱管轄權的空間效力范圍,指國際刑事法院可以對發生在何地的犯罪行使管轄權。國際刑事法院作為一個有著獨立法律人格的法律組織,其本身并沒有主權和領土,它所擁有的管轄權等權利實際上是其成員國根據國家主權原則對該法律組織自主作出的權利讓渡。
(三)屬人管轄權:國際刑事法院的屬人管轄權也稱管轄權的對人效力范圍,指可以作為國際刑事法院被告的主體范圍。國際刑事法院的任務是審判個人而非國家,并追究那些犯有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最嚴重罪行的人員的刑事責任。[3]
(四)屬物管轄權:國際刑事法院的屬物管轄權,也稱管轄權的對事效力范圍,指可以由國際刑事法院審判的國際犯罪的范圍。同各國國內法院的對事效力范圍相比,國際刑事法院屬物管轄權的范圍是較為狹窄的。
四、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的內容
(一)屬時管轄權
國際刑事法院的屬時管轄權,是指國際刑事法院啟用國際刑事法律規范審判嚴重危害國際社會的犯罪行為的時間。依照國際慣例,法律規范的時間效力一般是指法律規范在時間上的有效性,其中包括生效時間、失效時間、變更期間的效力以及法律規范是否溯及既往的問題。[4]
作為常設機構的國際刑事法院正式在其規約中規定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這相對于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四個臨時性的國際刑事審判機構而言無疑是一項重大的進步。
(二)屬地管轄權
國際刑事法院的屬地管轄權也稱管轄權的空間效力范圍,指國際刑事法院可以對發生在何地的犯罪行使管轄權。國際刑事法院作為一個有著獨立法律人格的法律組織,其本身并沒有主權和領土,它所擁有的管轄權等權利實際上是其成員國根據國家主權原則對該法律組織自主作出的權利讓渡。同時,根據《羅馬規約》第十二條的相關規定,如果一項規約管轄范圍內的國際犯罪發生在締約國領土之內或發生在締約國注冊的船舶或飛行器上,則國際刑事法院對該國際犯罪可以行使管轄權;如果一項國際犯罪發生在非締約國的領土上或其船舶或飛行器上,且該國聲明接受國際刑事法院對該國際犯罪的管轄權,則法院也可以對該國際犯罪行使管轄權。
(三)屬人管轄權
國際刑事法院的屬人管轄權也稱管轄權的對人效力范圍,指可以作為國際刑事法院被告的主體范圍。國際刑事法院的任務是審判個人而非國家,并追究那些犯有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最嚴重罪行的人員的刑事責任。[5]
(四)屬物管轄權
國際刑事法院的屬物管轄權,也稱管轄權的對事效力范圍,指可以由國際刑事法院審判的國際犯罪的范圍。同各國國內法院的對事效力范圍相比,國際刑事法院屬物管轄權的范圍是較為狹窄的。
五、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法律適用
(一)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的效力依據和先決條件
1.效力依據:國際刑事法院作為主權國家之間通過締結國際公約而成立起來的國際組織,其管轄權的效力來源依據是其基本法律文件等組織章程的規定。因此國際刑事法院是否享有管轄權,取決于其組織章程《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規定。
2.先決條件:根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十二條第二款與第三款的規定,即“如果下列一個或多個國家是本規約締約國或依照第三款接受了本法院的管轄權,本法院即可以行使管轄權:(1)有關行為在其境內發生的國家,如果犯罪發生在船舶或飛行器上,該船舶或飛行器的注冊國;(2)犯罪被告人國籍國。如果根據第二款的規定,需要得到一個非本規約締約國的國家接受本法院的管轄權,該國可以向書記官長提交聲明,接受本法院對有關犯罪的管轄權。該接受國應根據本規約第九編的規定,不拖延并無例外的與本法院合作;[6](3)我們可以發現,國際刑事法院若要對某項國際犯罪行使管轄權,須以犯罪行為地國或罪犯國籍國為規約締約國為前提條件,如上述兩個國家均非規約締約國,而國際刑事法院若欲行使管轄權,就必須要求有關非締約國聲明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
(二)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的對象
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是指國際刑事法院依據羅馬規約管轄涉及特定國際犯罪的案件的權力。根據羅馬規約,法院的管轄權僅限于整個國際社會關注的最嚴重犯罪。具體地說:1.滅絕種族罪:滅絕種族罪又稱滅種罪,是所有“犯罪之王”,可以視為所有危害人類罪中最嚴重的犯罪;2.危害人類罪:危害人類罪,又稱反人類罪或反人道罪;3.戰爭罪;4.侵略罪:侵略是指一個國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或以本決議所宣示的與聯合國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五、我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的立場
作為在成立于新世紀的一個重要國際組織,國際刑事法院必將在未來的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國作為維護世界和平與打擊國際犯罪的重要力量,卻至今仍未加入《羅馬規約》。我國積極參與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創立過程,但在羅馬外交大會上卻對規約投了反對票。
國際刑事法院在規約生效后的短短四年時間內就已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有力地推動了國際刑事司法實踐的發展。考慮到國際刑事法院是在幾個強國和大國的反對之下建立起來的,法院在很短的時間取得上述成績的事實無疑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我們極有必要對我國對待國際刑事法院尤其是其管轄權問題的立場進行反思。首先,檢察官是刑事司法中的重要一環,擔負著調查和起訴犯罪、法律監督方面的重要職能,在保護人權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7]在檢察官獨立調查權的問題上,《羅馬規約》對于檢察官獨立調查權的規定意在盡可能減少政治因素對法院工作的影響,絕非在于干涉國家的內政。其次,對于侵略罪定義中安理會的作用問題仍在制定中,但由于侵略本身是一種國家行為,雖然目前侵略罪的定義各國因此基本認為國際刑事法院對侵略罪的管轄權應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定制約。
結語
國際刑事法院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國際社會對其管轄權等問題自然會存在著一些爭議與不同意見,而真理往往就在各種觀點的碰撞中閃現。我們可以認為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屬性與運作機制的“補充性”特點是符合國際社會現階段的現實的,其最好的實現了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的強制力與各國主權之間關系的平衡。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國際刑事法院能夠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支持而得以正式成立與運作。法院也只能通過其高效而公正的工作來消除一些非成員國的疑慮,從而使得更多的國家加入國際刑事法院。我們也應當承認,國際社會的法治化是大勢所趨,而國際刑事法院正是這一趨勢的典型代表,背離或孤立于這一趨勢之外是不符合我國的長遠利益的。我國應以一種更加開放與自信的態度來處理與國際刑事法院的相關問題,積極為早日加入國際刑事法院創造條件。
注 釋:
① 李世光,劉大群,凌巖:《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評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②謝默夫·巴西奧尼:《國際刑法的淵源與內涵-理論體系》,王秀梅,譯,法律出版社。
③王秀梅:《國際刑事法院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④趙秉志:《國際刑事法院專論》,人民法院出版社。
⑤張旭:《國際刑法論要》,吉林大學出版社。
⑥張景:《國際刑法綜述》,人民法院出版社。
⑦高燕平:《國際刑事法院》,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
⑧ 高銘暄,趙秉志,王秀梅:《國際刑事法院:中國面臨的抉擇》,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張景.國際刑法綜述[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317.
[2][4]王秀梅.國際刑事法院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164.
[3][5]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促進國際刑事法院發展項目辦公室,亞洲法律資源中心.國際刑事法院手冊[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3.
[6]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十二條)[M].
[7]楊宇冠,楊曉春.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