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不忘“形”
——試論文學(xué)方言的漢譯方法
李源園
(福建衛(wèi)生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福建 福州 350101)
得“意”不忘“形”
——試論文學(xué)方言的漢譯方法
李源園
(福建衛(wèi)生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福建 福州 350101)
文學(xué)作品中出現(xiàn)的大量方言一直是譯者需要面對的一大難題。對此譯界長期以來討論和爭議較多的是方言對譯法和口語體譯法。本文通過選取具體語段,旨在分析比較這兩種譯法的得失,初步探討文學(xué)方言漢譯的方法,為翻譯策略的選擇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議。
文學(xué)方言漢譯;方言對譯;口語體譯;方法
方言一詞最早見于希臘語,是指一種語言中跟標(biāo)準(zhǔn)語有區(qū)別,主要用在口語上或口頭上的地區(qū)性或區(qū)域性的語言變體,可以分為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載體,在文學(xué)作品中所使用的方言,對于塑造人物形象、折射地域特色、傳達藝術(shù)效果和增強作品感染力等方面都能發(fā)揮顯著的作用。然而,如何處理文學(xué)作品中的方言,對于譯者來說,卻是棘手的難題。奈達說過,“如果一個文本是以非標(biāo)準(zhǔn)的方言寫成的,譯者就要面對在目標(biāo)語中尋找合適的對等物的困難”。因此,如何讓浩如煙海的一部部優(yōu)秀的國外文學(xué)作品穿越時空,為盡可能多的中國讀者欣賞學(xué)習(xí),便要求譯者要正確處理好原語與目標(biāo)語之間的轉(zhuǎn)換,既忠實于原文,又能將文化風(fēng)格傳遞到位,同時不對作品的文學(xué)性和藝術(shù)性有任何的增減而給讀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難或偏差。基于這一議題,譯界討論得最多的就是以張谷若先生為代表的方言對譯法和韓子滿先生主張的口語體譯法。所謂方言對譯法,就是用譯入語中一種方言的成分來翻譯原文中方言成分的方法。而口語體譯法,則是用比較通俗、口語化的漢語來實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筆者認為,這兩種譯法各有千秋,而要獲得成功的譯文,首先,要吃透原文,深刻把握人物與方言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注重人物所操語言在塑造作品風(fēng)格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即必須得“意”;其次,不可忽視方言本身的功能性,讓譯語盡量貼合原語,即不能忘“形”。在漢譯時不妨結(jié)合方言對譯和口語體譯兩類譯法,對具體語段作具體處理,隨機應(yīng)變,融會貫通。兩者雙管齊下,從而做到“意”“形”結(jié)合,相得益彰。下面通過一些實例,做進一步的比較、分析和說明。
一、以“意”為本 還原風(fēng)格
文學(xué)作品是通過語言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而語言所彰顯的風(fēng)格則是文學(xué)作品的靈魂。對于譯者來說,如何最大程度地還原原著的風(fēng)格是需要在翻譯過程中不斷追求的目標(biāo)。翻譯是對意義的翻譯,更是對風(fēng)格的再現(xiàn)。因此,翻譯文學(xué)作品不僅要忠實于原著的內(nèi)容,而且要忠實于原著的風(fēng)格,這樣才能把原著的真實面貌傳達給讀者。
美國文學(xué)巨匠馬克·吐溫及其代表作 《哈克貝利·芬歷險記》在美國乃至世界文學(xué)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全書由主人公哈克這樣一個十三、四歲的流浪兒以第一人稱的形式敘述故事。該書主要特點便是方言、土語及黑人英語的大量使用,形成了原著濃厚的本土風(fēng)格。對此,張萬里先生的譯本是其中的佳品。他采用通俗簡潔的漢語口語體形式,將原著的這一風(fēng)格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請看下例:
原文:We slept all day,and started out at night,a little ways behind a monstrous long raft that was as long going by as a procession,she had four long sweeps at each end,so we judged she carried as many as thirty men,likely,she had five big wigwams aboard,wide apart,and an open campfire in the middle,and a tall flag-pole at each end.There was a power of style about her.It amounted to something being a raftsman on such a craft as that.
譯文:我們幾乎睡了一整天,到了夜里才動身走,有一排很長很長的木筏,好像一大隊游行的人馬似的,在我們的前面漂著。它每一頭有四根長漿。我們猜想那上面恐怕至少載著三十個人。筏子上搭著五個大窩棚,彼此離得很遠,木筏當(dāng)中還生著一個露天的大火堆,每一頭還有一根大旗桿。它的氣派實在是大極了。在這樣的筏子上當(dāng)個伙計,那才夠神氣的哪。
原文句子短小精悍,淺白通俗,孩子氣十足。再看譯文,同樣簡潔明了,稚氣未脫,一個單純淳樸、想象力豐富的小男孩形象便躍然紙上。
在用詞上,原文除個別詞匯如 monstrous,procession,wigwams等之外,其余都是常用的單音節(jié)或雙音節(jié)詞,long,tall,wide,big等形容詞頻頻出現(xiàn),其中l(wèi)ong甚至重復(fù)了三次。這十分符合哈克的年齡身份與個性特征,譯者在處理這些詞匯時也用了“很長很長的”、“大窩棚”、“大火堆”、“大旗桿”這樣的淺白字眼使得譯文的風(fēng)格與原文環(huán)環(huán)相扣,栩栩如生地刻畫出了人物的形象和特色。
這樣一段孩童式天真浪漫的敘述段落如果用某一特定區(qū)域的方言來譯,會顯得生硬刻意,不如口語體來得平實自然;而如果用標(biāo)準(zhǔn)語來處理,那效果更將大打折扣,風(fēng)格也將與原文相去甚遠,甚至?xí)屪x者覺得難以接受。
二、以“形”補形 語隨其人
方言土語能映襯人物的個性特征,身份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是一種立竿見影的藝術(shù)手段。因此,作者往往會花費很大功夫去模仿人物現(xiàn)實生活中的說話口吻和方式,使每一個人的語言都富有自己的典型特色。這對譯者來說是一項挑戰(zhàn)。奈達曾提出“譯文在譯語讀者中產(chǎn)生的效果應(yīng)等同于原文在原文讀者中產(chǎn)生的效果”。雖然完全的等同是無法實現(xiàn)的,但是譯者至少能夠盡可能增大這種等同的程度。
張谷若先生在這一方面開創(chuàng)性地融合山東方言和北京市井土語翻譯了托馬斯哈代的著名小說《德伯家的苔絲》中的威塞克斯鄉(xiāng)村方言,即采用了方言對譯法,最大程度地實現(xiàn)了意義和形式上的雙重對等。郭著章認為張先生的譯法“不失為傳譯原文中鄉(xiāng)土氣息的成功做法”。(郭著章,1994:746)下面我們來看其中的片段:
原文:“Had it anything to do with father’s making such a moment of himself in thick carriage this afternoon?Why did’er!I felt inclined to sink into the ground with shame!”(Tess P. 58)
譯文:“今兒過晌兒,俺看見俺爹坐在馬車里,出那樣的洋相,他那是怎么啦?是不是叫這檔子事折騰的?那陣兒把俺臊的,恨不得有個地縫兒鉆進去!”(張譯,35)
苔絲是一個生活在英格蘭西南部偏僻落后農(nóng)村,遠離繁華都市的女孩,譯文以北方方言為橋梁展現(xiàn)了其特定的身份背景以及身上濃厚的鄉(xiāng)土氣息,地域?qū)傩阅:鐣?biāo)志清晰。這是因為北方方言使用范圍廣,已被絕大多數(shù)人接受,對于非北方的讀者也不會構(gòu)成理解上的困難。例如,在苔絲的這段話當(dāng)中,譯文采用的是北方方言的人稱代詞“俺”,許多翻譯家在翻譯過程中都使用“俺”來顯示方言與標(biāo)準(zhǔn)語的區(qū)別。類似的還有“爹”這一稱謂。另外,像是“今兒”、“過晌兒”、“這檔子事”、“折騰”等,均是北方方言中十分常見的口語,特別是最后一句“那陣兒把俺臊的,恨不得有個地縫兒鉆進去!”這是苔絲當(dāng)下尷尬心情的自然流露,與原文的風(fēng)格十分貼近,入木三分地刻畫了這樣一個鄉(xiāng)村女孩的形象特征,真正做到了“語隨其人”。而如果放棄方言對譯法,而改用口語體譯法來詮釋這段對話,那么人物的神情口氣便不會那么逼真,她的社會標(biāo)志也不會那么明顯,給讀者留下的印象也不如前者那樣深刻。這便是方言的優(yōu)勢所在。
三、“意”“形”結(jié)合 如影隨形
翻譯是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在達意的基礎(chǔ)之上,找到最佳的措辭來對應(yīng)。鄭振鐸指出,“譯書自以能存真為第一要義……最好一面極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譯文流暢”。林語堂也說過,“譯者不但要求達意,并且要以傳神為目的,譯文必須忠實于原文之字神句氣與言外之意”。可見,翻譯不僅要神似,還要形似。就猶如臨畫一般,神形兼?zhèn)涞牟攀且环卯嫞庑谓Y(jié)合的才是一篇好譯文。在翻譯文學(xué)方言的過程中,如果能將方言對譯法和口語體譯法靈活運用,融會變通,效果會比單獨使用其中一種貫穿到底要來得好。請看傅東華先生對于美國著名小說家瑪格麗特·米歇爾的成名作《飄》的處理:
原文:She could not endure the suspense another moment.
譯文:這個悶葫蘆她再也熬忍不下去了。
原文:They(the Tarleton brothers)…mettlesome and dangerous but,sweet-tempered to those who know how to handle them.
譯文:他哥兒倆……不但頑皮而且惡作劇,可是誰要摸著他們的順毛,他們卻又脾氣好得很。
原文:Although born to the ease of plantation life,waited on hand and foot since infancy,the faces of the three on the porch were neither slack nor soft.
譯文:這兩位哥兒和一位小姐,都生長在殷富舒適的大戶人家,打出娘胎就有人從頭到腳地服侍著,可是他們的面孔都不像嬌生慣養(yǎng)。
從這幾段譯文不難看出,譯者根據(jù)實際情況,對具體的語段采用了不同的譯法。有像前兩段譯文中用方言對譯法譯出“悶葫蘆”、“摸著順毛”的傳神,也有如最后一段采用口語體一譯到底的做法,將讀者帶入原著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使得整篇譯作讀來有一種能屈能伸,搖曳多姿的感覺。
無論是方言對譯法還是口語體譯法,在使用時都應(yīng)該有個度,也就是讀者的接受限度和理解程度,以此為翻譯標(biāo)準(zhǔn),過猶不及。較理想的做法就是將不同的譯法結(jié)合,為我所用,既得“意”,也不忘“形”,讓譯文與原文有一樣的味道和意境,達到翻譯的目的要求,傳達原作神韻,傳播異域文化,譯出更符合中國讀者的譯文。
[1]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3.112.
[2]張谷若,譯.德伯家的苔絲[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
[3]郭著章.語域與翻譯[A].楊自儉,劉學(xué)云.翻譯新論[C].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739-750.
[4]韓子滿.試論方言對譯的局限性——以張谷若先生譯《德伯家的苔絲》為例[J].解放軍外國語學(xué)院學(xué)報,2002.
[5]笪玉霞.《哈克貝利·芬歷險記》原作與譯作語言特色的比較[J].濟南大學(xué)學(xué)報,2002.
[6]谷婷婷.語言變體與翻譯——由《哈克貝利·芬歷險記》看語言變體的漢譯[J].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3.
[7]徐泉,王婷.析傅東華譯《飄》中的歸化翻譯[J].牡丹江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哲社版),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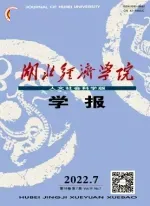 湖北經(jīng)濟學(xué)院學(xué)報·人文社科版2011年5期
湖北經(jīng)濟學(xué)院學(xué)報·人文社科版2011年5期
- 湖北經(jīng)濟學(xué)院學(xué)報·人文社科版的其它文章
- 支架式教學(xué)策略在小學(xué)英語課堂中的體現(xiàn)
——基于兩節(jié)小學(xué)英語骨干教師課堂語料的分析 - 高職商務(wù)英語專業(yè)目標(biāo)能力模塊及實踐教學(xué)模式
- 淺談商務(wù)英語教學(xué)中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yǎng)
- 英語聽力策略與英語聽力理解的關(guān)系探究
——基于對非英語專業(yè)學(xué)生的調(diào)查研究 - 關(guān)于完善中西部民族地區(q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
——基于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研究視角 - 基于“課證融通,理實一體”的高職會計電算化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
——以安慶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