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張愛玲小說創(chuàng)作的獨(dú)創(chuàng)性
劉艷
(荊楚理工學(xué)院 人文社科院,湖北 荊門448000)
試論張愛玲小說創(chuàng)作的獨(dú)創(chuàng)性
劉艷
(荊楚理工學(xué)院 人文社科院,湖北 荊門448000)
文學(xué)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表現(xiàn)為作家在題材的選擇、主題深度的挖掘,創(chuàng)作手法的運(yùn)用等各方面的特性。張愛玲是20世紀(jì)40年代上海有影響的女作家之一。與同時(shí)代其他作家相比,她的小說在主題、題材及創(chuàng)作手法等方面顯得別具一格,使她的小說表現(xiàn)出一種藝術(shù)的獨(dú)創(chuàng)性,而這也是其小說能夠經(jīng)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獨(dú)創(chuàng)性;故事自身;世俗人生;人性;參差對照
文學(xué)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表現(xiàn)為作家在題材的選擇、主題深度的挖掘、創(chuàng)作手法的運(yùn)用等各方面的特性。張愛玲是20世紀(jì)40年代上海有影響的女作家之一。與同時(shí)代其他作家相比,她的小說在主題、題材及創(chuàng)作手法等方面顯得別具一格。
一、讓故事自身去說明
張愛玲反對主題先行,她說:“我認(rèn)為文學(xué)的主題論或者是可以改進(jìn)一下。寫小說應(yīng)當(dāng)是個(gè)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了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1]
為什么她會(huì)如此認(rèn)為?首先我們要明白什么是故事?什么是“故事本身”?漢語中“故事”這個(gè)詞的本來意義是“過去的事”,英語中“故事”(story)一詞的古義是“歷史”或“史話”,在法語中歷史與故事都叫做histoire。可見故事和歷史有著某種聯(lián)系。而當(dāng)我們探究到故事的源頭時(shí),就會(huì)驚奇地發(fā)現(xiàn)故事和歷史原本是一體的,比如在古希臘,希羅多德既被稱作是歷史之父又被稱作是講故事的第一人。所以與歷史一樣,故事就是“過去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張愛玲說“我的本意很簡單,既然有這樣的事情我就來描寫它”。[2]這里“有這樣的事情”顯然是已經(jīng)存在的事,亦即“過去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因而她所謂的“故事”就是“過去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這是故事的本體意義,亦即“故事本身”。
那么為什么“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了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呢?存在主義哲學(xué)家阿倫特認(rèn)為:“任何已經(jīng)做出的或已經(jīng)發(fā)生的行為或事件,都在它們的個(gè)別形式中包含與彰顯其對于‘普遍’意義的分享,并不需要一種不斷進(jìn)行的、吞沒一切的過程,才能變得有意義”[3]。簡言之,即任何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件本身就具有某種普遍的意義。故事既然是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那么故事本身就具有了某種普遍的意義,因而并不需要對故事本身進(jìn)行改變或重建。阿倫特說:“真正的故事和虛構(gòu)的故事的區(qū)別恰恰在于后者是被‘制作’的,而前者不是。”[4]這里“真正的故事”就是“故事本身”,它是包含和彰顯了一定意義的獨(dú)立形式。所以阿倫特認(rèn)為“講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義,但卻不會(huì)犯固定它的錯(cuò)誤。”[5],而“虛構(gòu)的故事”反而會(huì)犯固定事件意義的錯(cuò)誤。所以張愛玲主張讓故事本身去彰顯意義比預(yù)先擬定了主題再去編造故事要好得多,是充分認(rèn)識到了故事的本性的。
故事還具有 “獨(dú)立性”,20世紀(jì)60年代法國敘述學(xué)家布雷蒙(C.Bremond)有一段敘述:“一部小說的內(nèi)容可通過舞臺或銀幕重現(xiàn)出來;電影的內(nèi)容可用文字轉(zhuǎn)述給未看到電影的人。通過讀到的文字,看到的影像或舞蹈動(dòng)作,我們得到一個(gè)故事——可以是同樣的故事”[6]。布雷蒙的這段話揭示出故事具有相對的獨(dú)立性,它不隨話語形式的變化而變化。除“獨(dú)立性”外故事還具有“虛構(gòu)性”,它是對過去已發(fā)生過的事的想象和建構(gòu)。在漢語中,故事除過去的事之外還有“謊言”的意思,比如“你別信他的,他在說故事呢!”英語中故事則另有tale(傳說、故事、謠言)/fiction(虛構(gòu)文學(xué)作品)之意。這種虛構(gòu)不僅是作者對故事的想象建構(gòu),讀者接受故事的過程也是一個(gè)重新建構(gòu)故事的過程。而這個(gè)過程會(huì)直接受到讀者生活經(jīng)驗(yàn)的影響。因此承認(rèn)故事的獨(dú)立性實(shí)際上也就承認(rèn)了生活經(jīng)驗(yàn)在讀者重建故事過程中的首要性。無論話語怎么表達(dá),讀者總是依據(jù)生活經(jīng)驗(yàn)來建構(gòu)獨(dú)立于話語的故事。所以對于同一故事,讀者會(huì)因各自時(shí)代、環(huán)境、經(jīng)歷、文化素養(yǎng)等的不同而獲得不同的感受和啟示。在這個(gè)意義上,張愛玲說“許多留到現(xiàn)在的偉大的作品,原來的主題往往不再被讀者注意,因?yàn)槭逻^境遷之后,原來的主題早已不使我們感覺興趣,倒是隨時(shí)從故事本身發(fā)現(xiàn)了新的啟示,使那作品成為永生的”[7],她的意思是說,因?yàn)楣适卤旧砭哂歇?dú)立于話語之外的意義,所以,隨著時(shí)間的不斷變化,各個(gè)時(shí)代的人會(huì)因各自的現(xiàn)實(shí)狀況對同一故事產(chǎn)生不同的理解和體悟。因此張愛玲反對主題先行堅(jiān)持讓故事本身去說明。
薩特在《什么是文學(xué)?》一文中說:“最初小說家講故事時(shí)自己不介入故事,他也不去思考自己的職能,因?yàn)楣适碌念}材都來自民間傳說,或者總是集體編造的,小說家做的只是把題材化為作品;他加工的材料的社會(huì)性以及這一材料在他動(dòng)手加工之前早就存在著一史實(shí),賦予小說家中間人的角色……他很少創(chuàng)造,他精心雕琢,他是想象的故事的歷史學(xué)家”[8]。張愛玲正是如此,她保持著小說創(chuàng)作的最初本色,她總是采用第三人稱的過去時(shí)態(tài),自己不介入故事,僅僅只是充當(dāng)故事本身的建構(gòu)者,即講故事的人(《傾城之戀》、《金鎖記》皆然)。她從民間取材,寫平凡人的世俗人生;用參差對照的手法精心塑造人物。
二、平凡人的世俗人生
在題材上,張愛玲僅僅選擇平凡人的世俗人生。張愛玲說:“我發(fā)現(xiàn)弄文學(xué)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yáng)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wěn)的一面。其實(shí),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們多是注重人生的斗爭,而忽略和諧的一面。其實(shí),人是為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斗爭的。”[9]
張愛玲說的飛揚(yáng)即革命、壯烈、犧牲。而“安穩(wěn),和諧”即是平凡、普通和世俗。《傾城之戀》寫了一個(gè)離婚后走投無路的女子如何找一個(gè)有錢人再婚的故事;《金鎖記》則講述了小麻油鋪出生的丫頭嫁進(jìn)豪門之后如何生存,并且逐漸占有屬于自己應(yīng)得的財(cái)產(chǎn)的故事。張愛玲認(rèn)為:“強(qiáng)調(diào)人生飛揚(yáng)的一面,多少有點(diǎn)超人的氣質(zhì)。超人是生在一個(gè)時(shí)代里的。而人生安穩(wěn)的一面則有著永恒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wěn)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shí)候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時(shí)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10]。畢竟,對于一個(gè)時(shí)代而言,處在時(shí)代的浪潮之巔的弄潮兒并不多。能夠?yàn)榱俗约簜ゴ蟮睦硐牒统绺叩男叛龆で楦锩⒏矣跔奚娜烁巧贁?shù)。不可否認(rèn),這些人是時(shí)代的英雄,而對于任何時(shí)代,英雄只是整個(gè)時(shí)代的一小部分。對于悠悠歷史而言,絕大多數(shù)時(shí)候是處于安穩(wěn)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的保持者就是那些埋頭于日常生活的普通人,這些人才是時(shí)代的大多數(shù),是歷史的主流,他們構(gòu)成了歷史安穩(wěn)的一面。隨著歷史的不斷進(jìn)步和發(fā)展,各個(gè)時(shí)代的英雄們受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影響和制約,他們的理想和信仰各有不同,然而不論歷史如何變化,普通人的世俗追求永遠(yuǎn)不會(huì)改變,它是一種“永恒”。張愛玲寫普通人的世俗人生,就是為了體現(xiàn)人生安穩(wěn)的一面,也是為了追求“永恒”。
按照張愛玲的說法,“安穩(wěn)”是“永恒的”,它是人的“神性”,亦即“婦人性”。那么何為“神性”何為“婦人性”?神性,即神的性質(zhì),就是神的本質(zhì),由于神是自有永有的源頭,因而神性有與生俱來且永遠(yuǎn)不會(huì)改變的特質(zhì)。“婦人性”是女人的性質(zhì),即女人的本質(zhì),張愛玲所謂的“婦人性”是女性特有的以人的生存本能為基礎(chǔ)的天性,它如神性一樣與生俱來,并且永不改變,它在情欲上表現(xiàn)為對愛情、婚姻、家庭的熱衷;在人格特征上表現(xiàn)為狹隘、自私和柔弱等。事實(shí)上這種婦人性不僅為女性所特有,也是大多數(shù)普通平凡的男性所具有的,而這些男男女女們正是構(gòu)成社會(huì)“安穩(wěn)”的一面的一份子。可見“婦人性”實(shí)質(zhì)上就是“人性”。在散文《燼余錄》中張愛玲反映道:起初得到開戰(zhàn)的消息時(shí),一個(gè)女同學(xué)為戰(zhàn)爭中沒有合適的衣服而發(fā)愁。人們照常地娛樂消遣,不同的是得為柴米油鹽相互爭奪。學(xué)生們因?yàn)椴挥么罂级鴼g蹦亂跳,成天就只是買菜、做飯、調(diào)情,唯一不同的是這種調(diào)情帶有些許悲觀主義的色彩。對此張愛玲發(fā)出感慨:“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xiàng),人類的文明努力想要跳出獸性的圈子,幾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費(fèi)精神么?看來如此。”[11]可見,張愛玲表現(xiàn)人生的“安穩(wěn)”是為了追求永恒,為了追求永恒,她極力寫人的“婦人性”(即“人性”),而且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這種永恒的人性是一種“變異淪落了的人性”。
為此,張愛玲把作品中的人物置身于真實(shí)的充滿各種關(guān)系的世俗人生中,并著重描述與刻劃人性的蒼白、自私、丑陋來強(qiáng)調(diào)真實(shí)的現(xiàn)實(shí)人生。《傾城之戀》白府兄弟當(dāng)初因?yàn)榱魈K帶來的財(cái)產(chǎn)而收留了她,一旦錢財(cái)用完就開始對她冷嘲熱諷,欲將其逐出門戶,而母親對此亦是只求自保。兄妹之情、母女之情蕩然無存。對于范柳原,流蘇只是把它當(dāng)作自己脫離苦海的工具,全無愛情可言。范柳原融中西文化于一身,一方面他親近著舊派淑女白流蘇,另一方面又與熱烈的薩黑夷妮公主打得火熱,他認(rèn)為“婚姻根本就是長期賣淫”[12]。《金鎖記》整個(gè)姜公館充滿了邪惡,這里的人個(gè)個(gè)自私、勢力、缺乏同情心。姜公館里的奴才小雙、鳳蕭雖然身為奴才卻和她們的主子一樣尖酸刻薄、搬弄是非,好窺探別人的隱私。曹七巧是在自私本性驅(qū)使下心靈被嚴(yán)重扭曲的典型,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不惜犧牲女兒和兒子的婚姻甚至人生。季澤是一個(gè)花花公子,在七巧的進(jìn)攻面前雖然有些動(dòng)心,但自私的心理讓他很快壓抑了自己的念頭,因?yàn)樗鞔_知道招惹自家人而且是自己親嫂子的嚴(yán)重后果。
“個(gè)人即使等得及,時(shí)代是倉促的,已經(jīng)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13]面對人性的變異淪落,張愛玲意識到,無論是生死還是愛恨,它們終將讓位于人類生生不已的生活。于是張愛玲把視角投向?qū)€(gè)體存在狀態(tài)的描述和思考:在庸俗的生活和強(qiáng)大的社會(huì)中,人類是應(yīng)在屈服中迷失自我還是在抗?fàn)幹锌隙ㄗ晕覂r(jià)值?人類應(yīng)該怎樣抗?fàn)帲繎?yīng)該確立怎樣的自我價(jià)值?張愛玲在作品中并沒有直接回答,而是通過對飲食男女,尤其是作為弱勢群體的女性的各種生活境遇直接呈現(xiàn)出來。
三、參差對照的手法
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張愛玲喜歡參差對照的寫法,體現(xiàn)在人物身上便是一種“不徹底”性,即人物抗?fàn)幍牟粡氐住T凇秲A城之戀》里,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zhàn)的經(jīng)歷并沒有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zhàn)影響了范柳原,使他轉(zhuǎn)向平實(shí)的生活,終于走進(jìn)了婚姻的殿堂,但婚姻并沒有使他變?yōu)槭ト耍廊槐A糁承┩盏纳盍?xí)慣與作風(fēng)。《金鎖記》里的曹七巧,開始對愛情抱有幻想到最后完全變成金錢的奴隸,她雖有些徹底,然而卻是走向了徹底的病態(tài)而不是徹底的覺悟。事實(shí)上,這與當(dāng)時(shí)主流文學(xué)所提倡的反叛家庭走向革命的徹底性完全不同。
這種“不徹底”還體現(xiàn)在人物個(gè)性的塑造上:張愛玲不用絕對的寫法,在她筆下,好人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好人,壞人也不是大奸大惡的壞人。她追求參差之間顯露人物真性情的審美情趣,這些體現(xiàn)了她獨(dú)特的審美追求。張愛玲從來沒有放棄用雙重的眼光和視角去審視作品中的人物,即使筆下的人物再怎么刻毒、潑辣、窩囊、怯弱,她總會(huì)抓住這些人物心理某一個(gè)瞬間的變化,并且投之以深情的關(guān)照,從而顯示出人物內(nèi)心深處最善良美好的部分,也是人性中最溫柔而且平日里不易流露的部分。這正是“參差對照”美學(xué)的具體表現(xiàn)。
在《金鎖記》中,曹七巧是一個(gè)陰險(xiǎn)狡邪、近乎瘋狂的人物。當(dāng)姜季澤花言巧語想騙取曹七巧的信任時(shí),“七巧低著頭,沐浴在光輝里,細(xì)細(xì)的音樂,細(xì)細(xì)的喜悅……人生就是這樣的錯(cuò)綜復(fù)雜,不講理。當(dāng)初她為什么嫁到姜家來?為了錢嗎?不是的,是為了見季澤,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澤相愛”,七巧非但沒有憤怒,而且她的內(nèi)心變化分明體現(xiàn)出她對真愛的渴望。這一點(diǎn)已足以讓讀者為之動(dòng)容。最終七巧拒絕了季澤,“她到了窗前,揭開了那邊上綴有小絨球的墨綠洋式窗簾,季澤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長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風(fēng)像一群白鴿子鉆進(jìn)他的紡綢褂里去,哪兒都鉆到了,飄飄拍著翅子。”季澤畢竟是七巧人生中唯一愛過的而且希望與之共度一生的人。所以在他離開后,七巧會(huì)站在窗前留戀地看著他漸漸遠(yuǎn)去。可見此時(shí)的七巧是多么的痛苦、后悔而又無奈!
張愛玲說:“極端病態(tài)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shí)代是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么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14]對于普通平民而言,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壓力是如此沉重,幾乎讓人無暇顧及整個(gè)時(shí)代與社會(huì)的命運(yùn)。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一種平常的心情,去承擔(dān)和忍受。張愛玲所描寫和刻畫的就是這些人。
正是因?yàn)閺垚哿嵩谥黝}、題材、創(chuàng)作手法等方面的特別追求,使她的小說表現(xiàn)出一種藝術(shù)的獨(dú)創(chuàng)性,而這也是其小說能夠經(jīng)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1][2][7][9][10]張愛玲.自己的文章[A].張愛玲典藏全集[C].作家出版社,2004-11.
[3]Hanna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M].enlarged edition,London, Penguin Books,1977.64.
[4]阿倫特.竺乾威,譯.人的條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6.
[5]阿倫特.王凌云,譯.黑暗時(shí)代的人們[M].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97.
[6]申丹.敘述學(xué)與小說文體學(xué)研究[M].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8.20.
[8]薩特.什么是文學(xué)[A].沈志明,艾珉.施康強(qiáng).等譯.薩特文集[C].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194.
[11]張愛玲.燼余錄[A].張愛玲典藏全集[C].469.
[12]張愛玲.傾城之戀[A].張愛玲文集(第二卷)[C].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2-07,(1):72.
[13]《傳奇》再版本序言[M].上海雜志社,1944-09.
[14]張愛玲.自己的文章[A].張愛玲典藏全集[C].508.
[15]張愛玲.金鎖記[A].張愛玲文集(第二卷)[C].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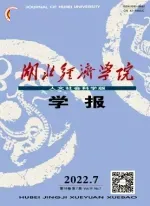 湖北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學(xué)報(bào)·人文社科版2011年5期
湖北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學(xué)報(bào)·人文社科版2011年5期
- 湖北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學(xué)報(bào)·人文社科版的其它文章
- 支架式教學(xué)策略在小學(xué)英語課堂中的體現(xiàn)
——基于兩節(jié)小學(xué)英語骨干教師課堂語料的分析 - 高職商務(wù)英語專業(yè)目標(biāo)能力模塊及實(shí)踐教學(xué)模式
- 淺談商務(wù)英語教學(xué)中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yǎng)
- 英語聽力策略與英語聽力理解的關(guān)系探究
——基于對非英語專業(yè)學(xué)生的調(diào)查研究 - 關(guān)于完善中西部民族地區(q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
——基于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研究視角 - 基于“課證融通,理實(shí)一體”的高職會(huì)計(jì)電算化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
——以安慶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