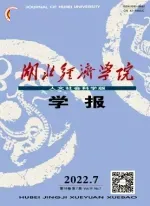“信達雅”對現代翻譯的啟示
彭珊珊
(廣東女子職業技術學院 外語系,廣東 廣州 511450)
“信達雅”對現代翻譯的啟示
彭珊珊
(廣東女子職業技術學院 外語系,廣東 廣州 511450)
“信達雅”三原則在中國翻譯界的是非爭論從未停息過。在壞“譯本”充斥市場的今天,重新提倡“信達雅”,并賦予其新的內涵,即“準確、通順、簡明”,或“信達簡”,對現代翻譯危機有警醒之效。而要做到“信達簡”,要從外語水平、工作態度和中文水平三方面努力。
信;達;雅;翻譯
中國近代翻譯家嚴復在其《天演論﹒譯例言》(1896年)中提出“信達雅”三原則[1],來概括翻譯活動要達到的標準,從此這三原則被中國翻譯界奉為“金科玉律”。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理論潮水般涌入中國,“信達雅”不斷受到各種批評,甚至有人認為“信達雅”該退出翻譯的舞臺。可是,在筆者看來,通過重新詮釋,“信達雅”仍是現代翻譯實踐最基本和最實用的準則。
一、現代翻譯的危機
中國的翻譯在世界上有顯著的地位,歷史悠久,數量驚人。《禮記》已有關于翻譯的記載。從漢代佛經的翻譯至今,中國翻譯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譯活動和理論研究從未停止過。尤其是近幾十年,大量的譯本涌現,其中不乏優秀的作品,能達到“信達雅”的標準;但不能否認的是其中有相當多的作品是不合格的。季羨林先生曾把這些不合格作品分為三類:能達到“信達雅”的譯本可算是上等作品;“信”、“達”夠,“雅”不足,或是“達”、“雅”夠,而“信”不足屬于中等作品;“信達雅”都做不到就是下等作品了。[2]這里講的不合格作品就指這些中下等作品。“雅”在翻譯中頗有爭議,而“信”,就是要忠實于原文,是“達”和“雅”的基礎,也是翻譯最起碼的準則,無“信”就談不上翻譯,這也是嚴復把“信”放在三原則之首的重要原因。目前翻譯界的不少譯本,且不說譯本的“雅”和“達”,單是“信”都做不到;翻譯變成隨意創作,說翻譯界危在旦夕就不是聳人聽聞了。因此,我們在研究和學習西方翻譯理論的同時,不應徹底否定中國傳統的翻譯理論;而翻譯實踐首先必須腳踏實地,做到“信達雅”以盡翻譯之能事,至少“壞”譯本可以少些。
二、“信達雅”的再理解
嚴復的“信達雅”當時是白話文譯文的衡量標準,其中“信”就是忠于原文;“達”是文字表達;“雅”是要有文采。在現代翻譯實踐中,賦予其新的內容和解釋,“信達雅”仍舊是成立的。
(一)先說“信”。“信”可解釋為“準確”,是翻譯之本,就是一個詞或一句話究竟是什么意思,要準確地轉達出來。[3]例如:They each had a strong will and those wills sometimes clashed.譯本有二,其一:他們兩個都是很有主見的人,有時候他們的意見會相左;其二:他們每一位都具有堅定的意志,有時他們的意志難免發生沖突。其實原文的strong will不是“主見”之意,而是“堅強的意志”,從而顯出clash這個詞用得頗具力量。譯本一錯誤的根源是譯者沒弄懂strong will以及整個句子的真正含義,因而不能準確地翻譯。當然,準確不一定要“硬譯”,而 “意譯”也不一定不準確。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例子:Well,monks had a history of such things.有人譯為:嗨,和尚們有干這種事情的歷史。有人譯為:嗨,和尚干這種勾當由來已久。顯然,前者應該算“硬譯”,基本傳達了原意,目前十分流行,但顯得生硬;后者是“意譯”,但更接近原文的含義,值得推崇。再看一例:Nowadays,however,the crystal-ball promises of world peace are not so clear.原譯為:然而現在,像水晶球一樣透亮的世界和平前景卻并不那么光明了。“像水晶球一樣透亮的世界和平前景”拘泥于詞語的字面意義,是完全的“硬譯”。改譯為:然而,現在,可以預見的世界和平前景卻并不那么光明了。改譯的譯者根據語境對詞義進行引申,用“意譯”準確轉達了原文的真實含義。
(二)再說“達”。“達”可理解為“通順”,就是說理論事,邏輯無誤;文法無誤,符合漢語規范。“通順”的標準看似一般,其實對譯者的要求很高,譯者要準確表達原文的基礎上,發揮對漢語的理解和遣詞造句的能力,把流暢漂亮的譯文呈現出來。
[4]在“達”這個問題上,目前特別要避免照搬西方文字的句法結構。我們來看下面的兩組譯文:In the afternoon rush of the Grand Central Station his eyes had been refreshed by the sight of Miss Lily Bart.一種譯文是:在中央火車站下午的人流中,他的兩眼一亮,被麗莉·巴特小姐的身影迷住。另一種譯文是:在中央火車站午后的旅客洪流中,他一眼瞥見了麗莉·巴特小姐的身影,頓時覺得眼目清新,精神為之一振。被動式是英語句式,雖然在現代漢語中已基本習以為常,但好的譯者還是盡量避免使用,為了使譯文更符合漢語的規范,第二種譯文的譯者把內在的主語拉出來,對sight和refresh稍加發揮,使譯文更加傳神。 再看這句的兩組譯文:It noted that being overweight has been linked to sickness and death from such diseases as high blood pressure,diabetes and heart disease.一種譯文是:報告指出,過胖與疾病及諸如高血壓和糖尿病引起的死亡有關。另一種譯文是:報告指出,過胖容易引起疾病,容易導致由高血壓、糖尿病和心臟病等引起的死亡。前者照搬原文句子結構,用了不符合漢語習慣的長定語,行文不自然,令人費解;反之,后者符合漢語習慣,清晰易懂。
(三)最后說“雅”。“雅”在文言文中容易鑒別,在白話文中則很難成為一個統一的標準。[3]依筆者之見,“雅”在現代白話文中可理解為“簡明”。這是因為白話文以口語為根本,口語往往啰嗦,規避啰嗦而求“簡明”應該是白話文的努力目標。我們看下面這段話:Examine for a moment an ordinary mind on an ordinary day.The mind receives a myriad of impressions-trivial, fantastic,evanescent,or engraved with the sharpness of steel.一種翻譯是:把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內心活動考察一下吧。心靈接納了成天上萬個印象——瑣碎的、奇異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鋒利的鋼刀深深銘刻在心頭的印象。另一種翻譯:且慢,審視一下一個普通日子里的一顆普通的心靈吧。心靈接受無數的印象——瑣碎的、奇妙的、易逝的,或是刻骨銘心的。兩種譯文中前者重疊字太多,文字不簡練,且意思也不明了。相反,后者比前者少了21個字,簡練明快。
三、“信達雅”對現代翻譯的啟示
“信達雅”新的內涵解析“準確、通順、簡明”使其變成了“信達簡”,如果人們在現代翻譯中能遵照這三個標準進行翻譯實踐活動,相信我們會看到更多好的譯作。“譯而信”需要兩個基本條件,即外語水平和工作態度;“達和簡”則關鍵需要出色的中文水平。
(一)外語水平
說到學習外語,有兩種態度不可有:一是認為外語很神秘,無法學好;另一種是認為外語很容易,不費力氣就能學好。正確的態度是:天賦和勤奮不可缺。此外,外語水平有層次差別,外語學習者不能認為自己有很高的語言天賦,基本掌握了某一種語言就能勝任翻譯了。相反,外語水平的每個層級都有一個坎,只有付出艱辛的努力,跨過一個個坎,外語水平才能不斷提高。在此,筆者特別要提出中國人在國內學習英語的問題。由于英語和漢語分屬不同的語言體系,而國內缺乏良好的英語環境,國人學習英語比較困難,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們要探索英語作為外語在中國的教與學的策略,培養更多的優秀英語人才,只有這樣,我國的總體翻譯水平才有保證。
(二)工作態度
翻譯的工作態度不是天賦問題,而是認識問題。嚴謹和謙虛的翻譯態度是好譯作不可或缺的條件。[2]原文不懂的地方,一不請教人,二不查字典,胡亂翻譯,怎能有“準確”可言,這種態度不行。當年趙景深教授把milky way(天河,銀河)譯為“牛奶路”受到了魯迅先生的譏諷,成為翻譯界的笑柄。今天這樣的例子也數不勝數。以下兩個英語句子看起來很簡單,但它們的譯文卻大錯,結果弄出了笑話。Shakespeare has been interested in his family’s arms./莎士比亞對他家族的武器感興趣。Shakespeare struggled hard for his father’s coat of arms./莎士比亞為父親的上衣拼爭。這兩個句子的問題在于沒弄懂arms和coat of arms的意思。這兩個詞的意思一樣,都作“紋章”或“徽章”講,而不是“武器”和“上衣”。英語里一詞多義的問題對中國人而言是個永遠不可大意的問題。譯者只要認真查字典,并虛心請教有經驗的人,恐怕不會鬧這個笑話。這兩個例子足以說明翻譯工作態度的重要性。
(三)中文水平
著名的語言學家呂叔湘在談及翻譯的體會時說過,譯者翻譯英文需要七分英文三分中文。但也有很多行內人士認為英譯漢需要七分中文三分英文。筆者在此不想探討哪種說法更準確,只想籍此說明漢語水平在翻譯中的重要性。看懂的英文不能用中文準確生動地表達出來,譯作一定不能吸引漢語讀者。相反,中文水平佳的譯作能淋漓盡致傳達原文的含義和神韻。例如,下面這段話的漢譯就好像中文寫作,而非翻譯,體現了作者對原文透徹的理解和良好的中文駕馭能力。She remained motionless,as if she had not heard him.Then she snatched her hands from his,threw her arms about his neck, and pressed a sudden drenched cheek against his face./她一動不動,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過了一會,她掙脫了雙手,一把抱住他的脖子,忽地把她濕透了的臉蛋兒偎在他的臉上。原文是兩個句子,譯文為了強調一對情人難分難舍的情景,把英語中常見的then譯為“過了一會”,讓女主人公的動作有了停頓感,使下面幾個動作“掙脫”、“一把抱住”和“偎”有層次地加強,翻譯得很到位。
四、結語
現代翻譯中下等譯作敗壞了我國的翻譯風氣。有人建議加強翻譯評論,加強監督來克服翻譯的危機,但這免不了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依筆者之見,在講求效率的現代社會,譯者們都遵守最基本的“信達簡”翻譯三準則,不斷提高外語和中文水平,踏踏實實翻譯,這才是改變壞譯風的根本。
[1]黃嘉德.翻譯論集[M].上海:上海西風出版社,1939.
[2]季羨林.季羨林談翻譯[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3]馮世則.翻譯匠語[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
[4]蘇福忠.譯事余墨[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