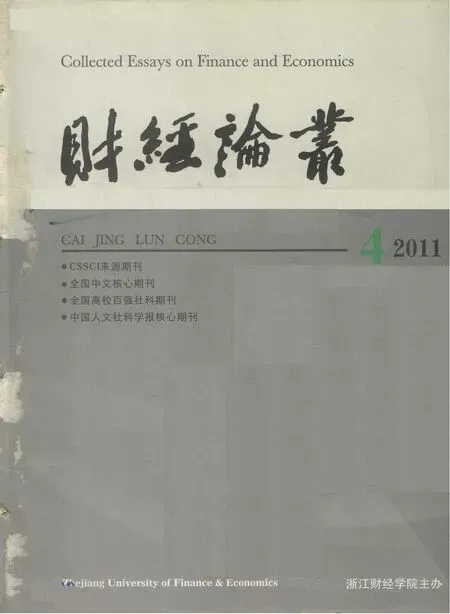財政分權、轄區競爭與地方政府投資行為
申 亮
(山東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山東 濟南 250014)
一、引 言
我國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在保持著改革前行政隸屬關系的同時,還具有了一定的財政契約關系。地方政府成為擁有獨立經濟利益的政治組織,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自己的財政收入并負擔相應的財政支出責任。這種財政分權改革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激勵強度[1][2],促進了經濟增長[3][4][5],從而使各個地方政府產生了強烈的財政競爭。同時,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的考核、任命仍然具有絕對的權威,并通過設定就業、增長和稅收等顯性經濟指標作為地方政府官員晉升的標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一競爭[6][7]。而這兩個方面轉化為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卻是一致的,都體現為對GDP的競爭[8]。
地方政府投資是地方政府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手段,也是地方政府間競爭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作為 “有限理性”的經濟人,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其中既包括地方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也包括政府官員的政治利益。這導致了地方政府投資行為的復雜性。金志云[9][10]、杜超[11]對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從博弈論的角度進行了初步分析,本文運用博弈論分析工具進一步構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投資博弈模型,研究在財政分權、轄區間競爭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及其經濟效應。
二、模型說明
假設在一個封閉式的經濟體,整個經濟由兩個地方政府組成。地方政府i(i=1,2)的核心目標是促進轄區經濟增長,其主要手段是運用地方政府投資。假設某產業市場容量有限,在沒有其他投資主體參與的情況下,兩個地方政府對該產業進行投資,設地方政府i的投資量為gi,則全社會投資總量為G(G=g1+g2)。很明顯,該產業的市場容量就是該產業的市場需求,任一地方政府的投資收益都會受到該產業市場容量的限制。假設該產業的市場需求函數為:

其中,Q為該產業的市場容量,它通過全社會的總投資G來實現;p為當市場需求為Q時的產品價格。
假設地方政府1和地方政府2對該產業的投資可以完全相互替代。這樣,當該產業的市場需求量為Q時,設單位投資產生的產量為k(k>0),則地方政府i投資gi所產生的產量為kgi,全社會總投資G的產量為:

假設,

此時,全社會總投資所產生的產量正好為產品的市場需求量,該產業市場實現均衡。
假設c(c>0)為投資的單位成本,地方政府i投資gi所產生的收益為πi,則πi=kgip-cgi。聯立 (1-3)式,可得

假設全社會投資G所產生的收益為π,則有

下面我們分別從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之間關于投資的博弈,來分析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結合我國現行的財政體制,在上述政府間投資博弈中,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不考慮轄區競爭,只考慮地方經濟增長目標時的博弈;一種是既考慮轄區競爭,又考慮地方經濟增長目標的博弈。
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投資博弈
(一)經濟增長為唯一目標時的模型
在這個博弈中,作為理性的 “經濟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會從自身收益最大化出發來確定地方政府的投資量。
從中央政府的收益出發,全社會的投資量G應該實現社會收益最大化。根據 (5)式,有

由?π/?G=0,得到中央政府希望的最優投資量為G*,

但是,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地方政府的投資要實現地方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即,

由 ?πi/?gi=0, 得

同理,對地方政府j有

聯立 (7-8)式,可得地方政府1與地方政府2在分散決策時,全社會的投資量G′為,

比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決策,可得:
(二)加入政治競爭目標時的模型
下面我們再考慮加入轄區間政治競爭目標的情況。由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任命有著絕對的權威,對地方政府而言,除了實現轄區經濟利益目標外,地方政府官員還處于一個政治晉升博弈中,即努力實現中央政府的政績考核目標,而獲得政治晉升。現階段,中央政府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關鍵指標主要是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等顯性指標,這使得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成為地方政府官員目標函數的重要組成部分。假設中央政府對兩個地方政府的考核主要通過經濟業績來進行,經濟業績更好的地方官員將在競爭中勝出。每個地方政府的經濟業績以yi表示,yi采用下式表示:

其中,πi表示地方政府投資所得到的經濟業績,πi采用 (4)式計算;gi表示地方政府j的投資量;r表示地方政府j的投資對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的邊際影響,為簡化問題,我們假定|r|<1。當r≠0時,表示地方政府i的投資行為對地區j有 “溢出效應”。當0<r<1,此 “溢出效應” 為正,說明地方政府i的投資行為有助于地區j的經濟增長;當-1<r<0,此 “溢出效應”為負,說明地方政府i的投資行為不利于地區j的經濟增長;當r=0,“溢出效應”不存在,說明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對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不產生影響。ei是一個隨機擾動項。
已知地方政府間政治競爭的規則是:如果yi>yj,那么官員i將得到晉升,假設獲得晉升給地方政府官員帶來的收益為v(v>0),此時地方政府官員i的總收益為晉升收益和投資帶來的直接收益之和v+πi,而地方政府官員j不被提升,僅獲得收益為πj;如果yi<yj,地方政府官員i將未被提拔,獲得收益僅為直接投資收益πi。則在加入政治競爭的模型中,地方政府官員i的收益表示為:

其中,Prob(yi>yj)表示yi>yj的概率。
對地方政府官員i而言,要實現自身收益最大化,即

由 ?Ui/?gi=0 得,

同理,對地方政府官員j而言,也有,

聯立 (12-13)式可得,加入政治競爭的模型中,地方政府官員為了達到提拔的目的,兩個地方政府各自決策所確定的最優投資量總和為,

由函數的對稱性,可知?Prob(yi>yj)/?gi=?Prob(yj>yi)/?gj,所以上式可寫為,

比較 (6)、(9)、(14)式,可得:

這說明,加入政治競爭的晉升收益后,地方政府官員的投資激勵會加強,地方政府的投資總量比只考慮經濟增長目標時要更大。
四、地方政府之間的投資博弈
(一)經濟增長為唯一目標
在僅考慮經濟增長目標的模型中,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分兩種模型:一種是分散決策模型,兩個地方政府以達到自身的收益最大化為目標,各自獨立決策;另一種是合作模型,兩個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決策最優投資量,以期達到雙方收益之和最大化。下面我們對這兩種模型分別予以討論。
1.分散決策模型。在分散決策模型中,如果兩個地方政府同時投資于某一產業,由于假設其投資是可以完全替代的,即假設其投資環境等外部因素都一樣,此時,地方政府取得的投資收益與它們的投資先后順序有關。如果兩個地方政府同時投資該產業,雙方的決策就構成了cournot博弈;如果一方搶先投資該產業,另一方看到對方投資獲益以后跟著投資,雙方的決策就構成了序貫理性的stackelberg博弈。
在cournot博弈模型中,根據 (4)式,地方政府1與地方政府2的收益函數分別為,


在stackelberg博弈中,我們假設地方政府1搶先投資,地方政府2跟隨投資。我們采用逆向歸納法求解如下:
地方政府2的收益函數π2=kg2[a-bk(g1+g2)]-cg2,
由 ?π2/?g2=ka-k2bG-c-bk2g2=0 得到 ,
結論2:地方政府2對地方政府1的反應函數為

由結論2可知,g2是g1的減函數,這表明,在地方政府1搶先投資下,地方政府1的投資越大,地方政府2的投資就越小。在極端情況下,如果地方政府1的投資占據了整個產業市場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地方政府2就會選擇不投資。
將 (15)式代入地方政府1的收益函數π1=kg1[a-bk(g1+g2)]-cg1,可得

2.合作決策模型。在合作決策模型中,為了避免雙方惡性競爭,浪費資源,兩個地方政府將合作決策,以實現雙方收益總量最大化。即要求

聯立 ?π/?g1=0, ?π/?g2=0,g1=g2可得結論 4。

3.模型比較
從 (Ⅰ)可看出,地方政府之間合作決策獲得的投資總收益最大,地方政府一方搶先投資的stackelberg博弈獲得的總收益最小。但是,對單個地方政府而言,搶先投資的一方獲得的收益最大,等同于合作決策時獲得收益,隨后投資一方獲得收益最小。
從 (Ⅱ)可看出,地方政府在stackelberg博弈中的投資總量最大,在合作博弈決策中的投資總量最小。對單個地方政府而言,采取搶先投資策略的地方政府所需投資量最大,合作決策中所需投資量最小。
可見,地方政府采用合作決策時,所需投資最小,取得的投資收益最大,是一種 “雙贏”的選擇。但是,現實中這種選擇卻很難出現,反而經常出現地方政府搶先投資,或者地方政府獨立決策而盲目投資、重復投資,不僅形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而且,取得的投資收益也并非最佳。顯然,這種現象單純從經濟利益的角度是無法解釋的,我們必須從地方政府的第二種收益,即政治利益出發來作出合理解釋。
(二)加入政治競爭目標
政治競爭的特征是只有有限的官員可以獲得提升,一人所得構成另一人所失,因此博弈參與人面臨的是一個零和博弈。這種零和博弈決定了地方政府合作決策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同時,如果某一地方政府決策時不考慮另一方的決策,由此可能造成雙方收益均等,將不利于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晉升。因此,加入政治競爭目標后,地方政府會極力避免出現cournot博弈,雙方面臨的只能是stackelberg博弈。
由上述分析可知,考核地方政府的經濟績效yi滿足 (10),即

假設隨機擾動項ei與ej相互獨立,服從分布F,則 (ei-ej)服從一個期望值為0的對稱分布F,相應的密度函數為f。根據政治競爭的規則,地方政府i被晉升的概率為,

則地方政府官員i的收益可表示為:

對地方政府官員i而言,要實現自身收益最大化,即

由 ?Ui/?gi=0 得,

在均衡條件下,上述一階條件變為:

從 (16)式可看出,gi是關于r的減函數。這表明,在地方政府政治競爭博弈模型中,r越小意味著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越大。即某一地方政府投資決策對其他地區存在消極 (積極)影響,即-1<r<0(0<r<1),這種影響將會加強 (削弱)該地區的投資激勵。這是因為,政治競爭讓參與人關心的只是自己與競爭者的相對位次,在公平競爭中獲勝固然可以增加自己的優勢,給對手制造障礙、減少對手的收益也可以實現競爭優勢。因此,地方政府更愿意實施分散決策,對可能形成“雙贏”的合作決策則激勵不足。換句話說,政治競爭博弈是排斥地區間合作的。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上,本文運用博弈論工具分析了我國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研究表明:在財政分權改革下,地方政府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很強的投資沖動,投資規模超過中央政府希望的最優投資規模,尤其是在當前依然是以經濟增長為主要考核指標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下,這一投資沖動更加突出。而且,經濟考核指標激勵愈強,地方政府投資愈加偏離中央政府的最優投資規模。不僅如此,地方政府之間的經濟競爭進一步推動地方政府投資規模的擴大,加上政績考核的激勵,地方政府之間不僅難以形成區域間合作,而且為了得到政治晉升,形成了一輪又一輪的投資競爭,造成了資源浪費的同時,也影響了全社會的發展質量。
2011年是我國 “十二五”計劃的開局之年,又逢地方政府干部集中換屆峰值期,從已經公布的數據來看,各地方政府制定的 “十二五”經濟增長年均目標大多超過10%,遠勝中央政府制定的7%的平均增長目標。考慮到地方政府設定預期目標多留有余地,實際增速可能會更高。如果沒有有效措施 “減壓”,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助推下的經濟快速增長及由此帶來的經濟過熱可能造成“十二五”期間最大的經濟風險。
因此,完善我國現行財政體制和改革以經濟指標為中心的政績考核體系,以此來矯正地方政府投資行為成為當前經濟政治改革中一項迫切的任務。
(一)完善我國現行財政體制,確定合理的地方政府激勵機制
1.合理劃分政府間收支責任。相比取得的財政收入,中國地方政府承擔了過多的財政支出責任。應科學劃分政府間財權和事權,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增強地方政府的服務功能,減弱地方政府的經濟增長壓力。
2.健全地方財政民主,增強財政透明度。創造條件讓公眾能夠監督政府,讓公眾能通過有途徑表達所需要的公共產品數量、質量以及種類,促使地方政府根據轄區內公眾的不同偏好,提供最有效率、也最能滿足居民需求的公共產品組合。通過增強地方政府的財政透明度,規范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減少預算的隨意性。
(二)建立 “以人為本”的政績考核體系
在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中,不僅要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總量,而且要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社會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公平正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反映到體系中,引導政府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民生改善上來。完善官員的責任追究制度,加入官員任期穩定性要求。在考核方式、考核程序、考核方法、考核結果上要增強透明度,加大群眾滿意度在考核評價中的比重,促進政府工作效率的提升。
[1]Jin,H.,Yingyi Qian,and Barry R.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9,2005,pp.1719-1742.
[2]Zhang,Xiaobo,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China: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Inequality.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7,Forthcoming.
[3]Xie,Danyang;Zou,Heng-fu;and Davoodi,Hamid,1999,“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45:pp.228-39.
[4]Qian,Yingyi,Gerard 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1998,1143-62.
[5]陳抗,Arye L.Hillman,顧清揚.財政集權與地方政府行為變化 [J].經濟學 (季刊),2002,(1):111-128.
[6]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7,(7):36-50.
[7]王文劍,覃成林.財政分權、地方政府行為與地區經濟增長:一個基于經驗的判斷及檢驗 [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7,(10):60-64.
[8]張軍.中國經濟發展:為增長而競爭 [J].世界經濟文匯,2005,(4).
[9]金志云,趙強,龐笑萌.地方政府投資支出競爭的博弈分析及機制設計 [J],江西社會科學,2008,(4):75-79.
[10]金志云.雙重激勵下的地方政府間競爭行為的博弈分析——以投資支出競爭 [J].安徽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2(2):123-127.
[11]杜超,焦文超.財政分權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實現經濟增長的模型研究 [J].統計與決策,2010,(7):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