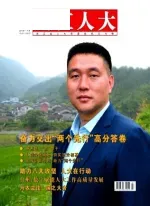鄉村危局
■黃 震
鄉村危局
■黃 震
已是深秋時節,雨連續下了多日,絲毫沒有停歇的意思。通往沙了村的路泥濘難行,兩邊的茅草高過人頭。車子在雨霧里繞行,最后停在了一處山坳。文成峃口鎮人大副主席蔡永茂說,沙了村到了。山谷里滿是雨霧,沿著山坡立著幾排黃泥瓦房。沙了村原屬于公陽鄉,在去年的撤鄉擴鎮中,并到了峃口鎮。
沙了,最后的村民
整個村子在雨水中闃寂無聲,逼仄的青石路上長滿了苔蘚。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傾頹的民居。許多房子的屋頂上到處是大洞,地基傾斜,院墻坍塌,褐色的橫梁浸泡在雨水中,搖搖欲墜。一處斷墻角落里露出倒塌了一半的鍋灶,上面有落滿灰塵的鍋蓋和鐵鏟,依稀透露出昔日主人在這里生活的氣息。
高高聳立在山坡上的柿子樹,落光了葉子,掛著紅色的果實,是這個村莊唯一的一抹亮色。蔡永茂在公陽鄉做過十幾年的鄉干部,對這一帶非常熟悉,他說:“沙了村原有80多戶人家,300多人口,如今只剩下30多人,基本都是老人,青壯年都出去了。”
我們敲開村干部葉昭炎的家門,里面灰暗潮濕。西首的土篾墻塌了一半,露出幾根孤零零的木柵。聽到下面的聲響,老葉從樓上下來,看到我們后他面露驚愕。平時這個村基本沒有訪客,偶爾鄉干部下村會到老葉家里歇腳。老葉今年已經77歲了,鄉里一直想找個人接替他的工作,但是整個村莊實在找不出年輕一點的人。由于長年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地方,老葉聽不懂普通話,我跟老葉的對話基本要靠當地干部翻譯。
老葉家原本是個大家庭,有4個兒子,7個孫女,1個孫子。2個兒子在寧波打工,還有2個在溫州,孫輩也跟著出去了,平時基本不回來。家里就剩他一個人,守著一畝田,每年可以收五、六百斤谷子,基本夠他一個人吃。
房子已經長年沒有維修,屋頂上的瓦片被臺風吹得七零八落。站在老葉家的頂樓,可以見到屋頂滿是星星點點的漏光。兒孫們不常回家,但他們的房間還保持著原樣,老葉會定期打掃。幾處漏風的地方也小心地用塑料畫紙糊好,隨時準備迎接兒孫們回家。
村里的小學早已廢棄,院子改成了豬欄,雜草叢生。在老葉的講述中,村莊也曾經有過繁榮的往昔。老屋前面的樹下就是村莊的中心。夏天,每到吃午飯,這里就擠滿了人,男人、女人一邊說笑,傳著閑言碎語,一邊捧著飯碗就著腌菜吃白飯。晚上,這里是歇涼的中心,到了半夜,還有人在這里搖著蒲扇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
當地官員說,對于這些留守的老人來說,他們的生活實際上比20年前更苦了。20年前,村里的老老小小都守著這片山坡,至少精神上有慰藉。現在觸目之處,少有人跡,買點油鹽醬醋也得跑到十幾里外的公陽。
蔡永茂在這里做了10多年的鄉干部,對這里的山山水水有感情。他說:“以前路還沒有修好,下鄉經常是一雙膠鞋一個手電筒,蒙蒙亮出發,天擦黑才能回來。現在路好了,下鄉方便了,但是工作的對象卻沒有了……”言談間,蔡永茂神色有些落寞。
出村的時候,一位老婦跟蔡永茂打招呼。老人正在吃中飯,桌上放著一碗腌菜頭,另一碗是黃豆。家里的黃泥地因為少有人走,已經長滿了苔蘚。老人在家獨居,兒女們不放心,給她留下一只手機。老人只會接,不會打。
當地干部介紹說,因為靠近公路,沙了村還不算最窮的。山上有一戶人家,女的40多年前從四川蓬安嫁到這里,已經有20多年沒有回去過,因為付不起盤纏。
對于沙了村來說,這些老人就是村莊最后的居民,他們走后,村莊也將不復存在。從這里走出去的年輕人,他們不可能再回來了。
馱尖,高山之巔的村莊
沙了村的衰敗多少讓人神傷。當地的干部執意要我去看看另一個村——馱尖村。在當地人的眼里,馱尖村的今昔變化,簡直是一個奇跡。
馱尖,正如它的名字一樣神秘。這是一個畬族村,位于海拔700多米的高山之上。馱尖全村有93戶,322人。千百年來住在山頂上,信息閉塞,許多村民不會說漢語,住的是高不到2米的茅草房,過得是“火篾當燈草,火籠當棉襖”的日子。當地人至今還流傳一句話:“馱尖人做大戲,公陽人分餅。”意思是嘲諷馱尖人窮得連大戲都做不起。
但是馱尖這兩年的變化,讓人刮目相看。村支書鐘昌造帶著村民,做了一件令當地人難以想象的事,拆掉了村里原本散落在各個山頭的茅草房,統一在山巔修建了新房。
聽說村里來了客人,村民們都來鐘昌造家里幫忙,舂黃豆,做糍粑,用畬族人最高的禮儀,迎接我們這些山外來客。
馱尖村海拔高,秋雨連綿,氣溫比山下低不少。村里通了路,修了新房,生活與以前相比,已經有了天壤之別。但是畢竟地理位置偏遠,山上的生活依然艱難。

快到吃中飯的時間,鐘楊珠在灶膛里燒火做飯。中飯是米飯焐芋頭。已經好幾天沒有吃到肉了。平時山下的公陽鎮上會有人販點肉送到山上來賣,但是一碰到下雨天,常常十多天都沒人來。打開話閘,鐘楊珠訴說起日子的艱難。女兒去年考上杭州的一所機械學校,才讀了一年就輟學了,因為付不起一年幾萬塊的費用,不得不到溫州一家服裝廠打工去了。據說村里有好幾個考上大學的年輕人,最后都輟學了。
令鐘楊珠頭痛的不僅于此,如今山上野豬肆虐,莊稼的收成也不好。“番薯苗剛剛長了這么一點,”鐘楊珠用手比劃,“野豬就來吃了。”好在山巔云霧繚繞,適合種茶葉,每年可以靠種點茶葉補貼家用。
鐘楊珠的隔壁住著藍大媽和小孫子。4層樓高的房子里,就住著祖孫倆。兒女們都出去打工了,藍大媽負責在家里看孫子。令她擔心的是,隨著小孫子年歲漸長,到上學的年齡了。村里沒有學校,讀書必須要到10多里外的公陽,或者到更遠的文成縣城。“到時只能到公陽去租房子,陪小孩讀書。”看著剛剛蓋起的新房,藍大媽有點不舍。
馱尖位于群山之巔,長年云霧繚繞。據說天晴的時候,從村里遠望,洞宮山連綿不絕,景色絕佳。村口的村委會有一副當地書法家撰寫的對聯,“翠竹蒼松云卷千峰包,奇花異卉泉和萬籟聲”,說的就是山上的美景。
鐘昌造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在山巔打造畬鄉農家樂。他說,村里雖然建了新房,但青壯年還是都出去了,如果不能吸引年輕人回來,村莊終究難以逃脫衰亡的命運。
對于鐘昌造的計劃,當地的干部并不看好。“地方太偏了,文成風景漂亮的地方多的是,人家為什么到你這里來。”
集聚,改變鄉村危局的藥方
文成,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其實離寸土寸金的溫州市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在外來者的眼里,很難想象,咫尺之間繁華和凋敝會切換得如此之快。當地官員告訴我,文成主要還是吃了地理位置的虧。文成境內大山連綿不絕,是真正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發展的空間非常有限。而周邊地區經濟發達,大量的農村勞力被抽走。反過來,更加制約了當地的經濟的發展。
當地一位官員打了一個比方,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扶貧不是簡單的給予,應該為當地村民找到謀生之道,而年輕人的出走,讓當地的一些扶貧項目都找不到合適的實施人。
說到底,農村的衰敗,是急劇城市化的犧牲品。不管是沙了還是馱尖,它們都是被城市化浪潮裹挾的中國鄉村的縮影。沙了和馱尖的現狀,其實反映的是整個鄉村世界遇到的難題。當2.5億農民工在城市的邊緣奮力打拼的時候,錐傷他們心靈的,還是遙遠的故鄉,“幼無所養,老無所依”的困局。根據全國婦聯2009年的統計,中國有5800萬留守兒童,這個數字如今直逼6000萬。他們有些不滿周歲,父母就離家打工,只和爺爺奶奶生活,甚至還沒學會自理就要進寄宿學校。如何破解現代化圖景下的鄉村困局,文成給出的答案是——集聚。
把散落在大山角落里的老人和小孩遷出來,在靠近城鎮、自然條件較好的地方實現集中居住。“因為只有集中居住,才有可能解決諸如養老和教育的配套問題。”當地扶貧辦的官員告訴我,縣里今年專門出臺了《關于實施農村宅基地置換推進農房改造集聚建設的若干意見(試行)》,鼓勵農民通過置換宅基地的方式進城鎮居住。
“這項政策的前提是尊重農民意愿,在農民自愿永久放棄農村所有宅基地的前提下,按有關程序和辦法有償置換城鎮住房,切實讓農民得到實惠。”當地官員介紹說,通過宅基地置換、下山搬遷、地質災害避險遷建等方式,引導高山遠山、地質災害高易發區、不宜居住村的群眾,整體向中心鎮、中心村(新社區)搬遷集聚。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把集中連片整體搬遷村,靠近安置地、條件成熟的高遠山村,危舊房戶、住房困難戶列入優先安排的行列。置換戶可選擇在城鎮農房改造集聚建設安置區有償置換多層或高層公寓房,或者作價領取貨幣補貼到城鎮自行購置商品房;甚至在鄉鎮統一規劃的中心村自建、統建聯立式或公寓式住宅。
但集聚的政策在實施中還是遇到了一些現實困難。對于一些老人來說,已經習慣了山里的生活,不愿在遲暮之年搬離故土。縣里雖然有支持置換購房戶向商業銀行申請辦理住房按揭貸款、小額聯保貸款的政策,但一些家庭還是無力支付建房的費用。另外,讓村民們擔心的是,如何保障集聚后的生活。離開了土地,生活會不會變得更加艱難和不可預知。
“集聚這項政策的方向是對的,但在實施的過程中,還有很多現實的問題需要解決。”一位與農民打了半輩子交道的當地官員說。
解決鄉村的危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