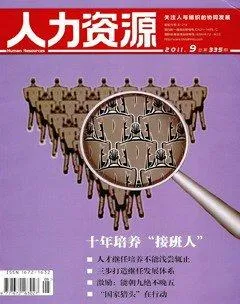分紅權激勵:做蛋糕與分蛋糕的統一
經國資委反復研究、修訂,央企分紅權激勵文件出臺,試點在人們的爭議中啟動。面對毀譽參半的輿論關注與熱議,國資委有關負責人坦承,相對于此前股權激勵的探索無功而返,分紅權激勵“阻力相對小很多”。究其原因,當是央企分紅權激勵試點體現了一種做蛋糕與分蛋糕相統一的精神。無論該試點能否交出讓13億“股東”滿意的答卷,而這在當前有助于克服一種將分蛋糕與做蛋糕對立起來的“發展糾結”。
做蛋糕與分蛋糕的統一
在央企上繳紅利非常有限而為國人詬病的情況下,新近推出的央企分紅權激勵如果是正當的,在邏輯上只能是做蛋糕與分蛋糕的統一。這就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種將做蛋糕與分蛋糕對立起來,執著于做蛋糕與分蛋糕哪一個更重要,認為重視分蛋糕必然會影響做蛋糕的“發展糾結”,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已經被實踐證偽。因為分紅權激勵并非簡單的利益分享,而是著眼于將蛋糕做得更大。
央企這次激勵試點“選擇了分紅權激勵而不是股權激勵,選擇了激勵對象是崗位而不是具體員工,選擇了業績增量而不是業績存量”。在兩個試點單位中,航天恒星的激勵總額與企業當年的經濟增加值和經濟增加值改善值掛鉤;有研稀土采用了當年凈利潤額與凈利潤增加額作為計提總額。也就是說,分紅權激勵獎的是增量,只有將蛋糕做大,創造出新的價值才給予獎勵。試點方案體現了向核心科研技術崗位傾斜的導向。多年來,我國國有科技型企業一直存在收入“該高的崗位不高、該低的崗位不低”的現象,特別是核心科研人員的收入大大低于市場平均水平,難以留住人才。此次分紅權激勵試點實行后,航天恒星和有研稀土的科研類崗位和激勵額度占比均達到90%以上,其余崗位也均為與科研成果轉化密切相關的經營管理崗位。經測算,兩家企業核心崗位的科研人員收入水平平均有望提高30%以上,能夠實現有效激勵。
如果說這是在分蛋糕的話,就有助于推動員工進一步將蛋糕做的更大。從短期來看,國資委雖然要拿出一部分增大了的利潤進行分配,但可以促進員工關注企業資本成本的控制,更加注重企業經濟效益的改善,以便在增量中分享更多的收益。在這里,做蛋糕與分蛋糕就是統一的,員工分享的越多,也就意味著企業的蛋糕做的更大。
而沉湎于“發展糾結”的人則認為,只有先把蛋糕做大,才有蛋糕可分。這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可以理解的,犧牲公平被視為打破大鍋飯體制的開拓。但是分灶吃飯、減員增效所派生出來的一個慣性,正是國企在人們心目中形象不佳的一個原因,那就是多數人的蛋糕讓少數人分,把減負當作改革的必然。事實上,以犧牲公平來換效益有一個可以忍受的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就會影響效益的可持續性。當兩極分化超出公認的警戒紅線時,就連“先富帶后富”的改革初衷也容易遭到人們的質疑。在新的情況面前,如果解不開“發展糾結”,仍然堅持把做蛋糕作為重點,政府就涉嫌推卸體現社會公正的責任。反過來說,推出更能體現公正精神的分蛋糕方案,并不會阻礙發展,而是在為發展設置新的助推器。
常識告訴我們,同樣是建造,人和蜜蜂的區別就在于,蜜蜂的建造是本能的反映,而人在建造之前,腦海中首先會形成構思和框架,可以更加有效地開展創造性的工作。做蛋糕與分蛋糕哪一個更重要的答案正在于此,設計出合理的分蛋糕方案,并取信于民,就能對做蛋糕產生積極的影響。實際上,當央企進行分蛋糕試點時,社會做蛋糕的努力仍然沒有、也不可能停頓下來。如果說生產和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兩極,兩者又是同時進行的,就不能說“分蛋糕”的時候,“做蛋糕”的活動就停滯下來了。如果一定要進行第一要務、第二要務的排序,那就猶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一樣,在特定的時間段將“分蛋糕”作為重點或者第一要務,并非離經叛道。
參照系的躍遷是關鍵
當然,央企分紅權激勵在理論上可以立足不等于現實中的無懈可擊,有些人擔心分紅權激勵,不僅解決不了央企收入水平過高的老問題,還會出現新的分配不合理現象,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這并非空穴來風,有專家告訴我們,在一些高新技術企業試點分紅權激勵有其必要性,可以作為推進央企改革的重要一步;但央企必須同時在內部進一步完善績效考核制度和分配制度,提高分配的透明度,進行全方位的監督,防止把部分核心科研人員漲薪變成所有員工“搭車”漲薪。人們所擔心的種種負面現象的出現并非不能克服,問題取決于在試點的過程中,博弈的雙方誰具有實際的話語權。可以肯定的是,博弈的雙方不能僅僅滿足在體制內尋求平衡,需要實現參照系的躍遷。
這并非純粹的思辨,最本質東西的還是利益的統籌,即從“帕累托改進”到“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改進”是經濟學的一個概念,是指在不減少一方的福利時,通過改變現有的資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央企分紅權激勵大致上就是如此。而“帕累托最優”是指,在一切“帕累托改進”的機會都用盡了的情況下,如果再要對一些人的福利有所改善,就不得不損害另外一些人,即在不減少一方福利的情況下,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在改革開放初期,進行“帕累托改進”的制度安排有助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當既得利益已經形成的時候,再堅持“帕累托改進”的制度安排,客觀上就是對既得利益群體的保護,因此躍遷到“帕累托最優”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實施央企分紅權激勵必須抑制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否則就等于繼續為央企高管的天價年薪背書。
央企分紅權激勵選擇從科技企業開始,無疑體現了央企實現經濟轉型的積極訴求:然而這還需要央企負責人的指導思想真正轉到科學發展觀上來,而不是在科技領域進行新的一輪“跑馬圈地”。經濟轉型不是外延式的另搞一套,而是一種內涵式的成長。其實質不僅在于央企掌握的科技是否具有含金量,而且在于這種科技的研發與驗證自身是否具有壟斷性。央企的貢獻大而形象不佳,除了“天價燈”、“茅臺酒”事件表現出來的奢侈,還在于坐享壟斷地位的好處。分紅權激勵試點所選擇的航天、稀土科技領域具有一定的壟斷性,一般規模的民企很難涉足:假如享受分紅權激勵的科研像高鐵建設那樣,在體制內自我研制、自我驗收、然后進行量的擴張,那么這種轉型注定是鉆政策空子的又一種“皇帝新衣”。
實現參照系的躍遷主要體現在跨越體制的思考上,應當符合分配制度改革頂層設計的基本精神。首先,央企當前缺少的不是激勵而是監督,其總體工資水平不算低。在這種情況下,分紅權激勵不能把科研精英的精力引向急功近利:一方面不應當把分紅權激勵演變成內部的普遍漲薪,另一方面在科研失利時應當給予必要的支持。其次,央企紅利不應該滿足于單獨制定僅僅讓部分群體受益的分配原則,必須同時考慮怎樣為重新切好國民收入大蛋糕作貢獻。分紅權激勵不能違背讓全體公民成為直接受益者的終極目標,至少應當以最終上繳國庫的紅利為基數,不能享有優先權。再次,對于具體的企業來說,必須減少內部操縱的空間。比如分紅權激勵對象不能參加股東會、行使投票權,分紅權激勵方案應當向公眾公示等。
突破線性思維的局限
那種將分蛋糕與做蛋糕對立起來的“發展糾結”,有一把“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尚方寶劍,似乎很有威力。然而問題在于,硬道理與線性思維具有本質的區別,發展不可能是一種直線的、單向的、單維的、缺乏變化的軌跡,分蛋糕與做蛋糕完全可以作為發展的兩翼。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新的系統工程,人力資源管理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而人力資源管理要想更好地完成包括成功激勵在內的新使命,同樣需要突破線性思維的局限。
老板要關注企業的“人事賬”,必須把人力資源管理真正放在戰略高度來認識。長期以來,有些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被認為是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事,似乎老板管的是做蛋糕,是在抓大事;而人力資源管理屬于分蛋糕的范疇,是一個怎樣執行的問題,怎么分那是老板的一句話。的確,因為勞動力資源豐富,老板可以坐享人口紅利而沒有后顧之憂。而分紅權激勵的模式告訴我們,企業坐享人口紅利的慣性,應當被勞動者享有分紅權所校正。經濟轉型的現實要求老板不僅要關注發展,更應當關注怎樣發展,需要從拼物質資源轉變為拼科技優勢。這就必須提高人力資源管理的地位,需要老板投入更多的精力抓分蛋糕,以便更好地凝聚、激勵員工做蛋糕。《呂氏春秋》所謂“賢主勞于求賢,而逸于治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企業要克服人力資源管理與資本運作的兩張皮現象,確保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落地。過去,有些企業雖然也強調以人為本,實際上是把勞動力當作成本看待的。如果把人力資源成本的增加視為無法遏制的趨勢,就是一種線性思維的表現。事實上,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分蛋糕并非一種施舍:而應當和貨幣、材料等資源的投入一樣,有其合理的回報,而且同樣會增值。因此,面對成本上升的環境和趨向,我們必須有新的思維,樹立人力資本的觀念。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甚至比貨幣資本還來得重要。人力資源管理者需要轉換角色定位,像資本運作那樣進行人力資本的經營,成為資本運作的有力推動者,形成默契。
人力資源管理本身也需要不斷地自我完善,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可持續成長的人力資源保障。如果說企業在金融危機或者通膨的影響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環境,也不是什么成本問題,而是成長問題,那么人力資源管理就應當從僅僅關注不傷害勞動者的生存狀態,提升到關注員工的發展狀態。在宏觀層面上,轉變發展方式的要害是縮小“三個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從以出口、投資為主轉到以消費為主,改善民生,拉動內需。而在企業層面上,人力資源管理就不能像過去那樣,在不突破勞動者維持生存狀態所需底線的狀態下分蛋糕,需要關注員工的幸福指數,使員工處于良好的發展狀態。除了當下的人盡其才,還要形成一套長期的人才培養和發展計劃,這包括使員工得到需要的培訓、讓員工能夠更充分地發揮出自己的潛質、清晰并實現自己的職業發展路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