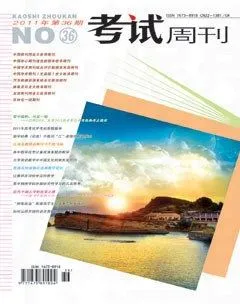閱讀教學中對語言的“優值理解”
語言文字符號的價值在于“義”,即理解“義”,運用“義”。這個“義”也就是語言符號所指代的事物與現象,言語交流實際上是人們借語言來反映事實,溝通思想。從閱讀教學來看,理解語言是閱讀教學的起點與歸宿,全部活動范圍都離不開理解語言,如教學目標——設定理解語言的要求;教學過程——展現理解語言的活動;教學方法——保證理解語言的有效;教學評價——分析理解語言的得失利弊。閱讀教學也有語言運用,但閱讀教學中的語言運用主要在使用中確認語言的“義”,提供運用的案例,其用意并不在于專門的語言運用訓練。在閱讀教學確立“語言理解”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我們權且提出“優值理解”的評價標準,這一標準相對來說比“好課”、“有效教學”等更貼近語文性質。
一堂課怎樣才算“優值理解”?優值理解就是對語言文字的一種具體的、細致的、正確的、清晰的、深刻的、全面的理解。在一堂課內,能引導學生對所學的語言文字做到這樣的理解,或基本上達到這樣的理解,是不容易的事。只有這樣的理解,才是真正讀懂了所學的語言文字,才能在意識中呈現出所反映的事物的原貌、原意、原情,獲得真知、真理、真情;只有這樣的理解,才能體悟語言的精妙,培養敏銳的語感,提升語文水平;只有這樣的理解,才能激活學生的思維與想象,增強智力,才能激發學生學習語文的積極性,愛學語文。堅持這樣標準的理解訓練,才具有強勁的活力,才能培養出扎實的、高水平的閱讀理解能力。相反,那種對語言文字空泛的、粗疏的、錯誤的、模糊的、浮淺的、片面的理解,就是“低值理解”。
在教師中流行的所謂的小學語文課文淺顯“易懂論”、小學生只需大體懂得就行的“模糊理解論”、學語文靠多讀熟讀以讀代講的“全盤朗讀論”等都是導致低值理解的不當言論。小學語文,既容易又困難,容易的是文字短小淺顯,難的是淺顯文字反映的內容并不淺顯。赤壁之戰這樣的歷史大事,只有千余字表現;園明園的毀滅也只千多字描述。小學課文絕大多數都是普通記敘文,簡短淺顯,只能反映事件的概略,而文字的間接性、概括性卻遮蔽了事物具體的真實細節,給閱讀帶來很大的困難。文章作者走的是“事物—概括化—文章”的路,要想破解文字的概括性,只有在閱讀教學時走“文章—具體化—事物”的逆向還原的路。
《史馬遷發憤寫〈史記〉》短短兩千字的課文,學生很難感受司馬遷為實現偉大理想而忍辱負重、堅韌不拔、發憤著書的精神。我在教此課時,故意將課題中的“發憤”寫成“發奮”,引導學生發現錯誤,從而提出:為什么用“發憤”而不用“發奮”?司馬遷遭遇怎樣的“飛來橫禍”?從課文中找答案。其用意就在于突出重點,把握“發憤”這一核心,確立探究的問題,以期通過此問題的解答,樹立人物形象。在學生敘述的同時,讓教師的點評提升學生的理解與表達:尊重事實;痛恨小人,敢于直言;一片忠心卻被誣上罪名……司馬遷所受的酷刑是對他人格最野蠻的侮辱,也是對他一家、對他父母先人的極大羞辱,每每想到這里,司馬遷就會渾身出冷汗,衣服濕透。作為士大夫的司馬遷,非常重視做人的尊嚴和名聲,文中“悲憤交加”詞語寫出了他的心情。
面對自身的侮辱,面臨世人的譏笑,為什么司馬遷想到血濺墻頭,卻又沒有了此殘生呢?借助課件演示:“……何至于甘心陷入囚禁而受辱呢!……我所以暗自忍耐,茍活下來,陷身與污穢的監獄中而不死去,是因為我感撼于內心想做的事業尚未完成,如果在恥辱中離開人世,我的文章著述便不能彰明于后世……”此段話是摘自有關傳記,配以男低音,隨著竹簡緩緩打開,通過視覺和聽覺撞擊學生的心靈,從司馬遷的內心獨白中體會他復雜的情感。司馬遷將秉筆執書看作是史官的天職。他從極度的悲憤中解脫出來,將個人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帶著滿腔的憤恨、沉重的憂傷和無盡的痛苦,默默將自己全部的心血,傾注到撰寫的《史記》中。憤怒出詩人,憤怒出《史記》,這就是文中用“發憤”,而不用“發奮”的原因。教學中,我十分注意納入的資源必須具有典型性、史實性、生動鮮明性與簡潔性,并注意這些資源的有機組合,使之成為教學中的必然、自然、當然,此項設計,使整個教學具有很強的感染力與震撼力。類似的文章,學習時必須細讀、精思,對概括化的語言文字鉆研、探究,通過思維想象(主要是具體化思維)用時空和情節的連續性,揭開語言文字的豐富內涵,還原事物可及的真實(原貌、原意、原情),這才是真閱讀,真理解。
做到“優值理解”是很不容易的事。除了上述的文字間接性、概括性外,閱讀教學是憑借文章學習語言,學文與學語同步進行。這使學習理解語言文字有了更廣闊的平臺,也增加了難度。這里又有一個“文語結合”的概念,即借文學語,借語學文,語言理解應包括理解結構,理解表達,理解文體,理解作法等,包容了各種語言形態的理解。在小學,文章中的語言是活用的言語,理解在不同內容、不同語境中的大量言語及語言組合與變化,正是學生學習語言、積累語言的需要,也是理解文章的需要。
當前小學語文教學存在著重文輕語、抓文棄語的問題。教師備課只重文章的理解,課堂教學只抓文章內容,而不重視語言理解,造成學生語言分析能力薄弱,普通的文章也只能敘其梗概與印象。語言是文章構成的主要成分,是文章的介質,不作言語分析,所理解的文章思想是膚淺的、模糊的、空洞的。在執教《青海高原一株柳》時,我就是想盡力顯示言語教學的力度。
在教學“幼苗存活”一段中,凸顯自然環境嚴峻的詞語有“持續干旱”、“全毀”、“嚴酷”、“絕不寬容”;體現幼苗頑強生命力的詞語有“不可思議”和兩個“奇跡”。在一個自然段內,解讀詞語的分量如此重,其效果就是學生對這一節的內容會產生具體、清晰、深刻的理解,對學生語言認知的準確性、靈敏性無疑是一次扎實的訓練。全文四個落點的段落言語教學的分量都較大,從全程來看,把語言教學提到了主體的地位。四個點的選擇,都體現青海高原的那株柳樹之所以巍然成景,是因為它頑強地與環境抗爭的結果。眾多的詞語的解讀最后統統趨歸于一個中心,即文章的主題,呈現一種事實趨歸于思想、多點輻合于一個中心上,明顯呈現文語合一的教學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在領會主題思想時,不是概念式的而是言語解析式的。表述主旨的兩句話中就抓了“毅力”、“抗爭”、“韌勁”三個重點詞和“沒有……也沒有……而是……”的選擇句式及“九十九”與“一”的對比詞語,使主旨的領會清晰而深刻。全篇教學如此設計,突出了語言,以語言教學為主,也突出以文章的思想為統帥的文語合一的雙促進理念,充分體現了小語教學的基礎性、遞進性與發展性。
什么是閱讀?“閱讀是從一種有形的語言符號中獲得意義的心理過程”。這種獲得意義的含義是多方面的,因此理解小語課文并非容易的事。“易懂論”、“模糊理解論”、“全盤朗讀論”,等等,指向粗枝大葉、囫圇吞棗式的閱讀和模糊含混的理解,不利兒童理解能力的培養,尤其導致學生產生學語文沒意思的消極思想,不愛學語文,挫傷其學習積極性。我們必須反對“易懂論”、“模糊理解論”、“全盤朗讀論”等,消除它們對閱讀教學的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