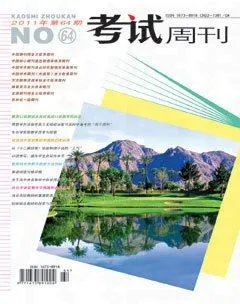從《小二黑結婚》談趙樹理小說的“土氣”
摘 要: 趙樹理的小說洋溢著濃郁的農村生活氣息,從題材、風情習俗、人物形象等方面里里外外都透著“土氣”。本文以《小二黑結婚》為例,淡淡趙樹理小說的“土氣”。
關鍵詞: 趙樹理小說 《小二黑結婚》 “土氣”
在現當代文壇,再沒有哪位作家能像趙樹理這樣,在生活和心靈上如此貼近農村,貼近農民。他的作品處處充滿著農民的生活氣息,透露著山區的鄉土味道。人們稱之為“土氣”。
有人認為這種“土氣”不登大雅之堂,不能達到雅俗共賞,其實不然。彭德懷曾這樣評價《小二黑結婚》:“像這樣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可見,趙樹理小說的“土氣”并不是雅俗不可以共賞的,而是“土”得恰當。
《小二黑結婚》充分體現了這種“土氣”,我們可以從如下幾方面來看。
一、題材“土氣”
題材“土氣”。《小二黑結婚》寫的是農村一對青年男女為爭取婚姻自由跟封建殘余意識和惡霸勢力做斗爭的故事。愛情,是文學史上一個傳統的話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白蛇傳》、《紅樓夢》等作品,他們的愛情不是雙方在夢幻中團圓,就是雙雙遁入空門,或者雙方茫茫然出走,這些結局畢竟是悲慘的:愛情的毀滅。盡管有一些反封建思想,但他們的反封建意識并不徹底。這真正說明了愛情這一話題在過去文學史上并沒有得到最充分的表現。
在《小二黑結婚》中,這一話題得到了嶄新的表現:青年男女不僅僅追求自身的幸福,而且緊密結合當時的社會階級斗爭而培育了愛情,他們反對的是一切阻礙自由愛情的封建落后思想和殘余勢力。作者在作品中以輕快的旋律、明朗的節奏來表現他們反封建的徹底性和對自己的愛情無比堅定的信心。這種新穎的風格在文學史上是不曾有過的。同時在表現他們的斗爭中,作者又自然地描寫出山西地區農民的生活狀況。如在“三仙姑來歷”一節中寫道:“于福是個老實后生,……于福的娘死了,只有個爹,父子兩個一上了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婦一個人。”“于福他爹看見不像個樣子,有一天發了脾氣,大罵一頓……新媳婦卻跟他們鬧起來……父子兩個沒了辦法。”從這平實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山區農民的生活狀況:男子耕種,女子在家做活。因為貧困,所以三仙姑才得以支配起于福。每次外出,她都騎在驢背上,害得于福跟在后面跑。這種描寫讓我們在讀完文章之余又了解到當地的習俗。這樣,《小二黑結婚》在繼承民族傳統題材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結合了山西地區的風俗習慣和農民的生活狀況,具有了濃郁的地方色彩。
二、風情習俗“土氣”
趙樹理在風情習俗方面主要關注的是神靈崇拜、婚喪禮俗等。《小二黑結婚》中的二諸葛和三仙姑,他們共同實現了趙樹理對當時農村普遍存在的崇神信鬼現象的憂慮和針砭。無論是二諸葛的“論一論陰陽八卦,看一看黃道黑道”,還是三仙姑的“裝扮天神”,都是對超自然力的神秘現象的崇信。而這對處于底層的民眾似乎有著神奇的吸引力,即便新中國成立以后一直到新世紀,仍不絕如縷。
趙樹理對農村中的婚喪禮俗非常熟悉,“參加過婚喪大事”[1],《小二黑結婚》中三仙姑將女兒小芹許配給吳先生,二諸葛給兒子小二黑收養童養媳的描寫,既展示了在舊農村父母包辦兒女婚姻的傳統習慣,又表現了舊式農民以婚姻來攀附富貴或求安務實的心理特征和價值觀念。
三、人物形象“土氣”
在短短不到一萬字的篇幅中,作者塑造了幾組活靈活現的農民形象:二諸葛和三仙姑、小二黑和小芹。
二諸葛,原名劉修德。“當年做過生意,抬腳動r65vjmWuxITtIVIF8KsyvMFrnj4NtYS7yq2CjO05vHg=手都要論一論陰陽八卦,看一看黃道黑道”。這個綽號是作家給人物封建意識的一種標志,也是一種幽默的嘲笑,突出和強調人物的這一性格特點。
作者通過兩個場面繪聲繪色的描寫,二諸葛就浮雕似地站立在我們面前。
第一個場面:“不宜栽種”。在久旱逢雨的時候,農民都在耕種。但是二諸葛卻迷信舊歷書中的“禁忌”,因此,大家也就嘲笑他,把這件事傳為笑談。迷信,幾乎成了劉修德認識生活、對待生活的唯一標尺。小二黑被金旺兄弟捆綁,他按照自己獨特的、奇妙的邏輯,歸因于他在一天清早“碰上個騎驢媳婦,穿了一身孝”,“戴孝的沖了運氣”,以及“二黑他娘夢見廟早日唱戲。今天早上一個老烏鴉在東房上叫了幾聲……”。所有這些他都認為是征兆,無窮的憂慮,然而他卻自認為是先知先覺者。可見封建迷信觀念對他毒害之深。
他反對小二黑與小芹結合,因為他堅持那種對迷信的迷信:“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小芹生在十月,是個犯月。”無論是因為什么,實質上都是從傳統的舊道德觀念出發,封建迷信觀念在作怪。正是這種迷信觀念支配著他,無視兒女的幸福,給小二黑收留了一個十二歲的童養媳,頑固地一再要求區長“恩典恩典”。
“恩典恩典”是作者表現該人物的第二個場面。在區上,看見小二黑與小芹坐在一條板凳上,他罵道:“不要臉!” 并堅持求區長“恩典恩典”。可見他腦瓜里隱藏的舊東西與環境格格不入,而他卻頑固地堅持這一套。劉修德雖然可笑,但他也非常可愛。因為他堅持那一套的舊觀念、迷信的時候,不但沒存壞心,反而是為兒子好。從小二黑被捆著送到區里,他“一夜沒有睡”。到了區上一再要求區長“恩典”,可以看到他有一顆亮晶晶的心。因此在本質上,他是一個心地善良的老頭子,誠實的農民,慈愛的父親。作者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無論是“不宜栽種”或者“恩典恩典”的場面中,作者帶著熱情和善意,幽默地奚落了他一番,而在最后,滿懷信心地給他安排了一條新的出路。
三仙姑雖然也是個“神仙”,但她這個“神仙”可跟劉修德不同:她假裝神仙只是為了糊弄人。她比劉修德可惡之處就在這里。作者通過“米爛了”的小故事, 對騙人的“下神”做了幽默的揭露。從“三仙姑的來歷”一節中,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出,她的裝神是對沒有愛情的婚后生活不滿的一種表現。“于福是個老實后生,不多說一句話,只會在地里死受”,“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2]三仙姑和于福過著沒有愛情的夫妻生活,正是這種不道德的婚姻派生了三仙姑的不道德行為,四十多歲了竟然還跟女兒爭風吃醋,這完全是一種畸形的、變態的性格。
三仙姑盡管是一個受害者,卻不值得人們的同情,因為她受到封建社會的腐蝕,沾染的惡習太多了。她不滿于福,就盡情地虐待他。她每天睡著懶覺,不做家務。于福燒罷早飯,不敢先吃,擺著飯菜等待三仙姑梳妝打扮完畢,這一家才能開飯。三仙姑出門,于福立即備驢。她坐在驢上,于福跟著跑。三仙姑發起脾氣就裝起神來,于福就趕快跪下挨訓。她簡直是把于福當奴仆對待,甚至對女兒也喪失了母女情分,為了貪財,為了給自己不道德行為掃除障礙,狠心“賣女”。小芹被人抓走,做母親的卻幸災樂禍。三仙姑的心靈里充滿這種黑暗的東西,是她令人生厭的原因。她的這種變態心理正是那個不給她愛情自由而又歪曲她的性格的舊禮教、舊社會造成的。
還好,三仙姑還沒有喪失最后一點羞恥感,作者在最后一節中交代了這一點:“三仙姑……回去對著鏡子研究了一下,真有點打扮得不像話;又想到自己的女兒快要跟人結婚,自己還賣什么老俏?……把三十年來裝神弄鬼的那張香案也悄悄拆去。”從這可以看出,作者正是通過這兩個人物的描寫來對封建觀念、舊社會做了徹底的否定,也反映了作者希望他們在新的環境中開始新的生活,跟舊社會遺留給他們的舊習氣、舊觀念斷然決裂。
在塑造了二諸葛和三仙姑這兩個豐滿的藝術形象之外,該小說還塑造了小芹、小二黑兩個農村新人形象,他們也是生動真實的,他們身上散發著新時代的氣息,無論在家庭里、社會上,他們都敢于為自己的幸福而斗爭。
他們的家庭都不好,然而他們并不受父母的影響。盡管小二黑從小就跟父親學那些“天干”、“地支”、“五行”、“八卦”之類的東西。當二諸葛還沒有來得及把全部的“法寶”傳授給小二黑的時候,當小芹只覺得“她娘哼哼得很中聽”的時候,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新時代來臨。當大人們對著二諸葛問:“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種?”孩子們一跟小二黑生了氣,就連聲喊道:“不宜栽種,不宜栽種……”這話深深地刺痛了小二黑,“好幾個月見了人躲著走,從此和他娘商量成一氣,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
小二黑跟父親的迷信觀念決裂以后,在反“掃蕩”時,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他和小芹在與惡霸勢力、封建觀念斗爭上充滿著無比堅定的信心。當金旺兄弟斗爭他們的時候,小二黑反問:“無故捆人犯法不犯?”小芹則火辣辣地走進村公所劈頭就問:“村長!捉賊要贓,捉奸要雙,當了婦救會主席就不說理了?”而且在反對封建包辦婚姻上,表現得特別徹底、堅決:當二諸葛收童養媳的時候,小二黑回答得輕快、干脆:“你愿意養你就養著,反正我不要!”當三仙姑許親的時候,小芹敢于頂撞:“我不管!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去!”作者對這些人物的描寫,不只是對自由婚姻的歌頌,更是對整個時代和人民政府的歌頌。
這三組人物塑造得生動、傳神,既大眾化又不乏個性。作者之所以能塑造出這樣活靈活現的人物,是因為他對農村的生活有獨特的感受和獨到的見解,對農村的封建家長制家庭、沒有文化的愚盲生活,閉塞的與世隔絕的環境有更多一層的體會。“文壇太高了,群眾攀不上去,最好拆下來鋪成小攤子”[3],這也是趙樹理“土”的一個方面。
四、人物語言“土氣”
在作者的筆下,語言是通俗易懂的,又是逼真傳神的。如《小二黑結婚》是這樣為三仙姑畫像的:“三仙姑卻和大家不同,雖然已經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繡花,褲腿上仍要鑲邊,頂門上的頭發脫光了,用黑手帕蓋起來,只可惜官粉涂不開臉上的皺紋,看起來好像驢糞蛋上下上了霜。”這段描寫,作者用平實的語言形象地描述出三仙姑的“老來俏”。這正達到了作者鍛煉語言的宗旨:要讓“農村一般認識字的一看就懂,不識字的一聽就懂”。
為了強化語言的逼真、傳神的藝術效果,趙樹理還從農民的口語中錘煉出俗語、歇后語和比喻等來豐富自己的描寫。對三仙姑的老來俏,用“驢糞蛋上下上了霜”的比喻,突現三仙姑人老珠黃卻還涂脂抹粉的怪模樣。在斗爭會上,小芹辯駁說:“捉賊要贓,捉奸要雙,當了婦救會主席就不說理了?”“插起招軍旗,就有吃糧人。”這些俗話的運用,抓住了特點,使讀者在捧腹大笑之余,又感受到這些語言諷刺入骨的藝術效果。
由此可見趙樹理的小說少了畫意詩情,卻多了粗拙厚樸,里里外外都透著一股“土”氣。正是這種土氣,使《小二黑結婚》受到了群眾的熱烈歡迎;也正是這種士氣,“在太行農村普遍演出的《小二黑結婚》,深入地幫助了勞苦農民去解脫在自己身上的封建鎖鏈”;[4]也正是這種“土”氣,使他的作品受到了各國人民的歡迎,“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5]因此,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欣賞品味去貶低他的作品,畢竟他的作品適應了當時群眾的需要,相反,他的這種本色的創作風格還應值得我們去學習。
參考文獻:
[1]王春.趙樹理是怎樣成為作家的.人民日報,1949-1-16.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恩全集,第21卷:96.
[3]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人民日報(晉冀魯豫),1947-8-10.
[4]澤然.農村劇團的旗幟.人民日報(晉冀魯豫),1947-5-3.
[5]魯迅全集: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