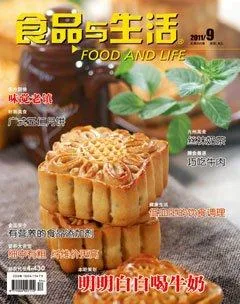荷蘭海鮮一口吞
吹著大西洋的海風,嗅著略帶咸味的潮濕空氣,來到席凡寧根海邊,品嘗著來自深海純凈水域,絕對可以滿足最挑剔味蕾的海鮮饕餮大餐。荷蘭的海鮮不僅美味,在歷史上對于荷蘭的崛起還曾起到過舉足輕重的作用。
記得《大國崛起》系列里面的荷蘭篇,關于阿姆斯特丹的崛起,有這樣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建在鯡魚骨上的城市。這個1/3國土位于海平面之下的小國,深受大海的恩賜,鮮美的魚類經常入菜,而最具代表性的當數鯡魚。
腌鯡魚改變荷蘭人的命運
荷蘭位于歐洲西北部,瀕臨北海。受洋流的影響,每到夏季,就有大批鯡魚洄游到荷蘭北部的沿海區域。14世紀時,荷蘭人口不到 100萬,卻有近20萬人從事捕魚業。在當時,漁汛到來之際,北海上就出現了壯觀的景象,1 500艘漁船在這里忙碌著。荷蘭人每年可以從北海中捕獲超過1 000萬公斤的鯡魚,小小的鯡魚為1/5的荷蘭人提供了生計,并成為荷蘭人的經濟支柱,也是阿姆斯特丹獲得經濟成就的最早動力。鯡魚的貿易業也拓展了荷蘭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往來。荷蘭人不敢想象,沒有了鯡魚,生活會是什么樣子。
不過,造物主并沒有給荷蘭人獨享鯡魚的權利,生活在北海邊的其他民族,也組織了捕撈鯡魚的船隊,以獲得這種自然資源。和其他魚類一樣,鯡魚保鮮的時間只有幾天,當時還沒有制冷設施。隨著大量的鯡魚涌入歐洲市場,荷蘭人的鯡魚開始滯銷、腐爛,這讓一些荷蘭人的生活陷入貧窮的危機。為了減少其他國家的捕撈量,荷蘭人曾和他們的鄰居蘇格蘭人爆發過三次戰爭,以爭奪鯡魚漁場,但戰爭也沒能改變荷蘭人的命運。
n1tkrXBy3uzg0m6muFkwMf7lRHmlhLIEt8YRZK9nuAg= 1358年,在荷蘭北部的一個小漁村,一個名叫威廉姆·伯克爾斯宗的漁民發明了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魚腸子的方法:把鯡魚的肚子剖開,把內臟取出,把頭去掉,然后把鹽放在里面,這樣可以保存一年多的時間。荷蘭漁民的一把小刀,將一種人人都可以染指的自然資源,轉化為荷蘭獨占的資本。借助暢銷的鯡魚,荷蘭進而開始了和東北歐、英格蘭、南歐、非洲的貿易,海上貿易迅速發展起來。如今在鹿特丹的一些古老房屋上,仍可以見到鯡魚的圖案。這些并不醒目的標志似乎在時刻提醒人們:鹿特丹作為世界第一大港的歷史,就是從一只只裝滿咸鯡魚的大缸開始的。到17 世紀的時候,這個僅有150萬人口的國家不但成為整個世界的經濟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區,還將自己的勢力延伸到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當時,人們稱荷蘭為“海上馬車夫”。
生鯡魚一口吞是最正宗的吃法
直到今天,許多荷蘭人在食用鯡魚時,仍保持著這種幾個世紀前形成的飲食習慣:去除內臟之后的鯡魚,簡單腌制后不經過任何烹調,直接提著魚尾一口吞下。于是當我走在海牙的街頭,看到這樣一個賣生鯡魚和其他海鮮小食的貨攤,決定嘗試一下荷蘭式的吃法。沒想到,看荷蘭人拎著鯡魚尾巴一口吞下十分容易,自己卻無法做到,嘴就算張到最大程度,也只能仰著脖子一點一點吃下去。看到我這費勁樣子,旁邊一位老者示意鯡魚還有另種吃法。看他把鯡魚切成幾節,與生洋蔥一起用小叉子叉著吃,比起一口吞,這樣既斯文又可以品嘗到魚的美味。
生鯡魚十分肥嫩,魚骨頭非常軟,稍有點腥味,中國人初次吃肯定會有些不習慣。但我很快便愛上了這種街頭美味。據說鯡魚含有極高的維生素D,有益于心血管以及強健骨骼。而這家議會大廈門口的鯡魚攤兒,聽當地人說,是全海牙最好吃的。后來在阿姆斯特丹我只要碰到鯡魚攤兒,便忍不住來上一條。由于是冬季,鯡魚的數量不是很多。到了春末夏初所謂新鮮的鯡魚季,那時滿街都可以找到好吃的鯡魚攤兒了。
至于海鮮,荷蘭人還是很有口福的,許多沿海城市,比如海牙、鹿特丹都可以找到不錯的海鮮館。海牙的席凡寧根海灘是我最喜歡的去處,那里各種魚檔海鮮館兒沿著海灘一字排開:鮭魚、淡水鱈魚、鰨魚、銀魚樣樣鮮美,烹制方法五花八門,有生食、蒸煮、炸和煙熏等等。天氣好的時候,坐在半開放式的排檔里,要上一份各類新鮮海魚的拼盤,再來一杯冰啤酒,看著海鳥在頭頂盤旋,期待著從客人那里得到一些賞賜。如今這里已經成為當地人和外國人最喜歡光顧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