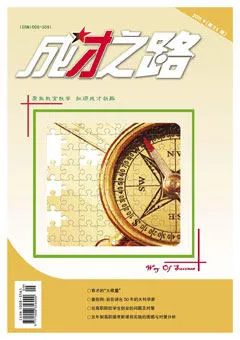從教育現狀看中國制造業升級之人才困境
無論是“十二五規劃”還是今年的總理講話,均強調了教育的重要性及投資教育的決心。這是令人鼓舞和欣慰的。但是,當下中國教育現狀堪憂:教育結構不合理,教育理念有問題,教育內容與現實脫節。這一特點嚴重影響了中國制造業升級,需要引起政府及相關機構重視解決。
先來看教育結構不合理。中國目前是、未來仍將是制造業大國的經濟地位,決定了現階段中國需要的是大量的技術工人,而不是大量的白領。而目前中國高等教育遍地開花,職業教育一是總量萎縮,二是內容與現實脫節、落后,此種現狀導致的結果是出現大量希望做白領、而且也只能做白領的學生群體,而技術工人這塊一是很少有地方生產、二是切合實際的職業教育奇缺。這種經濟結構與教育結構錯位現象,也是當前畢業生求職難的間接原因。
二是教育理念有問題。中國社會自古至今的教育理念是“學而優則仕”,最好的學生都涌向政府。這與中國千年政治文化也有關系,與目前社會大環境也有關系。這種理念導致社會整體都認為技術工人處于社會底層。而處在世界制造業上游的德國社會則不是如此。在德國,高中畢業以后人才就開始分流,一大部分人選擇了去職業教育,另外一部分有志于學術教育的繼續上了大學。而去職業學校的學生畢業后和上大學的學生畢業后薪水相差無幾,至多在職業選擇上有所差別。這種理念導致了德國的職業教育有著穩定的優秀生源供給,從而保證了一流的技術工人儲備。這也是德國制造在世界范圍內勝出中國制造的主要原因。還有,日本早稻田大學依田熹家教授對比中日現代化,指出中國的教育文化是“目的獲得型”,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目的達到了,就不需要教育了。而日本的教育是“能力提高型”,認為不管何時都要讀書學習,通過學習來普及和提高能力。如此,才能在社會各個群體中提高素養,從而推動所從事工作的提升。日本制造成為世界品牌和質量的保證,除了與日本的民族文化傳統有關系外,與他們獨特的教育理念也是有著很大關系。
再次,教育內容陳舊、與現實脫節,也是需要重視的問題。中國目前的職業教育內容無法適應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實踐需要,且師資隊伍質量日趨下降,這是現實生活中職業教育的地位決定的。高等教育內容空泛,大學四年下來,理工科學生可能還好點,文科學生可能記住最多的是英語;專業設置上前兩年是到處開花的國際貿易、行政管理、法律等,現在是金融、經濟等,每個學校都開設。這樣的后果是社會上到處都是這些專業畢業的學生,質量良莠不齊不說,與社會需求對接就是很大問題。而充斥社會中的證書考試,放眼望去,都是心理咨詢師、人力資源師、會計師、高級口譯和語言類的,就是沒有與工業生產對接的證書考試。在日本,如果要從事工業生產,必須要參加相應的職業認證考試,社會中也有類似的培訓教育。就是名牌大學畢業的學生要從事工業生產,也必須參加此類教育與考試。這樣就保證了大學生畢業后進入工廠之前專業技能的學習與獲取,從而完成理想與社會需求的有序銜接。
其實,短時間內看,雖然中國國內勞動力價格提升,人民幣升值,但是中國制造業地位世界暫無其他國家能一力代之。目前金磚四國中沒有一個國家能替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印度的現狀決定了它長期只能集中于醫藥和軟件產業,巴西集中于資源和農業出口,俄羅斯主要是能源等,所以中國目前是、仍將是世界制造大國。
有契機,也有危機。郎咸平先生曾經說過,中國經濟真正的危機是制造業危機,原因不僅指目前的經營環境惡劣,還指中國制造業處于世界產業鏈的最低端,利潤率太低。要想沿著產業鏈條向上延伸,就必須在研發設計和銷售服務上下工夫。這就需要有對口的、高質量的技術工人隊伍來完成,這就是職業教育與整個社會的教育理念的調整問題了。
以上三方面的問題,嚴重制約了中國教育的內涵式發展,也嚴重影響了中國教育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培養提供人才的數量和質量。中國制造如果想實現在世界產業鏈上的位置突破——產業升級,就必須正視和正確解決這三個問題。調整教育結構,理順教育理念,更新和調整教育內容,三者必不可少,也不可顧此失彼,需要在下一步的規劃發展中統籌解決。如此,中國制造業的升級才有現實的可能,“中國制造”才有可能成為品牌和質量的象征,發展“中國創造”才會有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