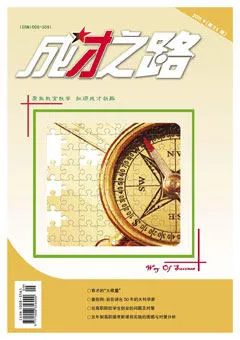窮孩子沒有春天?
拿到班級花名冊時,陸銘(化名)注意到,全班60多位同學,農村籍學生只有5個左右。
作為北京大學某文科院系2009級1班的班長,陸銘此前一直以為,通過高考選拔獲得中國這所頂尖大學通行證的同齡人,多數該有著和他類似的成長經歷:出身農村,家境貧寒,獨立自強,品學兼優。現在,手上的花名冊顛覆了他的認識。
有統計顯示,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在北大校園,陸銘鮮有同鄉,畢業于縣級中學的他也沒校友可聚,他成了孤獨的傳奇——眼下,什么樣的年輕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華?
寒門少年都去了哪兒
清華大學講師晉軍指出,一名清華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這樣的: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務員或教師,每年與父母起碼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國游學的經歷。
北大校園里,學者廉思組織了一個“返鄉調查”計劃,以為學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車票的方式,鼓勵他們假期回到家鄉,完成一篇調研報告。今年,這個計劃不得不暫停。
“申請經費的學生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干脆就沒有了。”廉思說,農村學生越來越少,對大多北大學子而言,一張免費硬座火車票實在太沒吸引力,臥鋪、飛機,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復旦大學招生辦一位老師的印象中,這幾年被招進復旦的學生,父母都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與體面的社會地位。“學生們都在復制父輩的模樣。”
那么,學習刻苦,成績不錯的寒門少年都去了哪兒?
教育學者楊東平的研究顯示,以湖北省為例,2002~2007年5年間,考取專科的農村生源比例從39%提高到62%,而軍事、師范等提前批次錄取的比例亦從33%升至57%。而在重點高校,中產家庭、公務員子女則是城鄉無業、失業人員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動感到艱難的不僅僅是農村少年。2004年,廈門大學進行調查后發現,普通工人階級子女考入重點高校與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別減少了7.9%與5.6%。
學者廉思與他的團隊走訪蟻族后發現,家庭狀況與所考入的學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
連專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讀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選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莊作為研究樣本,那兒濃縮了中國基層凋敗的模樣——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鬧出點什么動靜,一大幫無所事事的年輕人立即呼啦啦地從網吧、桌球室里涌了出來。
不平等的起跑線
仝十一妹,這位來自河北滄州農村的24歲女孩,現在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研一學生。
仝十一妹的小學、初中分別在鄉村與縣城度過。中考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母親為成績一路優異的她報考了衡水中學。在這所軍營式的河北省超級中學,仝十一妹度過了緊張且競爭激烈的3年,2006年,她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如果我當時留在縣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仝十一妹說,那一年,她所畢業的縣城中學年級排名第一的學生,也只是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線名校。
這是優質教育資源高度集中的征兆。超級中學是各省重點中學的升級版,它們大多位于省會城市,擁有豐厚的教育經費與政策支持,像抽水機般吸納當地及周邊縣城最優秀的學生與最優秀的老師,每年幾乎壟斷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華的名額。
超級中學的出現
超級中學的出現,很大程度成就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機會,大多被各省最富競爭力的高中包攬。例如,全國十三所外國語學校,每年最優秀的學生都可直接保送進入北大、清華。陜西超級中學調研數據顯示,2010年,北大清華在陜西自主招生名額的98.9%、保送名額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壟斷。
裸分考上北大、清華的幾率越來越小。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學生中,只有10人沒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則通過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徑邁入北大,他們絕大多數出自超級中學。
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競爭力的重點高中實力越來越強,迅速升級為超級中學。絕大多數的普通高中與縣城高中,被遠遠甩在了后面。
教育學者楊東平說,“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疊加了優越家庭的優勢,寒門子弟拿什么和他們競爭?靠什么改變命運?”
越來越窄的向上通道
過去幾十年中,高考向弱勢群體傾斜的補償性政策對象主要包括少數民族學生、烈士子女等。但較之特長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奧賽等加分,比例與力度顯然偏小。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賦予部分名校招攬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權,有機會通過這一途徑直通名校的,是超級中學與省級重點中學的學生。
在甘肅會寧這座以寒窗苦讀聞名的狀元縣做實證研究時,清華新聞學院2009級本科生張曄遇上了一名垂頭喪氣的農村少年,這位被學校推薦參加自主招生考試的學生剛從考場上下來。“很多題目,他連看都看不懂。”張曄說。
自主招生的考題涉及面廣,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觸到的事物,比如五線譜,比如殲十……清華社科2010級的陳美詩則在自主招生考試中遇到了一道關于費孝通在哪里上大學的題目,她說:“我在進清華前連費孝通是誰都不知道,這題清華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
藝術加分與寒門子弟更是絕緣。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體育特長生七成來自大中城市,來自農村的只有6%;而藝術特長生,迄今沒有一位來自農村。
“這意味著,中國高校擴招后,并沒有增加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楊東平說,“相反,普通高校文憑的市場競爭力在擴招后越來越弱,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難度越來越大。”
陸銘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與小學、初中同學的聯系越來越少,圍坐在這位清華大學高才生旁邊,那些在縣城工作或從外地打工返鄉過年的同學不知道該說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