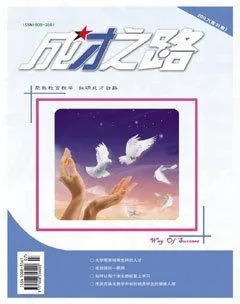每件事至少有100種做法
許多教師和專家都問過魏書生老師:“你怎么就敢十多年不批改一次作文呢?你怎么就敢讓學生互相批改作文呢?這些打破傳統、獨樹一幟的做法,你究竟是怎么想出來的呢?”
魏書生老師的回答是:
“我喜歡這樣思考問題:每件事至少有100種做法。請仔細想一想,有哪一件事沒有100種乃至上千種做法呢?
比如治胃病,難道只能吃胃舒平嗎?就大的方面而言,至少就有三大類治法:中醫、西醫、氣功師。中醫治胃病的藥方,古今不下100種。西醫呢?保守治療和手術治療,具體方法恐怕也能有幾十種。氣功師呢?儒道佛醫,各門各派,不同治法,恐怕也能有上千種。
比如一個字,學習的‘學’字,至少也有一百種寫法。甲骨文、金文、隸書、篆書、魏碑、行書、楷書、草書、仿宋,寫法的區別就很大。單就楷書而言,柳公權、顏真卿,直至現代的啟功、趙樸初,這些大書法家的字,風格各異。這樣看來,僅僅一個‘學’字,也不只100種寫法。1 000名學生或1 000位書法家,同寫一個‘學’字,也會有上千種區別吧!更值得思考的是,我們很難比較隸體的‘學’字和篆體的‘學’字誰優誰劣,也很難說出哪個書法家的‘學’字能排在第一位。他們的‘學’字千姿百態,千變萬化,各具特色,妙處無窮。
治胃病、寫一個字這樣的小事,尚且有這么多種不同的做法,最后殊途同歸,為什么對講課、留作業、批改作文這樣復雜得多的事情,卻認為它只有一種模式呢?‘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都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的形式呢?’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說的這些話,值得我們深思。
如果這樣想,教學改革的天地就十分廣闊,就容易從一種模式的牢籠里解放出來,因而感到自己大有作為。”
有許多教師和專家還問過魏書生老師:“你目前采用的批改作文的方法是不是最好的?”
魏書生老師的回答是:
“我現在采用的批改作文的方法,肯定不是最省力的方法,肯定不是效果最好的方法,一定還有很多更好、更科學的方法等著我去發現、去采用。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現在采用的批改作文的方法,就個人的實際情況而言,肯定比過去精批細改,讓兩座大山壓得很少有時間學習與思考的方法要好。正因為比過去好,所以不管哪個所謂權威要強迫我回到老路上去,我也不回。因為我教的歷屆學生的作文平均水平一直名列全市前茅;與此同時,因為我目前所采用的批改作文的方法不是最好的,還要不斷地探索、尋求、繼續前進,爭取找到更好、更科學的方法。總之,找到一種方法,再找到一種方法,用一用,比一比,哪種方法做事效率高、效果好,就用哪一種。”
推而廣之,魏書生老師這樣思考問題的方法具有普遍的積極意義,正如他自己所說:
“不只是治病、寫字、講課、批改作文至少有100種方法,調動學生積極性呢?幫助后進生進步呢?管理班級呢?管理學校呢?管理企業呢?管理社會呢?做行政工作呢?做黨務工作呢?處理周圍的人際關系呢?不是都有100種乃至更多種不同的做法嗎?運用那種方法沒做好,無須懊悔,無須煩惱,再換一種就是了。運用這種方法效果挺好,也無須驕傲,無須固步自封,再往前去尋求更好、更科學的方法。人活著,不能總想自古華山一條路,而應該多想條條大路通羅馬。經常這樣思考問題,容易使人變得開朗、樂觀、豁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