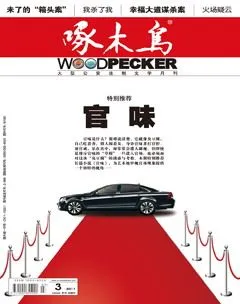火場疑云
蘇珊娜·菲格羅警官受到了驚嚇,而且她很不喜歡處于擔驚受怕的狀態——這使得她憤憤不平。更糟糕的是:她確信她的搭檔諾姆·本尼斯也驚魂未定。然而,本尼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個錯誤導致他們倆都陷入了泥潭。
蘇茜(注:蘇珊娜的昵稱)坐在等候室的一邊,她雙臂交叉疊在胸前。在同一間屋子的另一邊角落里,與她相隔同樣距離的地方,諾姆·本尼斯也坐在那里:他的雙腳伸開,下巴擱在膝蓋上,低垂著腦袋。他看起來一副傷心欲絕的模樣。
蘇茜暗自尋思:真該死!他是自作自受呀……她真的希望他深感內疚——犯下如此愚蠢的錯誤而不能自拔。這個執拗的家伙!
可是,他們倆長期以來一直在合作共事!
本尼斯還是她忠誠的伙伴和朋友。
警官學院教導你說:有些東西是你需要懂得的。而且這份職業和你的搭檔又教會了你:某些東西你確實需要弄懂。蘇茜·菲格羅在跟隨一位視導員完成她最初的實習工作后,就和本尼斯簽約成為警務搭檔。在一開始的時候,她很害怕諾姆會對她有所成見。因為他看上去中規中矩,況且從閱歷而言——他活像是面向二十一世紀警務工作職業典范的流動廣告。當蘇茜初入此道時,他已經是芝加哥具有十年警齡的一名警官了。本尼斯的身材像個倒三角形:肩寬胸闊,臀部瘦削。他長了個國字臉,皮膚呈棕色。當警察集合點名的時候,她第一次見到他愁眉苦臉的樣子。不過她很快就意識到:其實他認為和一位身材矮小的樸實女性做忠誠搭檔,會有許多樂趣的。
他們倆很快就互相適應了。不知道究竟是年紀比他小十歲,還是彼此坦誠相見的緣故,他從未取笑過她屬于一種“礙手礙腳的、只配待在家里的”或者是一種“多嘴多舌、打小報告的”人物。他也不像她的教官那樣會因為她不知道如何填寫一張特殊的表格而輕視她。他懂得警察局不是靠汽油或者電力來驅動的,而是靠辦案文件來運作的,而且他知道當她填寫了幾百份表格之后,就一定會對所有的表格了如指掌。
本尼斯善于冷嘲熱諷,但并非尖酸刻薄。
對于蘇茜而言,她倒是調侃過他,說有一長串女人會迷戀上他,可惜每個人都不會超過三個星期的限度……說罷,她又感到后悔。那是因為她自己也是個離異女人,她的前夫稱她為“維權行動警察”(注:反對歧視少數民族或者婦女而采取的集體斗爭,稱為“維權行動”)。前夫借此來表示:她對于任何人而言,都顯得個子太矮小、太女性化而不適合。
然而,本尼斯恰恰認為她非常勝任警察工作,曾對她說:“你作為我的殿后幫手,那可是前所未有的佼佼者。”
“嗨,本尼斯!我可不是只做殿后的,我還是急先鋒呢!”
“那倒也是。”
在一次集體旅游活動中,蘇茜和諾姆隨同第一警務區的一些警員,曾經去富爾婁夫酒吧喝啤酒。可是最近他們不去喝啤酒了,而是私下約好一起去觀看一部特別的影片。蘇茜暗自思量:這種約會并不專屬于少男少女呀。他們在互相打約會電話時,心里不免有些尷尬,因為事實上恰巧發生了警備車上的浪漫故事……
可是在當下,他們甚至都不愿互相對視一眼。
這是二月十五日上午十一點——就是那場意外事故發生后的一天,沿著大廳的邊上有兩個房間,其中一間的圓桌前,圍坐著五個負責調查的官員:包括一名警察局局長助理,一名州律師和前來檢視此案文件的聯邦代表。擺在他們面前的是消防局的報告,還有醫事檢察官和探員們在現場找到的初期物證。但是根據來自其他部門的報告,只能說明那場事故發生后的情況。在這個節點之后,正是諾姆和蘇茜的說法出現分歧之處。
他們的隊長薩舍拉克也在等候室里,跟他們坐在一起——和他們倆一樣,滿臉的不高興。沉默許久后,他終于開口了:“我無法阻止調查這起案件,這使我很煩惱。我不愿揣測你是個逃避責任的人,菲格羅。”
“您這是什么意思?”
“難道你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如何看待此案的?”
“意識到了呀,老板。他們知道我和諾姆對于昨晚事故的說法有兩個不同的版本,而且認為我們其中有一人對此案的描述不是恰如其分的,因此必然有一人在撒謊。在我們倆當中,誰會是該受譴責的人?”
“不,菲格羅。應該不是你的那個搭檔。”
“搭檔!我絕不會有個受譴責的搭檔,而且眼下也不打算有一個!長官。”
薩舍拉克嘆了口氣說:“聽我說,我們背著局里私下交談而已,也許會被告發的。”
“為什么呀?”
“他們認為你在那場火災中扔下那個快死的男人不管,菲格羅。你可以想想如何自圓其說,掩蓋一下。使它聽起來像那人已經死了一樣。”
本尼斯呻吟著說:“然而他早就死了,長官!菲格羅決不會……”
“本尼斯,他們認為你事后補充了那種判斷——就在你意識到你的描述引起了調查組對于那個男人是否已經死亡的懷疑之后。”
“那可不符合事實。今天早晨我把情況做了書面記錄的時候,我才說他當時已經死亡。”
“說服力不強。其實你早就‘以為他死了’。他們猜測:你之所以過后更加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你們想使菲格羅擺脫困境。”
“不,不是這樣的,長官。那種說法恰恰不對。長官,菲格羅是歷史上與我合作共事的最好的警官。她決不會拋棄一個大活人。”
“你是否要重新考慮你的證詞,本尼斯?”
本尼斯的目光從蘇茜那里移到隊長臉上,隨后又轉移回來。他的臉色顯得極度痛苦,開口道:“我不能改變。很對不起,菲格羅。我不能撒謊。也許我一下子被那場火災搞得暈頭轉向,不過我得說出我所知道的一切。我不能撒謊。”
“可是你正在撒謊,本尼斯!”她正色道,“但愿我知道你為什么要這樣做。”
菲格羅的內心此刻像滾開水般地翻騰著。本尼斯的目光從菲格羅的臉上移開,凝視著角落里的一棵枯死的盆栽植物。隊長又嘆了口氣,隨后房間里一片死寂。
房門被推開,一位身穿制服的男人跨進房內,說道:“全體調查人員準備就緒,請你們去吧。”
“昨天是許多人稱為‘真正的芝加哥氣候’的夜晚。”蘇茜·菲格羅對調查組說,“大約在下午三點時開始下雪,當時我和本尼斯警官剛開始值勤。我們立即意識到快到交通擁堵時間了,屆時由于道路積雪,情況會十分糟糕。還有就是——因為要趕赴情人節的晚宴,人們開始涌入城內。在四點鐘的時候,漫天飛雪,一片白茫茫,簡直連馬路對面的景象都看不清楚。到了五點鐘左右,在通往湖濱大道和肯尼迪快車道的那些彎曲道路及坡道上,大批車輛首尾相接,慢吞吞地在積雪道路上爬行。其中一些車輛汽油耗盡,堵塞了街道,直到路政管理部門派來拖車才將它們拉走。”
她努力控制住心中的恐懼和促使她激動的那些想法,忠于一個警察的職守才是她的本分。
“在那個時刻,我們親臨交通堵塞現場解決問題,是習以為常的。我們要把那些熄火的車子中的人接出來,但他們又不大愿意配合,很費勁呀。我們找到一些事故車輛中的民眾,開著警車送他們到臨時避難所。我們……”
局長助理沃德龍突然打斷了她的敘述:“菲格羅警官,談談那場事故吧。”
“遵命,長官。不過天氣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都知道昨晚的天氣是什么樣的。接著說。”
“是的,長官。”沃德龍這家伙要找麻煩了,她尋思道。他的面相不善,而且他的嗓音像刀刃一樣鋒利。有時候她會情緒激動,尤其是每當她覺察到有另一名警察不樂意在警察部門有婦女的時候。雖然私下里她不愿判定:眼前這個家伙站出來,是想捏住她的把柄,但是她愿意打賭:他能證明某個女警察是否被嚇唬住了,看來他很欣賞做這種事……
“在二十點四十分,我們接到一個電話……”
“呼叫警務一區33號警車!”無線電里說。當時他們在第一警務區的33號警車里。由于菲格羅在開車,本尼斯拿起無線電通話機回答:“我是33號。”
“在切斯特納特路西段的8-1-7坐標點,有個女人叫救命。”
“分隊長,你是否確認在幾樓?”
“在二樓。”
“打電話的人說了名字么?”
“噢,是的,叫‘市民’,反正與市民有關。”
“我知道是那個家伙。”
“是個年輕姑娘。”
“不管是什么人了。”
由于下大雪的緣故,這座城市顯得很沉悶。但實際上附近并沒有汽車的噪音,而且他們聽到的警方調度員的聲音比往常更加清晰。沒有必要再重復指令了。于是本尼特說道:“通話結束。”
街道上已經鋪著厚厚一層積雪,雪花仍然紛紛揚揚地飄下來。菲格羅說:“哎呀,本尼斯。這不是公共交通的問題,全都是由于私家車拋錨引發的堵塞。”
“要是你把警車開上人行道,我們就可以繞開這些拋錨車輛了。”
“沒錯。”
“注意別撞壞人行道上的消火栓。”
“本尼斯,求求你啦!你明明知道,我是個多么出色的駕駛員。”
“菲格羅,我的搭檔,對于你的信賴我敢用生命來擔保。我是以日常規范來推斷的呀。”
“幸好你還活著。”
“注意那只大垃圾桶!”
“離開那玩意兒差不多有一英里呢。”
“只差四分之一英寸。”
無線電里又傳出了調度員的聲音:“警務一區33號車。”
“我是33號。”
“我們接到了那個女人第二次呼救的電話。你們在什么位置?”
“在拉塞爾路向北行駛。開車真艱難哪,分隊長。”本尼斯回答,盡力避免喘氣——因為此刻菲格羅突然拐了一個彎,險些撞上一根路燈桿。“不過我想,我們的車子剛開出去才兩分鐘。”
“是的,33號。好吧,順便告訴你,新聞報道中說:這場大雪要持續下到明天中午才會停止呢。”
“太棒了。”
本尼斯和菲格羅終于把警車開到了長龍般的車流的前面。他們經過了成千上萬座高樓大廈,卻不知道到底發現了什么異常情況。他們只有互相依靠,其中一人只知道另一人就在身旁,他們甚至使用起最簡潔的交流方式。本尼斯伸出一根手指,告訴菲格羅:讓她停下車,然后站在某幢公寓大樓門口較遠的一邊。接著他走到門跟前,敲了敲門。當他再次敲門之前,菲格羅指著某處喊道:“瞧!”
這扇大門上面的門縫周圍,冒出了一股濃煙。
本尼斯用手去感覺那扇門,想弄明白它是否是涼的——哦,確實是涼的。他退后兩步,飛起一腳去踹門。正在此刻,不料那扇門突然洞開,有個男人飛奔出來——他的頭發和夾克衫上都著了火,口中尖聲大叫著。他根本沒有看見這里有兩名警察,而是發狂似的從樓梯上直沖下來。
本尼斯疾步上前,尾隨著那個男人,同時想著菲格羅會向警方調度員呼叫緊急求援。他三步并作兩步沿著臺階沖下去,還是沒有攆上那個嚇壞了的男人,直到那人蹦跳著、尖叫著在大門外的水泥臺階上跌倒為止。那男人頭發和夾克衫上的火苗已經蔓延開來。本尼斯將他在雪地里翻滾了三到四圈,想讓被燒傷的肌肉涼一涼,以防止進一步的損害。他還抓起一把又一把的雪,在那個男人的頭部和背部輕輕拍打著。
時間緊迫,顧不上等著瞧一瞧大火究竟給那男人帶來多大的傷害了。只有上帝知道這幢大樓里還有多少人。本尼斯連忙轉身回到大樓內,沿著樓梯跑上去。
與此同時,菲格羅接通了無線電對講機:“警務一區,33號,緊急呼叫。”
“請講,33號。”
“在這幢公寓大樓發生了火災,火勢正在迅速蔓延。”
“我將到達煙霧最濃的地方。”
“就在四樓。”
她在無線電里只講了六秒鐘。與此同時,她迅速觀察了公寓的情況。她幾乎看不見任何東西,因為煙霧實在太濃了!
菲格羅發現自己走到一間廚房里了:那里有個女人,從地上爬起來,直端端地沖向一個存放掃帚的儲藏室。當她碰到墻壁的時候,她又跌倒了,再次爬起來往前沖……可憐她在萬分驚恐中,竟然把那堵墻當做了房門!
菲格羅一把緊緊拽住她。“別擋我的路!”那女人一遍又一遍地尖叫。
菲格羅說:“嗨!停下!”
“別擋我的路!”
菲格羅輕輕拍打著她的背,讓她平靜下來。
現在火焰順著地板蔓延,熊熊燃燒。這個女人不停地尖叫。
“跟我來吧,真該死!”菲格羅抓住這個女人的手。眼下火焰順著地板一路蔓延,這個女人還在尖叫大喊。
“快跟我走,真該死!”菲格羅緊緊抓住這個女人的手,把她強按在地板上面,然后一只手抱住這女人的肩膀,匍匐著朝房間門口爬去。
這個女人的身上已經著火了,她的皮膚摸上去也是滾燙的,菲格羅相信她被火燎出了水皰。
就這樣推著拉著、哄騙加威嚇,菲格羅總算那女人拽到了起居室里。在爬過這一片地板的過程中,菲格羅似乎覺得她翻越了一個躺在那里不會動彈的男人的軀體,但是她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這個問題。她一心想著趕快把那女人帶到門口。
門廳里的空氣仍然是涼爽的,從門縫中透進來新鮮空氣,于是菲格羅飛速將門打開,把那女人推出房門外,朝她大喊道:“快對鄰居們發出警報!”
沒有時間確定她所做的一切是否恰當。她只看見本尼斯從樓梯跑上來了,菲格羅便朝他大叫道:“屋子里面還有個男人!”
憑借著雙手和膝蓋,菲格羅又爬回了房間里,她觸摸墻壁才能判斷自己所在的位置。她終于找到那個男人,可是與此同時她突然聽見嬰兒的啼哭尖叫聲。本尼斯也在大火濃煙中摸索到了她身邊,他拍拍那男人的胸口,可是那男人一點都沒有反應。
菲格羅用手試探那男人的前額。雖然嗆人的煙霧彌漫在周圍,但是他沒有知覺,而且沒有體溫。此刻嬰兒的哭叫聲更加響亮了——從他們身后的一間臥室里傳過來。
“我要去救那個嬰兒。”她對本尼斯說。她吃不準是否聽見了烈火的呼嘯,接著她發現本尼斯也跟隨在后面,他們一起爬到了那間臥室。
“究竟有幾個小孩?”她叫道。
只有一張帶著圍欄的兒童小床。
本尼斯站起來,從小床里抱出一個小女孩,用一只胳膊挾住她,像橄欖球賽的四分衛攜帶著球奔跑一樣——直端端地沖向門口。蘇茜·菲格羅留下來,繼續尋找另一名孩子。
現在火苗已經舔到了天花板,她沒有多少時間了。
一張小床。得抓緊了!沒有另一張兒童床。刻不容緩!炙熱的空氣!就在她透過濃煙四處張望的時候,瞥見只有一個小女孩的玩具:同一個年齡段玩耍的兩個布娃娃,一只有填充物的玩具狗熊,一個裝小松糕的鐵聽和幾把塑料勺子……可以確定:只有一個孩子。
突然,天花板有一部分轟然坍塌……
趴在地板上吸足最后一口氣,菲格羅一躍而起,像箭一般的沖向房門。起居室此時燃燒得跟地獄一樣,倘若她記不清門在哪個方向的話,就不可能沖出去了。她的頭發被火焰燒得吱吱作響,她甚至看不見躺在地板上的那個男人——不管怎么說,他已經斷氣了,而且她還要警告住在樓上的那些鄰居。
在外面的大街上,消防車正在穿越那些拋錨汽車的堵塞,趕來火災現場。他們直到十分鐘之后,才趕過來。
“我要指出的是——”薩舍拉克隊長對沃德龍助理說,“本尼斯和菲格羅警官把其他居民救出了那幢大樓。在那樣的糟糕天氣和緊迫的時間條件下,他們倆為消防隊的到達和后續救援打下基礎,當然是救了災民的命。”
“我們理解那個情況……”沃德龍字斟句酌地說。
薩舍拉克又說:“當消防隊趕來時,整幢大樓已經著火了。隨后他們尋找水源時又出了點麻煩——那些拋錨的汽車堵塞了通往消防栓的去路。”
“我們了解這一點。”
“在凌晨三點三十分的時候,大火終于被撲滅。當時本尼斯和菲格羅警官仍然在呵護著那些居民——即便他們最終已經連續作戰了四個半小時。”
“薩舍拉克隊長,我很感激你想幫助你手下人員的意圖,不過我們感興趣的是當時在莫里特公寓發生了什么,而不是之后發生了什么。我們繼續講下去。”
本尼斯氣憤地說:“我親眼看見菲格羅從樓上救出了六個居民。”
“本尼斯警官,我們稍后再聽取你的故事。”
薩舍拉克隊長大聲說道:“她在救援行動中全身都著火了——這你知道嗎,助理先生?”
“它與現在討論的話題無關。在宣判的時候,我們也會考慮這個因素。”
“難道你的意思是說:有一個導致宣判罪名的決議?局長助理。”
“當然是了,隊長。噢——這只是初步的圓桌會議,我的口誤。”他轉身朝其他四名調查組成員說:“我們會將薩舍拉克隊長有關這個議程的質疑記錄在案。再說,我們還要把所有情況理出頭緒來。今天我們并不打算利用這個程序,把它當做一種方式——去直接聽取卷入該事件的兩名警官的陳述。”
薩舍拉克隊長說:“在過去的十二個小時內的任何時間,他們都可以那樣做。那是由于他們的職業忠誠,不愿意更改其書面報告,才會有意識地強調有可能引起歧義的同一件事物,使你們覺得有破綻——”
“隊長!這是發現真相的過程,任何爭論都不合時宜。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直到事實證明證詞有變化或者證明不了有變化的時候。”
這里的負責人是沃德龍,而不是薩舍拉克。警察部門的管理機制就是這樣。薩舍拉克除了坐在邊上之外,無可奈何——正如通常掛在墻上的那幅局長照片那樣,做個擺設。
他與沃德龍互相對視了二三秒鐘。
菲格羅開口道:“長官,我能問一問在什么情況下導致了那場火災嗎?我們是中途遇見那種情景——”
“那也不成理由。”
“我并非暗示情況一定如此。然而,當時公寓里明顯已經起火,而且屋里有三個成年人,他們似乎都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滅火。為什么莫里特先生會躺在起居室當中的地板上面?例如:如果他已經遇害了,我想我就有權了解此事的起因。顯而易見,他不是被煙霧嗆死的,他倒下那塊地板處的空氣中沒有濃煙。”
“我想,沒有什么不可以告訴你的原因。我們擁有一張合理的現場全景照片,還有那個被救女人和鄰居們的回憶證言。”
莫里特一家在那天下午爆發了爭吵和斗毆——包括丈夫和妻子,還有莫里特先生的小舅子也摻和其中。他們喝完酒便打架,打過架又喝酒……事后在他們那套公寓房燒毀的殘留物中,發現了大量的空啤酒罐和裝有蘇格蘭威士忌酒的玻璃瓶碎片。
大約在傍晚時分,左鄰右舍對這家人的瞎胡鬧已經相當厭倦了。根據警方的調查和當事婦女的陳述:大約在晚上九點的時候,莫里特先生一直在大聲叫嚷、威脅他的妻子,并且用拳頭擂墻壁,隨后開始毆打妻子。她也回擊了片刻,終因不敵而倒下,其丈夫便用腳狠狠地踢她。女人不斷地尖叫著呼救……有個女鄰居想來幫忙,但不敢進屋或者敲門,于是她就打電話報警。
與此同時,那個小舅子過來救援其姐姐了。他揮拳襲擊姐夫——當時姐夫勃然大怒,便猛推一把,將小舅子推倒跌在其姐姐身上。隨后姐夫抓起一瓶烈酒,像發瘋一樣四處傾灑在起居室和廚房的地面和墻壁上,點燃了這些烈酒……那個小舅子怒氣沖沖地從地上爬起來。那個妻子被眼前的情景嚇壞了,便掙扎著爬向她認為是大門的地方。但她由于挨了丈夫的幾記拳頭而暈頭轉向,況且目前房間里又是火光一片、煙霧繚繞,她實際上是爬進了廚房里。
這時小舅子順手撈起一把椅子,不偏不倚地砸中了他姐夫的頭部——莫里斯先生砰然倒地……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菲格羅和本尼斯警官剛剛趕到公寓大樓的外面。當時那個小舅子的頭發已經著火,使他驚慌失措,飛奔著逃出了公寓,途中被本尼斯警官遇見并予以救援。
沃德龍繼續說:“菲格羅警官,在本尼斯警官帶著嬰兒離開之后,你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將莫里特先生搬出室外。你也許搬不動,但是你必須試一試。”
“我明知躺在地板上的那個男人已經死了,而且他渾身冰涼呀。”
“本尼斯警官,他的身體是冰涼的嗎?”
本尼斯張口結舌。菲格羅的眼睛盯住他,但是他的目光游移到別處。在一瞬間他挺直了身軀,抬平兩只肩膀,仿佛正在拿主意要采取某種行動。接著他垂下腦袋,面孔朝著地面。
“當時他的身體還是溫熱的。”
薩舍拉克隊長問道:“在火苗燒到他之前,是否有辦法證明他活著還是死了?你們應當可以測試肺部吸入碳的情況。如果他沒有呼吸——”
“薩舍拉克隊長,我們感謝你的幫助。”沃德龍接過話頭,其聲調毋庸置疑地表明了不曾那樣想過。“不論相信還是不相信,我們都認為他沒有死。”
薩舍拉克惱怒地觀察著眼前的一幕。他很清楚目前的局面,肯定是某個地方出了點問題,然而他又無法插手。菲格羅絕不會扔下一個大活人不管,聽任其被活活燒死。薩舍拉克擔任隊長職務已經相當長了,所以不可能在判斷他手下警官的個人品質方面出大的差錯。菲格羅身上存在一個有待查明的問題,但絕非見死不救——而是見義勇為。正如許多個子矮小的女警察一樣,她甚至勇于冒著不必要的風險去做她應該做的事。眼下對她的指控是大錯特錯的。
沃德龍又補充道:“整幢公寓樓被大火吞沒,直到消防隊最終把它撲滅為止。此后不久,上面三層樓房的整體結構轟然坍塌,壓在地下室上,成為一片廢墟。刨出的莫里特先生的尸體,看起來就像是焦黑的擦煙斗的通條一樣。”
菲格羅凝視著那臺筆記本電腦。
“等一下!”她突然說。她明白對上司說話不能提高嗓門,用的是比較輕柔的語調。“如果你們給我點時間,讓我理清頭緒,我想可以解釋清楚發生的一切。”
她站了起來。
沃德龍回答:“你可以在這兒說清楚。”
“如果我可以離開一分鐘時間,就能用實驗來證明。”
“一分鐘,那行呀。”
菲格羅從放咖啡壺的桌子上拿起兩只泡沫塑料杯子,還不到一分鐘,就端著兩杯水回來了。
“沃德龍助理,你是否愿意將一只左手指放進左邊的杯子里,再將一只右手指放進右邊的杯子里?”
“不。先給我解釋清楚,你想干什么。”
“在我做解釋的同時,薩舍拉克也許能演示一下。在我們的工作中一直這么做的。”當菲格羅說這番話的時候,薩舍拉克心領神會。
“一杯是熱水,另一杯是涼水。在發生火災的那天晚上,本尼斯警官在室外曾經將雪拍打在那個小舅子的身體上,隨后便跑回了那個著火的公寓里。他這么做的同時,我正在把那個女人拖出廚房。她的身上摸起來有些發燙,似乎像有燒傷的水皰之類的東西。當我再次進入那間公寓的時候,是摸著滾燙的墻壁前進的。此時,本尼斯警官剛剛從外面返回屋里,所以我們幾乎是同時接觸到莫里特先生的身體。”
薩舍拉克隊長插話說:“我開始明白了。”
“莫里特先生那時已經斷氣了,不過只有十到二十分鐘時間,也許他當時的體溫和我今天的體溫相差無幾。隊長,你可以用手摸一摸我的下臂嗎?”
薩舍拉克照此辦理了。接著他微笑道:“我的右手摸上去是溫暖的,而左手摸上去卻是涼的。”然后他轉身對沃德龍說,“同樣一只手臂,摸上去卻截然不同。”他又朝沃德龍做了個手勢,說,“你要試一下嗎?”
菲格羅和本尼斯坐在他們的巡邏警車里,本尼斯開口道:“再次點撥一下我所經歷的這樁謎案。”
菲格羅大聲長嘆一口氣,然而本尼斯心中明白她喜歡他們的共同經歷。
“雞鳴狗盜之徒決定要去盜竊一所互助會的房子,往往會選擇深夜時分作案——尤其是在一個下著大雪的夜晚。因為未經觸動的積雪可以一直通往公寓的大門口。因此那個盜匪自言自語地說:‘ 如果我倒退著走向大門口,他們就會認為是屋里的某個人偷走了東西,因為找不到沿路走進去的腳印。’”
“這個主意倒也不賴。”本尼斯笑道。
“他就是按照這個方式作案的。他挑選了許多零碎物品,比如一二個錢包,一臺10英寸的電視機或者一臺音響,隨后便離開了。那些小孩早晨起床后發現失竊現象,便報了警,我們這些警察趕到現場,看見了那些腳印。我們一般會根據有過小偷小摸案底的線索,在該社區內追查作案者。可是當我們把懷疑對象抓來的時候,他反而迷惑不解了。他會對于雪地里的那些腳印提出質疑——明顯只有走出去的腳印,而沒有走進屋內的腳印呀?現在,本尼斯,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
“因此他就會說——真是裝腔作勢:‘你們想想看,雪地里的腳印像這種樣子,你們來解釋一下,究竟是房子內部的人作的案,還是外來者作的案。’”
“真狡猾。”
“是呀,我們便說:‘我們根據腳印來判斷,就是外來者作的案。’他驚奇萬分地說:‘那絕不可能!我當時是倒退著走進去,然后倒退著走出來的!’”
蘇茜·菲格羅咯咯地笑著說:“那些小偷是狡猾,可是他們絕不會變得聰明。”
“你瞧,菲格羅,就像這個火災的案子一樣。你觀察判斷所有情況的角度,就反其道而行之了。”
“沒錯,本尼斯。吸取經驗教訓吧。在下班后想要看場電影么?”
他謹慎地朝周圍觀察了一番,確定沒有人看見他們后,便將他的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我要帶著你一起去吃晚餐,菲格羅。我們已經錯過了情人節。”
責任編輯/筱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