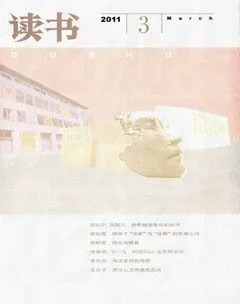獵頭與獵身
二○○一年,我應邀參加在加拿大卑詩大學(UBC)舉行的一個國際移民學術研討會。會上,一位加拿大學者在談及當今技術人才跨國流動之社會影響時,揮舞著拳頭激動地大聲說道:“是千百萬中國農民養(yǎng)育了比爾·蓋茨!”其時正是比爾·蓋茨的微軟事業(yè)如日中天之時,此言一出,全場一陣唏噓聲。作為當時在場唯一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我深感心靈受到強烈震撼!在那之后,每當我探討國際移民之社會影響時,腦海里總會不自覺地浮現出當年會議的場景;也是從那之后,每年在給學生講授“移民社會學”課程時,我總會論及“中國農民與比爾·蓋茨”命題。我的理解:因為中國農民養(yǎng)育了無數IT業(yè)青年才俊,其中不少加入比爾·蓋茨的微軟為其效力,以寶貴的青春年華和知識才干將微軟推向了IT業(yè)的巔峰,因此可以說,是千百萬中國農民養(yǎng)育了比爾·蓋茨。
近日,我饒有興味地一口氣讀完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項飚博士的英文專著《全球獵身:從信息產業(yè)看印度勞工體系》(以下簡稱《獵身》)。幾乎從開卷伊始,“中國農民與比爾·蓋茨”的命題就一直跳躍在字里行間。我想,如果當時項飚在場的話,他一定還要補充一句:養(yǎng)育了比爾·蓋茨的還有千百萬印度農民!更重要的是,細讀全書,咀嚼作者如何將印度IT人跨國流動提升到經濟全球化與當代勞動力市場重構的制度性層面進行剖析,深感言近旨遠,入木三分。
如果不算附錄的話,《獵身》一書不過百來頁,描述的現象也簡單明了:自上世紀末葉以來,印度各地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大量被稱為“技能店”(T-shop)的私立IT技術培訓學校,吸引了成千上萬懷揣致富夢想的印度青年。他們?yōu)榱四軌蛉胄W藝而想方設法籌措高額學費,好不容易獲得一紙證書后,又為能夠盡快出國務工而向勞務中介行繳納五花八門的費用。他們夢寐以求的就是早日奔向被譽為“IT麥加”的美國,從而實現“在(印度)農村有地,在(印度)城市有房,在美國有高薪工作”的IT夢。
很容易,這會被寫成一個學人們已經重復過無數次的“跨國遷移實現脫貧致富”的故事。然而,《獵身》的價值卻在于它脫出了此類老生常談之窠臼,另辟蹊徑。該書以印度勞動力流動制度架構中特殊的“獵身行”(Body Shop)為切入點,追蹤印度IT青年如何實現跨國流動的全過程,在展示一個立足印度、全球運作、號稱“獵身”之信息產業(yè)勞動力管理體系的同時,剖析這一特殊的勞動力群體價值如何在全球化體系內被創(chuàng)造、被利用、被增值,進而指出:跨國化獵身操作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構建了新的跨界流動紐帶,還在于它體現了創(chuàng)造財富的新戰(zhàn)略,轉移價值的新途徑,以及全球社會不平等的新模式。
獵頭與獵身
我曾經為該書的英文書名《Global “Body Shopping”》如何準確譯為中文犯難:如果直譯為“全球賣身”,恐怕讀者立馬聯想到的就是色情業(yè)“小姐”。當我向項飚討教、得知他已經將書名意譯為《全球“獵身”》時,不能不為之拍案叫絕。“獵身”源自“獵頭”卻又有別于后者,妙就妙在巧用“獵”之“迅速尋找與購買”之意,卻又區(qū)分出“身”與“頭”之別,而如此創(chuàng)意完全基于對印度IT人培養(yǎng)、雇用、流動之系列流程的深刻洞察。
IT業(yè)無疑是高科技行業(yè),IT從業(yè)者是公認的技術人才,然而,構成IT業(yè)基礎的大量“程序員”日以繼夜所從事的,卻是《獵身》所描繪的“沉悶乏味、單調,且收入偏低的所謂‘驢活’(印度IT人語)。”因為,無論是編程、檢測或試錯,都需要能夠熟練運用在業(yè)外人眼里如天書般的專業(yè)代碼,但是,其工作過程卻是在看似潔凈、舒適的環(huán)境中,埋頭從事沒有多少創(chuàng)造性、卻極度耗費時間、腦力直至體力的艱苦工作。尤其在大型軟件工程的編寫測試過程中,基層程序員個人的作用,是確確實實的“螺絲釘”。因而在我國,也有IT程序員不時自我調侃是“IT民工”。
由此,就形成了一對耐人尋味的悖論:由于IT業(yè)不斷展示出的“神奇魅力”,IT人被罩上“科技人才”之光環(huán),因此需要“獵”;然而,由于IT業(yè)實際上需要的是大批專業(yè)的“IT民工”干“驢活”,因此被獵的是“身”而非“頭”。雖然軟件通過程序控制的合理化、標準化、自動化從而提升使用者之效益,但軟件開發(fā)自身卻充滿了不確定性。近二三十年來,以美國為首之發(fā)達國家IT業(yè)高速增長的基礎,正是通過增加軟件開發(fā)的人力投入不斷試錯,“即便是最著名的(IT)成功故事……也有賴于大量的無償勞動力,以克服軟件生產過程本身的低效和瓶頸”(K. Ei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