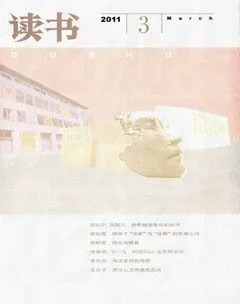品特的“政治轉(zhuǎn)向”
冥冥之中,我感到自己與品特有緣。正式接觸品特,是在進入中央戲劇學(xué)院之后。在此之前,零星讀過他的《看管人》(許真譯,收入袁可嘉、董衡巽、鄭克魯選編的《外國現(xiàn)代派作品選》)和《送菜升降機》(施咸榮譯,收入朱紅作序的《荒誕派戲劇集》),這兩部翻譯作品集當(dāng)時在國內(nèi)影響很大,但我未曾特別注意到其中的品特。進入中戲讀博,師從廖可兌先生,在系統(tǒng)學(xué)習(xí)西方戲劇史的時候,我對品特有了更多的了解。一九九○年,同在中戲讀研的孟京輝導(dǎo)演了《送菜升降機》,后來,他將此次演出稱作他“與品特的初戀”。我當(dāng)時觀看了他的演出,第一次產(chǎn)生了對品特的濃厚興趣。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對品特的研究成為一個組成部分。二○○五年,品特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二○○七年我申請國家項目“哈羅德·品特戲劇研究”,獲得批準(zhǔn)。為進行這項研究,二○○八年,我應(yīng)彼得·拉比教授之邀,赴劍橋大學(xué)訪學(xué)交流。當(dāng)時曾想拜訪品特,但拉比告訴我說品特已因喉癌臥病在床,我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回國之后,我與譯林出版社簽訂了有關(guān)品特戲劇選的翻譯合同,開始著手翻譯,當(dāng)時想盡快將戲劇選集出版,讓品特在其有生之年看到自己作品的中文版,但是,這個愿望未能實現(xiàn),品特于當(dāng)年駕鶴歸西。如今選集終于出版,希望能以此慰藉品特的在天之靈。
品特創(chuàng)作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威脅的喜劇”、“家庭戲劇”、“記憶的戲劇”和“政治戲劇”。我將其中“威脅的喜劇”和“記憶的戲劇”分別看成是人對于生存空間與時間的感受和哲學(xué)思考,“家庭戲劇”是對家庭關(guān)系與矛盾的現(xiàn)實主義分析與表現(xiàn),而“政治戲劇”則是對于現(xiàn)實生活中迫害與被迫害的直接而又激烈的反映。
品特第一部戲劇《房間》(一九五七)上演之后不久,評論家哈羅德·霍布森寫道,“(這部戲劇)具有尤涅斯庫的味道和貝克特的回聲”,從而將他與荒誕派戲劇聯(lián)系在一起。在《荒誕派戲劇》(一九六一)一書中,作者馬丁·艾斯林明確地將品特置于荒誕派作家的行列,強調(diào)了荒誕派戲劇的哲學(xué)性,將其與布萊希特史詩劇的政治性進行比較,實際上就是說品特等荒誕派戲劇家基本上是非政治的。這種觀點當(dāng)時被品特本人所認(rèn)可,早在一九六一年品特就宣布:“作為一個作家,在通常的意義上,我既不介入宗教也不介入政治。我沒有心存任何特別的社會目的。”而到了一九八九年,有人對他說“你一直是一位政治劇作家”的時候,他卻說:“我想早年,事實上是三十年前,我就算是政治劇作家了。”二○○○年,品特最早的戲劇《房間》與最新的戲劇《慶典》在倫敦同場演出,在接受采訪時,品特認(rèn)為以上兩部戲劇的共同之處就是涉及暴力問題,有位學(xué)者這樣說道:“非常有趣——你剛才談到的是一種關(guān)于戲劇的政治性的闡釋。”而品特的回答是:“噢,是的,絕對如此。”
可見,品特的前后戲劇創(chuàng)作和思想傾向似乎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政治轉(zhuǎn)向。對于他的這種轉(zhuǎn)變,英國批評界和公眾反應(yīng)不一。
無疑,早年的品特?zé)o論是在創(chuàng)作上還是在生活中,都與政治保持著相當(dāng)?shù)木嚯x,這在當(dāng)時的戲劇環(huán)境中尤其明顯。一九五六年,約翰·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首演,此時奧斯本、阿諾德·威斯克、約翰·阿登和愛德華·邦德等“憤怒的青年”正在英國劇壇橫沖直撞。他們直面英國的社會現(xiàn)實,在作品中宣泄自己的政治怒火。而品特卻與他們不同,從而被歸入了“荒誕派”行列,他的戲劇顯然是哲學(xué)性的,雖然他也受前者的強烈影響,作品具有那種所謂“廚房水槽現(xiàn)實主義”的風(fēng)格,特別是在細(xì)節(jié)上。
后來的品特有了巨大轉(zhuǎn)變,其后期作品絕大多數(shù)是傾向鮮明的“政治戲劇”。不僅如此,品特還積極投身政治。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末期,品特先后在各種場合就國際與國內(nèi)政治問題旗幟鮮明地發(fā)表意見,對于土耳其政府鎮(zhèn)壓庫爾德人、美國顛覆尼加拉瓜桑地諾政權(quán)和智利左翼政府提出抗議,指責(zé)撒切爾夫人領(lǐng)導(dǎo)的政府及其右翼政策。一九八六年,品特與其夫人安東尼婭·弗雷澤女士在家中組建了“六月二十日協(xié)會”,這是一個眾多左翼人士參加的定期討論會,活動直至一九九二年解散。
品特這一政治轉(zhuǎn)向,一直使人們感到疑惑。其實,這有著外部社會與個人內(nèi)在兩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一系列國際性的、主要是美國對于左翼政權(quán)的顛覆與干預(yù)事件,以及英國國內(nèi)右翼勢力的猖獗;二是品特與許多左翼朋友的密切接觸與相互影響。然而,更重要的是內(nèi)因,即品特本人的總體觀念,這又體現(xiàn)在他的宗教觀念、種族觀念、政治觀念和社會觀念上。
品特出身于猶太教家庭,從小接受猶太教的教育。但按照他的說法:“我去上課,因為我知道我只能去,我決定不了這件事情。但是過了十三歲,就是這樣,我永遠(yuǎn)地與宗教分手了。”品特與宗教的決裂與其母親及家族影響有關(guān),其父親的家族屬于猶太正統(tǒng),而母親的家族比較世俗,曾有人問其母親是否上猶太會堂,她堅定地回答:“不,猶太會堂屬于那些負(fù)罪感強烈的人。”品特在與宗教分手之前進行了怎樣的思想斗爭,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看看《懺悔錄》中奧古斯丁皈依宗教的精神歷程是多么痛苦,就可以想象品特做出脫離宗教的決定也非易事。
正如猶太人的宗教意識與猶太人的種族意識息息相關(guān)一樣,與品特的宗教觀念直接相關(guān)的是他的種族觀念。在歷史上,猶太民族多次長時期地遭受苦難。品特生于一九三○年,少年時代正值“二戰(zhàn)”前后。一九三二年,以奧斯瓦爾德·莫斯利勛爵為首的英國法西斯主義者聯(lián)盟成立(時至今日,互聯(lián)網(wǎng)上還有其相關(guān)網(wǎng)站),一九三四年,反猶主義成為它的綱領(lǐng)。在“二戰(zhàn)”之前一段時間及戰(zhàn)爭期間,納粹法西斯對德國國內(nèi)和歐洲境內(nèi)的猶太人進行了大規(guī)模迫害和種族滅絕。“二戰(zhàn)”期間,法西斯主義在英國偃旗息鼓了。但是“二戰(zhàn)”結(jié)束之后,法西斯主義又在英國死灰復(fù)燃。少年品特曾經(jīng)直接受到反猶勢力的人身威脅,幾乎爆發(fā)肢體沖突。所有這一切,肯定都在品特心中留下了陰影,并體現(xiàn)在其“威脅的喜劇”中。這里的“威脅”很大程度上就來自品特作為猶太人對于生存空間受到壓迫的感受。這些壓迫在多種層面、多種角度上存在:國際的與國內(nèi)的,宗教的與種族的,精神的與肉體的,經(jīng)濟的與政治的,社會的與個人的等等。毫無疑問,品特對于本民族的苦難有著強烈的意識。上世紀(jì)五十年代,在一家酒吧里,年輕的品特曾經(jīng)因為一個家伙當(dāng)著他的面侮辱猶太人而向?qū)Ψ桨l(fā)起攻擊,結(jié)果雙雙被帶進了警察局。當(dāng)被問及為何如此兇狠的時候,他的回答是:“不是因為他侮辱了我,而是因為他侮辱了許多其他人。他侮辱了死去的人,受難的人。”
然而,品特的民族認(rèn)同不是無條件的。猶太民族長期懷有強烈的復(fù)國主義情緒,而英國則是現(xiàn)代猶太復(fù)國主義的策源地。品特的父親就是一位猶太復(fù)國主義者,他毫無保留地?fù)碜o以色列政府的民族主義政策。而在對待以色列國家的態(tài)度上,品特則顯示出完全獨立的、努力公正的立場。他公開批評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難民的態(tài)度,抗議以色列因核武器計劃被揭露而對和平主義者、工程師瓦努努進行監(jiān)禁,為此,他甚至親自參加了位于倫敦的以色列駐英國大使館門外的游行集會。品特也許對猶太人有更高的要求,但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人類正義的。
在宗教和種族的問題上,品特與他所喜歡并深受其影響的卡夫卡十分相似,他們盡管與猶太人身份和猶太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都拒絕成為猶太復(fù)國主義者和猶太教徒。不同的是,與卡夫卡相比,品特在這兩個問題上更加理智,態(tài)度也更鮮明。
在品特身上,種族與政治身份有著某種聯(lián)系。對于戰(zhàn)后英國極右翼分子和死灰復(fù)燃的法西斯主義來說,猶太人和共產(chǎn)主義者是最主要的種族與政治仇敵。有一次,品特和他的“男孩幫”一起參加一個“英國國家黨”(戰(zhàn)后成立的英國極右翼政黨)的集會,會上他們中有人被指為“共產(chǎn)主義分子”,以致發(fā)生了暴力沖突。而用品特自己的話說就是“每一個人都遭遇過這樣那樣的暴力。在戰(zhàn)后的倫敦東部,我就遇到過它的極端形式,當(dāng)時法西斯主義在英格蘭卷土重來。我在那兒參加了多次打斗。如果你看起來有點兒像猶太人,你就可能遇上麻煩。還有,我去一家猶太人俱樂部,在一座舊鐵路拱橋旁邊,有好多人經(jīng)常等在我們必須經(jīng)過的一條巷子里,手里拿著破奶瓶。……我們經(jīng)常被當(dāng)做共產(chǎn)主義者。如果你走過,或者碰巧經(jīng)過一場法西斯主義的街頭集會,眼光帶有對立情緒——就是在里德利街市場,靠近達(dá)爾斯頓樞紐站——他們就會把你當(dāng)成共產(chǎn)主義者,特別是你胳膊下夾著書本的話。在那些日子里,那兒充斥著暴力”。作為猶太人,品特在感受到種族歧視的同時,一定也體會到了共產(chǎn)主義者受到的政治歧視,這種共同的受壓迫感導(dǎo)致他對于左翼思想產(chǎn)生了親近感。
品特曾經(jīng)就讀于倫敦皇家戲劇藝術(shù)學(xué)院,然而,這位戲劇家對于這座英國最高等的戲劇藝術(shù)學(xué)府印象很壞,他說自己“根本就受不了那個地方”。他討厭那里的任課教師,而任課教師也討厭他。他不斷地逃學(xué),但不告訴家里。對教育制度的厭惡只是他社會反叛的序幕,而對兵役制度的抗拒則是其高潮。一九四八年夏天,蘇聯(lián)圍困西柏林,美國將核武器運到了英國的軍事基地,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正是在這種嚴(yán)酷的冷戰(zhàn)氛圍中,當(dāng)年十月,十八歲的品特接到了兵役征召通知書,然而他毫不猶豫地明確選擇成為“良心拒絕者”(出于宗教或者道德上的原因而拒絕服兵役者)。為此,他受到了來自家庭與社會的巨大壓力,父母要求他回心轉(zhuǎn)意,而軍事法庭則兩次傳喚了他。他在法庭上嚴(yán)肅地回答說,戰(zhàn)爭意味著大量生命的死亡。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沒有求助于宗教信仰的庇護。結(jié)果他被罰款一百二十五英鎊,父親為他繳清,這對于那位可憐的窮裁縫來說,當(dāng)時已是一大筆錢。應(yīng)該說明的是,品特充當(dāng)“良心拒絕者”并非出自某種特別明確的宗教、倫理或者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某種本能性的良知,以及對國家機器或者官僚機構(gòu)的拒斥。
這就是年輕時代的品特,他不一定是無神論者,肯定不是反猶主義者、共產(chǎn)黨人或者無政府主義者,他不是任何既定學(xué)說、理論或者主義的忠實信徒。但是,此時的他在宗教、種族、政治觀念上,都與社會主流截然不同,甚至公然與之對抗。他是真正的特立獨行的個人,勇敢地面對龐大的社會。早期,他超然世外,然而在他身上,已植入了異端思想的基因,在后來面對嚴(yán)酷現(xiàn)實的時候,就發(fā)展成為明確的政治傾向。
(品特戲劇選集:《歸于塵土》、《送菜升降機》,華明譯,譯林出版社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