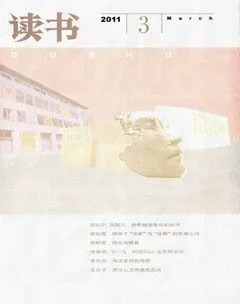“上念前
在古代文學(xué)研究的百年學(xué)術(shù)史上,錢穆的相關(guān)著述一直影響不彰。這固然由于錢氏是現(xiàn)代史學(xué)大家,其文學(xué)研究成就為史學(xué)聲名所掩。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他對(duì)具體作家、作品的評(píng)價(jià)和對(duì)文學(xué)史流變的主要見解,都與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的主流傳統(tǒng)大異其趣。在《漫談新舊文學(xué)》一文里,他曾這樣寫道:
及余四十左右,乃讀魯迅等新文學(xué),如《阿Q正傳》。自念余為一教書匠,身居當(dāng)時(shí)北平危城中,中日戰(zhàn)爭(zhēng),如弦上箭,一觸即發(fā)。而猶能潛心中國(guó)古籍,以孔老二之道為教,若尚有無(wú)限希望在后,此正一種阿Q心情也。使余遲生數(shù)十年,即沉浸在當(dāng)時(shí)之新文學(xué)氣氛中,又何得為今日之余。余嘗自笑此一種阿Q心情,乃以上念前古,下盼來(lái)者……
錢穆一八九五年出生,他慶幸早生了數(shù)十年,在人生前期即已形成對(duì)于古代文學(xué)相對(duì)穩(wěn)定、成熟的看法。另一方面,百年人生,大部分時(shí)間在“新文學(xué)氣氛”里度過(guò),壯懷激烈,出入古今,這也使得他可以憑借新文學(xué)及其所接受的西方文學(xué)觀念的全新參照系,細(xì)心觀察、思考和沉淀古代文學(xué)及其研究的利弊、得失。雖然,在一意西化的時(shí)代,錢穆終也不免眾里身單,以阿Q自嘲,但“上念前古,下盼來(lái)者”,他對(duì)于古代文學(xué)的溫情與敬意,連同這一份寂寞堅(jiān)守的苦心孤詣,都應(yīng)該成為我們重拾中國(guó)文化、中國(guó)文學(xué)自信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錢穆論古代文學(xué),首要的一個(gè)特點(diǎn),就是強(qiáng)調(diào)須將文學(xué)置于中國(guó)文化的傳統(tǒng)與體系之中,視之為中國(guó)文化的一種特有精神。“一部理想的文學(xué)史,必然該以這一民族的全部文化史來(lái)作背景,而后可以說(shuō)明此一部文學(xué)史之內(nèi)在精神。反過(guò)來(lái)講,若使有一部夠理想的文學(xué)史,真能勝任而愉快,在這里面,也必然可以透露出這一民族的全部文化史的內(nèi)在精義來(lái)。”(《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與神話》)
在《中國(guó)文化史導(dǎo)論》一書里,錢穆一開頭就指出,“只有中國(guó)文化,開始便在一個(gè)復(fù)雜而廣大的地面上展開”,與埃及、巴比倫和印度始終局限在一個(gè)小面積里的情形大不相同。這一中國(guó)文化特點(diǎn)表現(xiàn)在文學(xué)上即所謂“雅化”。以《詩(shī)經(jīng)》為例,其中的大雅、小雅,是西周政府里的作品,西周建都鎬京,“雅”原本指當(dāng)?shù)氐姆窖院头窖砸簟5驗(yàn)橹苁且粋€(gè)統(tǒng)一的王朝,各地封建諸侯貴族,十之七八是周人,其他十之一二亦須依隨周王室,模仿其雅言雅音。“雅”,可以說(shuō)是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通行的普通話。雅也因此而成為文學(xué)走出狹窄區(qū)域、超越“地方化”的一項(xiàng)必要條件。如《詩(shī)經(jīng)》十五國(guó)風(fēng),本分布在極為廣闊的地域,但它們由采詩(shī)官?gòu)母鞯厥占鴣?lái),譯成雅言,譜成雅樂(lè),風(fēng)格意境相差并不甚遠(yuǎn)。再如《楚辭》,其中《九歌》等作品,本來(lái)是江湘之間楚地的民歌,只因經(jīng)過(guò)了屈原的修改與潤(rùn)色,才雅化成為世所公認(rèn)的文學(xué)杰作。無(wú)論是《國(guó)風(fēng)》還是楚歌,它們雖然在各自的區(qū)域內(nèi)部可以成為地方文學(xué)的名作,但必須符合全國(guó)范圍內(nèi)通行的雅言標(biāo)準(zhǔn),才能成為中國(guó)文學(xué),才能列入中國(guó)文學(xué)史。
以《詩(shī)經(jīng)》和楚辭為源頭,雅化一直是中國(guó)文學(xué)演進(jìn)的主要特色。而圍繞著雅化,還有兩點(diǎn)值得注意。一是雅化與文字的關(guān)系。中國(guó)文字舉世無(wú)匹,自成一系,始終與語(yǔ)言不即不離,相為吞吐。如《方言》說(shuō):“眉、梨、耋、鮐,老也。”齊人說(shuō)“眉”,燕人說(shuō)“梨”,宋衛(wèi)人說(shuō)“耋”,秦晉人說(shuō)“鮐”,如果一任發(fā)展,必然方言日淆,文字多歧。但中國(guó)文化一開始就在廣闊的范圍內(nèi)展開,周尚雅言,秦法同文,眉、梨、耋、鮐等便統(tǒng)一為“老”字所取代。中國(guó)文字還常以舊形舊字表新音新義,以適應(yīng)后世新興事物的需要。如車輪外胎,古文曰“”曰“”,今直言車胎或橡皮車胎,不必另創(chuàng)橡橡之類的專名,更不必為橡皮車胎另造新字。這些文字特點(diǎn),構(gòu)成了古代文學(xué)雅化發(fā)展的基礎(chǔ)。
二是雅化使古代文學(xué)與社會(huì)政治結(jié)下不解之緣。因?yàn)檫\(yùn)用雅化的人,大都是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上層的貴族,他們最優(yōu)先注意的必然是政治教化,必然是實(shí)際社會(huì)應(yīng)用。錢穆曾以飽蘸熱情的歷史想象力描寫當(dāng)時(shí)朝會(huì)賦詩(shī)的生動(dòng)場(chǎng)景:“四方諸侯,既來(lái)助祭于四方宗廟,親聆《清廟》之頌,退而有大朝會(huì),又親聆《大雅·文王》之詩(shī)。于是于其離去,周天子又親加宴饗,工歌《鹿鳴》之詩(shī)以慰勞之。……其殷勤之厚意,好德之虛懷,豈不使來(lái)為之賓者,各有以悅服于其中而長(zhǎng)使之有以盡忠竭誠(chéng)于我乎?”(《讀〈詩(shī)經(jīng)〉》)可見,《詩(shī)經(jīng)》雖然自具深美的文學(xué)意義與價(jià)值,但深美的文學(xué)性,必須與政教有關(guān),必須對(duì)政教有用。
“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陸游這一聯(lián)詩(shī),《紅樓夢(mèng)》里的一個(gè)丫鬟很喜歡,拿去問(wèn)林黛玉。黛玉說(shuō),這種詩(shī)千萬(wàn)不能學(xué),學(xué)作這樣的詩(shī),你就不會(huì)作詩(shī)了;你應(yīng)當(dāng)讀王摩詰、杜甫、李白跟陶淵明的詩(shī),每一家讀幾十首,或是一兩百首,了解之后,就會(huì)懂得作詩(shī)了。錢穆認(rèn)為黛玉這一段話講得很有意思,因?yàn)樗龑?shí)際上指出了陸詩(shī)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背后沒(méi)有人。錢穆由此講到中國(guó)詩(shī)、中國(guó)文學(xué)的最高境界,就是作品背后有一個(gè)人,須要將作家與作品緊密結(jié)合,并且把作家置于第一位。“作家不因于其作品而偉大,乃是作品因于此作家而崇高也。”(《中國(guó)文化與中國(guó)文學(xué)》)比如蘇軾,其前后《赤壁賦》千古美文,婦孺?zhèn)髡b,但也須將之置于東坡全集之中,結(jié)合其政治、人生際遇,才能更好地理解。東坡當(dāng)年自獲罪而下獄,自獄釋放而貶黃州,自卜居臨皋而游赤壁,數(shù)年之間波譎云詭、死生莫測(cè),所經(jīng)所歷都在這一時(shí)期的詩(shī)詞信札、隨筆雜文之中逐年逐月、逐日逐事記錄下來(lái)。將東坡全集按編年順序讀下來(lái),才能真切體會(huì)到當(dāng)時(shí)東坡赤壁之游的心胸與修養(yǎng)。尤須留意的是,東坡當(dāng)年,在他掌守徐州的時(shí)候,自然不知道將有烏臺(tái)詩(shī)案;被投獄中,不知將有黃州之貶;待罪黃州,也不知將有赤壁之游。所以,他在此期間所寫下的一切,不過(guò)是隨時(shí)隨地的隨意抒寫,不過(guò)是必須自己親身應(yīng)接的普通日常生活而已。但也正因?yàn)槿绱耍攀侵袊?guó)文學(xué)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也就是所謂君子無(wú)入而不自得之境界。
錢穆因此指出,讀古代詩(shī)人如不讀全集,特別是像讀杜甫、讀蘇軾那樣按照年譜一首一首去讀,而只讀選本,如《唐詩(shī)別裁》之類,又愛看選家批語(yǔ),這一字下得好,這一句寫得好,這樣最多領(lǐng)略了些作詩(shī)的技巧,永遠(yuǎn)讀不到詩(shī)的最高境界去。“比如讀《全唐詩(shī)》,等于跑進(jìn)一個(gè)大會(huì)場(chǎng),盡多人,但一個(gè)都不認(rèn)識(shí),這有什么意思,還不如找一兩個(gè)人談?wù)勑摹!保ā墩勗?shī)》)
中國(guó)文學(xué)貴能將作者自己放進(jìn)作品之中去,中國(guó)藝術(shù)亦然。歐陽(yáng)修《筆說(shuō)》云:“古之人皆能書,獨(dú)其人之賢者傳遂遠(yuǎn)。……使顏公書雖不佳,后世見之必寶也。”錢穆?lián)艘暾f(shuō),中國(guó)社會(huì)向來(lái)重視作者勝過(guò)重視作品,甚至連古跡名勝也不例外。如秦始皇之阿房宮,單論建筑,不可謂不偉瑰絕倫,然楚人付之一炬,人不足惜;嚴(yán)子陵釣臺(tái),只不過(guò)是傳說(shuō)而已,但人們明知羌無(wú)故實(shí),終是流連憑吊,相認(rèn)為名勝(《讀歐陽(yáng)文忠公筆記》)。所以在重視作者這一點(diǎn)上,詩(shī)畫、書法、建筑,無(wú)不一律。
錢穆著力闡發(fā)古代文學(xué)的雅化和作者第一,還包含著另一層深意,即與新文學(xué)形成映照。新文學(xué)強(qiáng)調(diào)白話俗語(yǔ)文學(xué)、平民文學(xué),作者與作品分離,并將這些當(dāng)代意識(shí)反轉(zhuǎn)來(lái)重新評(píng)價(jià)甚至批判古代文學(xué)。錢穆對(duì)此大不以為然。“近代的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似乎絕不肯承認(rèn)民族間可以有相異之特性,更不肯承認(rèn)中國(guó)人可以有相異于西方之特性。”(《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與神話》)不過(guò),錢穆不滿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及其影響所生的新文學(xué),卻又不是簡(jiǎn)單地一概排斥,而是對(duì)純文學(xué)、俗文學(xué)等觀念與實(shí)踐,在傳統(tǒng)的脈絡(luò)里安置恰當(dāng)?shù)奈恢茫赋鏊鼈冊(cè)舅幍膶哟巍?br/> 在《讀〈文選〉》一文中,錢穆指出古代所謂純文學(xué)觀念,實(shí)際上經(jīng)過(guò)了一個(gè)漫長(zhǎng)的發(fā)展流變。古之為文,如經(jīng)史百家,都是產(chǎn)生于實(shí)際社會(huì)應(yīng)用的需要,此一時(shí)期,有文章而無(wú)文人。下逮兩漢,西漢有儒林,無(wú)文苑,但鄒陽(yáng)、枚乘、司馬相如等人不列儒林,是先已有文人之格,而無(wú)文人之稱。東漢始專為文苑立傳,出現(xiàn)了所謂文人。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其特征是無(wú)意于為人事實(shí)用的目的作文。但東漢文人尚沒(méi)有達(dá)到專一純意于作文的程度。真正意義上的文人之文,要到建安魏晉時(shí)期才出現(xiàn),“僅以個(gè)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為題材,抒寫性靈,歌唱情感,不復(fù)以世用攖懷”。不過(guò),錢穆指出,“文人乃人中之一格,文人之文,亦文中之一格”而已,《文選》“專據(jù)文人意境作文選文,奉為唯一之標(biāo)格,亦是所見不廣,因之文運(yùn)衰而世運(yùn)亦衰矣”。
至于俗文學(xué),在中國(guó)也不是沒(méi)有,不過(guò)同樣發(fā)展較遲、較后起。“中國(guó)之有俗文學(xué),在其開始之際,即已孕育于極濃厚之雅文學(xué)傳統(tǒng)之內(nèi),而多吸收有雅文學(xué)之舊產(chǎn)。”(《讀〈詩(shī)經(jīng)〉》)延續(xù)這種一貫的雅化觀點(diǎn),錢穆《中國(guó)文學(xué)史概觀》一文認(rèn)為,中國(guó)文學(xué)大體可分“政治性的上層文學(xué)”和“社會(huì)性的下層文學(xué)”兩種。自詩(shī)騷以訖秦漢,除漢樂(lè)府多為社會(huì)性下層文學(xué)以外,都是政治性上層文學(xué)的時(shí)代。漢末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以文之綺麗為工。迨至唐代,陳子昂、杜甫、韓愈等人倡導(dǎo)詩(shī)文革新,但其時(shí)抒寫日常生活私人情志漸已成文學(xué)的普遍現(xiàn)象,即使是杜甫、韓愈的詩(shī)文集,按年編排,即成年譜。不過(guò)重要的是,唐代詩(shī)文革新重新確立了新的文學(xué)傳統(tǒng)和標(biāo)準(zhǔn)。“私人之出處進(jìn)退,際遇窮達(dá),家庭友朋悲歡聚散,幾乎無(wú)一不足為當(dāng)代歷史作寫照,此成為唐以下文學(xué)一新傳統(tǒng)。其作品之價(jià)值高下,亦胥可懸此標(biāo)準(zhǔn)為衡量。”換句話說(shuō),面對(duì)魏晉以來(lái)的文學(xué)新變,完全回避和否定已不可能,乃轉(zhuǎn)而為之制訂基于先秦兩漢以來(lái)文學(xué)傳統(tǒng)的標(biāo)準(zhǔn)和規(guī)范。在此,錢穆提出一個(gè)值得注意的概念詞語(yǔ)——通達(dá)。由于社會(huì)下層文學(xué)實(shí)有兩個(gè)短處,一是為私不為公,一是只有作品不見作者,未能十足透露出中國(guó)文學(xué)傳統(tǒng)精神之所在。所以,“下層文學(xué)亦必能通達(dá)于上層,乃始有意義,有價(jià)值”。
持此標(biāo)準(zhǔn),錢穆論唐以下興盛乃至于泛濫的社會(huì)性下層文學(xué),實(shí)際上視其“通達(dá)”與否,又將它們分成了兩部分區(qū)別看待。如元?jiǎng)。洹白髡咧裱},處處仍可窺見其遠(yuǎn)自詩(shī)騷以來(lái)之中國(guó)舊傳統(tǒng)。家國(guó)興亡實(shí)在其深憶遠(yuǎn)慨中,而吐露于不自覺”。《水滸傳》、《三國(guó)演義》、《西游記》和《金瓶梅》四大名著,后兩部“只具游戲性、娛樂(lè)性,……內(nèi)不見作者之心意,外不見作者所教導(dǎo)”。中晚明以來(lái),俗態(tài)畢露,作家心中已無(wú)一大傳統(tǒng)存在,除少數(shù)例外,包括今人奉為無(wú)上拱璧之《紅樓夢(mèng)》在內(nèi),都不過(guò)是失墜了民族傳統(tǒng)的無(wú)足輕重之作:“作者心胸已狹,即就當(dāng)時(shí)滿洲人家庭之由盛轉(zhuǎn)衰,一葉知秋,驚心動(dòng)魄。雪芹乃滿洲人,不問(wèn)中國(guó)事猶可,乃并此亦不關(guān)心,而惟兒女私情亭榭興落,存其胸懷間。……其所得于中國(guó)傳統(tǒng)之文學(xué)陶冶者,亦僅依稀為一名士才人而止耳。”
對(duì)于古代文學(xué)與新文學(xué)之間的差異,錢穆還有一個(gè)重要的觀察,那就是古代文學(xué)往往在繼承和消化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guò)相對(duì)漫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而漸進(jìn)演變,新文學(xué)則接受西方影響,熱衷于通過(guò)對(duì)傳統(tǒng)的激烈顛覆而促成革命。
以新文學(xué)革命的觀點(diǎn)看待古代文學(xué),則無(wú)往而非革命。如胡適一九一六年四月五日《日記》所說(shuō):“文學(xué)革命,在吾國(guó)史上非創(chuàng)見也。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yōu)椤厄}》,一大革命也。又變?yōu)槲逖裕哐裕旁?shī),二大革命也。賦之變?yōu)闊o(wú)韻之駢文,三大革命也。古詩(shī)之變?yōu)槁稍?shī),四大革命也。詩(shī)之變?yōu)樵~,五大革命也。詞之變?yōu)榍瑸閯”荆蟾锩病!倍c胡適這種“革命”的文學(xué)史截然不同,錢穆早在《中國(guó)文化史導(dǎo)論》一書中就曾指出:
中國(guó)歷史只有層層團(tuán)結(jié)和步步擴(kuò)展的一種綿延,很少?gòu)氐淄品c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謂的革命。……西方人看歷史,根本是一個(gè)“變動(dòng)”,常由這一階段變動(dòng)到那一階段。若再?gòu)倪@個(gè)變動(dòng)觀念上加進(jìn)時(shí)間觀念,則謂歷史是“進(jìn)步”的……中國(guó)人的看法,人類歷史的運(yùn)行,不是一種變動(dòng),而是一種轉(zhuǎn)化。不是一種進(jìn)步,而是一種綿延。
錢穆這一概括,是在先秦、南北朝、唐宋元明等時(shí)代多次民族融合、文化澄清基礎(chǔ)上的歷史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在此文化基調(diào)、文化脈絡(luò)下,古代文學(xué)史也是一個(gè)“逐漸轉(zhuǎn)化、綿延”的過(guò)程。如諸子散文,《論語(yǔ)》、《孟子》仍屬于經(jīng)史體例,《墨子》才標(biāo)志著子學(xué)地位的確立,是古代散文的一大進(jìn)步。《墨子》之后有《莊子》。《莊子》恢奇,有意為文,更充分地流露出文學(xué)的趣味和境界,但仍多用寓言體,還算沿襲著古代記言記事的舊體裁。“可見文體演進(jìn),自有步驟,中間必經(jīng)時(shí)間醞釀。文學(xué)上一種新體裁之出現(xiàn),并不容易,并非可以突然而來(lái)。”(《中國(guó)古代散文——從西周至戰(zhàn)國(guó)》)古代文學(xué)的漸進(jìn)演變從作者這一個(gè)側(cè)面也可以看出來(lái)。如古詩(shī)三百首,絕大多數(shù)是無(wú)名作者,但此下演變出楚辭漢賦,都有作者可考。漢樂(lè)府和《古詩(shī)十九首》,亦無(wú)作者姓名,但建安以下五七言詩(shī),都有確切的作者。宋話本都無(wú)作者姓名,但元明雜劇、小說(shuō),又漸多有作者姓名。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乃不斷有新成分之加進(jìn),新方面之開展,惟其事必以漸不以驟,不可以一蹴而冀耳”(《中國(guó)文學(xué)史概觀》)。
在《中國(guó)文化與文藝天地》一文里,錢穆指出金圣嘆的文學(xué)觀點(diǎn),在西方文學(xué)尚未東來(lái)之前,就在許多方面與近代新文學(xué)界的主張不謀而合,但也存在著根本區(qū)別:“金圣嘆的文學(xué)觀念與其文學(xué)理論極富傳統(tǒng)性,只在傳統(tǒng)之下來(lái)迎受開新。而近代人的文學(xué)觀念與文學(xué)理論,則徹頭徹尾崇尚革命性。開新便得要拒舊,而且認(rèn)為非拒舊則不足以開新。”最后,對(duì)于崇尚革命的新文學(xué),錢穆還嘗試將之溯源、接續(xù)到王陽(yáng)明心學(xué)傳人、李卓吾及公安三袁。“民元以來(lái),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躍起,高呼禮教吃人,打倒孔家店,無(wú)忌憚之風(fēng),有過(guò)于萬(wàn)歷。倘言儒,必喜龍溪近溪乃如李卓吾之徒。倘言禪,則無(wú)修無(wú)悟,惟可有驚嘆。惟當(dāng)時(shí)新文學(xué)家亦遂稱道及于公安,然憚窺其全書,因亦不知其學(xué)之出于龍溪近溪,又直躋于禪而超之,否則或可為三袁更張聲氣也。”(《記公安三袁論學(xué)》)這一條線索在古代文學(xué)乃至現(xiàn)代文學(xué)領(lǐng)域都有不少研究,然眾口一咻,都失在未能像錢穆這樣始終立足于一個(gè)“逐漸轉(zhuǎn)化、綿延”的文學(xué)大傳統(tǒng)。
錢穆的古代文學(xué)研究還有著多方面的方法論啟示。歷來(lái)從事古代文學(xué)研究的人,往往竟務(wù)于考據(jù),但如果以考據(jù)來(lái)代替欣賞,就難免一葉蔽目,有可能與更高更大的文學(xué)價(jià)值失之交臂。在《中國(guó)文化與文藝天地》一文里,就《水滸傳》小說(shuō),錢穆現(xiàn)身說(shuō)法,展示了他所理解、欣賞的考據(jù)和一般研究者慣用的考據(jù),在眼光和境界上究有何不同。
關(guān)于《水滸傳》,歷來(lái)考據(jù)的重點(diǎn)集中在何時(shí)成書、作者是否是施耐庵或羅貫中等等。這些在錢穆看來(lái),都忘記了金圣嘆批點(diǎn)七十回本是三百年來(lái)最流行的本子這一事實(shí)。從幼年時(shí)代起,透過(guò)金圣嘆的批點(diǎn),錢穆知道宋江不是一個(gè)如其諢名“及時(shí)雨”那樣的好人,而是一個(gè)假仁假義善用權(quán)謀的大奸猾。在金批本中固然加進(jìn)了批點(diǎn)家的改寫,但就整個(gè)《水滸傳》的演變來(lái)說(shuō),是否一開始宋江就是這樣一個(gè)人,還是逐漸變成這樣的——錢穆認(rèn)為這才是真正需要“考據(jù)”、值得“考據(jù)”的。人們常說(shuō)“逼上梁山”,但所“逼”何來(lái)?眾多水滸人物實(shí)際上是在梁山泊或誘或脅之下被逼入伙,而宋江則為主謀。錢穆以為,在《水滸傳》之編集及內(nèi)容演變過(guò)程中,諸本對(duì)宋江其人的塑造與描寫當(dāng)有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別,一是對(duì)之有稱譽(yù)無(wú)譏刺,另一則如金批七十回本,在稱譽(yù)中隱含了譏刺。大概最先《水滸傳》的作者,雖然對(duì)社會(huì)下層民眾起而造反抱有同情,但對(duì)于一些領(lǐng)袖人物運(yùn)用權(quán)謀、利用群眾運(yùn)動(dòng),則言外頗有不滿或有惋惜之意。至于《水滸傳》之作者,若為施耐庵,錢穆則認(rèn)為與以上《水滸傳》作意的推測(cè)頗為相合。明人王道生作施耐庵《傳記》云:“張士誠(chéng)屢聘耐庵不至。及稱王,造其門,見耐庵正命筆為文,所著為《江湖豪客傳》,即《水滸傳》。頓首對(duì)士誠(chéng)曰:志士立功,英賢報(bào)主,不佞何敢固辭。奈母老不能遠(yuǎn)離。士誠(chéng)不悅,拂袖而去。耐庵恐禍至,舉家遷淮安。洪武初,征書屢下,堅(jiān)辭不赴。”聯(lián)系到《水滸傳》,開頭即安插了一位八十萬(wàn)禁軍教頭王進(jìn),此人神龍見首不見尾。在全書第一回目做此安排,絕非率意。最終王進(jìn)母子俱隱,與施耐庵以母老辭士誠(chéng)、拒明祖,恰可以互參消息。不直宋江,愿為王進(jìn),或許正折射出施耐庵隱微的心跡。
施耐庵、王進(jìn)等人實(shí)代表著元末明初一時(shí)名士的共同心情。這一點(diǎn),錢穆另撰有《讀明初開國(guó)諸臣詩(shī)文集》、《讀明初開國(guó)諸臣詩(shī)文集續(xù)篇》,洋洋數(shù)萬(wàn)言,雖非專為《水滸傳》考據(jù)而作,卻正可援以發(fā)《中國(guó)文化與文藝天地》一文未盡之覆。從宋濂、劉基、高啟、蘇伯衡、貝瓊、胡翰、戴良、方孝孺、楊維楨、趙等人的詩(shī)文集中,錢穆推跡元末明初時(shí)代背景與士人心理。“蓋自元騎入主,華夏大統(tǒng)中絕,諸儒僻處山林,講學(xué)書院,朋徒集,經(jīng)籍義理,猶存兩宋之一脈,此不能謂無(wú)功。”“元政既亂,吾華夏小民揭竿呼嘯而起,乃諸儒率鄙之為盜賊,必欲痛懲嚴(yán)削之,……自方國(guó)珍、張士誠(chéng)、陳友諒之徒,蓋莫不知敬禮儒生,欲引與共圖大事,而諸儒率避之若浼。……不得已而勉就明祖之辟召。然亦姑爾一出,非有忠憤自發(fā)之忱。”(《讀明初開國(guó)諸臣詩(shī)文集續(xù)篇·讀趙東山存稿》)因此,錢穆認(rèn)為“考據(jù)必先把握到一總頭腦處”。而“《水滸》作者同情忠義堂上諸好漢們而不滿于其領(lǐng)袖之一節(jié),實(shí)當(dāng)為討論《水滸傳》作者之作意與其時(shí)代背景之一主要總頭腦。……先不求其總頭腦所在,只在版本上,字句上,循諸小節(jié),羅列異同,恐終不易于細(xì)碎處提出大綱領(lǐng),于雜淺處見出大深意。如此考據(jù),亦復(fù)何用”。這一段治學(xué)感言,不禁令人聯(lián)想起復(fù)旦大學(xué)陳允吉教授對(duì)于陳寅恪治學(xué)特點(diǎn)的一段著名評(píng)語(yǔ):“主要表現(xiàn)在他(陳寅恪)具有過(guò)人的遠(yuǎn)見卓識(shí)。至于在細(xì)密的資料考證方面,倒并不是他最注意的。因此他所提出的一些新見解往往帶有某種預(yù)見或推導(dǎo)的成分,需要后人根據(jù)他提供的線索去發(fā)掘、研究有關(guān)史料,才能得到實(shí)際的證明。”(《韓愈的詩(shī)與佛經(jīng)偈頌》)
錢穆曾撰文論中國(guó)小說(shuō)戲劇中之“中國(guó)心情”,實(shí)際上,他也將自己的“中國(guó)心情”融貫到所欣賞的古代文學(xué)之中。他說(shuō),在中國(guó)文化體系中本無(wú)宗教,但“文章乃經(jīng)國(guó)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這種文學(xué)自信精神就幾乎等于一種宗教精神。所以,杜甫在一生困厄中“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金圣嘆批《西廂》,序文中有“思古人”、“贈(zèng)后人”兩文……“此種境界,實(shí)為中國(guó)標(biāo)準(zhǔn)學(xué)者之一種共同信仰與共同精神之所在。”(《中國(guó)文化與中國(guó)文學(xué)》)在這個(gè)意義上,錢穆之于古代文學(xué),與其說(shuō)是研究,倒不如說(shuō)也是一種信仰的擺渡,一種精神的接力。
(《中國(guó)文學(xué)論叢》,錢穆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二○○二年版;《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思想史論叢》(1—8冊(cè)),錢穆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二○○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