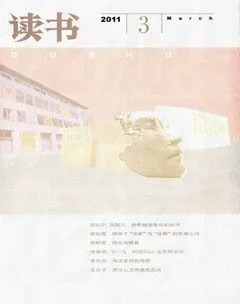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移民史
筆者以為移民史研究有兩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是以葛劍雄主編的《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為代表,在研究方法上與人口史研究相結合,其基本思路是“確定移民的分布范圍——確定各地移民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確定各地標準時點的人口數”,著眼點是“求證本期各次移民的數量和規模”,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歷史時期人口遷徙的原因、方向,人口遷移的數量,在總人口中移民所占的比例等方面。這可以說是一人口遷移史,也可以稱之為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對于此種研究方法,趙世瑜曾在對此書的評論中寫道:“我認為這基本上是沿襲傳統歷史地理學的沿革地理研究路向,依此做出來的將是‘人口遷移史’,而不盡然是移民史。”(趙世瑜:《我是什么人 我是哪里人》,《讀書》一九九九年七期)趙氏認為:“‘人口遷移’只是動態的客觀過程,而‘移民’則是活生生的人或人群,對后者來說,‘移’不是一種無生命的過程,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們的生活史。”若要深化移民史的研究,加深對移民的了解,應該“對這些徙自他鄉的人如何在陌生的土地上艱苦立足、如何處理他們與土著之間的關系等等不可忽視”。趙的看法其實更多的不是針對此書的作者所說的,而是對此后想在移民史研究領域有所發展的后進者指出的一條可能會取得成功的道路,即如何來進一步拓展移民史研究的領域,從移民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地域社會的發展過程。
要回答趙世瑜的疑惑,可能從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路向是不能回答的了,用趙的話說“是另外一部什么書的研究內容”。難能可貴的是,趙在此書評中已指出了若干未來移民史研究可能要處理的幾對關系或者說幾個可以拿來說事的方面,如移民與基層社會組織的關系、移民與社會生活的關系、移民與心理積淀的關系等等。趙的書評是在上個世紀末期所寫,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在移民史研究的個別領域,其實也獲得了發展。如前面談及的移民與心理積淀的關系問題,中山大學的劉志偉教授(《附會、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族歷史傳說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收于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譜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及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解析》,載《歷史研究》二○○六年一期)的研究都取得很大的進展。但移民在移入地如何生根發展、移民與基層社會組織的關系等方面的研究近十年來卻沒有取得多大的進展。要破解這個困局,從地域社會內部出發,或許是一個途徑,這就是筆者所說的有關移民史研究的第二種研究方法。
香港科技大學鄭銳達的《移民、戶籍與宗族:清代至民國期間江西袁州府地區研究》便是一本講述移民社會生活史,解答移民與社會基層組織關系的研究成果。該書利用族譜、戶籍冊等資料,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清初以來移民進入袁州府從入籍到家族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對移民與基層社會組織(里甲制)的關系做了梳理。
明末清初,社會動蕩,袁州府地區的老百姓逃亡甚眾,在此背景下,大量來自閩粵的移民進入到此地區,以種植麻、藍靛、煙草等經濟作物為生。由于山區種麻利潤甚大,而土著卻不善于種麻,以致這些所謂的“棚民”壟斷了種麻的利潤,引起土著極度的不滿。但是,“棚民”也有軟肋,他們本身不種植糧食,必須向土著購買,而這給了土著敲詐、剝削“棚民”提供了機會。在這種背景下,清初袁州府的“棚民”充分利用各種外在的時機作亂,如康熙十三年吳三桂反清,袁州“棚民”朱益吾乘機起事。對于土著與“棚民”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難解的心結。
對于清政府來說,它所關注的問題顯然不是土著與“棚民”之間的心結問題,而是如何將地方應繳納的賦稅足額征收上來的問題。因為長時間戰亂的影響,大量的土著居民逃亡,在里甲制下,一百一十里(或戶)中的剩余里(或戶)的賦稅顯然就要增加。為了減輕賦稅的壓力,清初至中葉,袁州府的地方當局對移民的到來持積極的態度。而這時期,移民(包括“棚民”)入籍也顯得較清后期容易,其途徑大致可分兩種:第一種是外來移民被招入圖甲頂替絕戶;第二種是外來移民未有被編入圖甲組織之內,而是入籍于客圖,取得“客籍”。這兩種情況可以是外來移民入籍的不同階段,即移民進入袁州府后首先入籍于客圖,再進一步就是頂替絕戶,成一般民戶(該書102頁)。
在地域社會發育相對成熟后,在地方資源有限(包括經濟的、文化的)下,移民與土著為了生活而展開的競爭游戲便會逐漸成為地方社會中的“大事件”。清中葉以來,袁州府土著與移民圍繞著是否入籍,也就是“戶籍”的問題糾葛不斷。這個到現在也具有現實意義的話題其實質在于,戶籍不僅僅是個身份證明。更深遠的意義是,戶籍背后擁有一系列讓人渴望得到的資源。就清代的袁州來說,它一方面能確保移民對土地的擁有;另一方面,它也是移民能否參加科舉考試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土著之所以反對,理由很簡單,大量移民的到來,稀釋了土著科舉中第的機會,雖然移民曾幫助土著減輕了他們身上的賦稅負擔。
利益對立,糾紛不斷的情況下,土著開始族群的建構,通過編纂戶籍冊來堵住移民入籍的可能性,“使家有據,戶戶能查,只期共杜將來召頂之弊”(《萍鄉十鄉圖冊·戶籍凡例八則》)。借由此,土著建構了自己的認同與邊界,來確定“我類”與“他類”。這其實反映了土著族群在地方社會中的強勢。
雖然土著加強了對入籍的控制及內部的防范,但移民仍有多種方式入籍。在清中葉前后,外來移民有兩種主要的入籍策略:其一是不同姓編為一戶(甲),也就是所謂的“多姓合戶”。在袁州府的部分地區,出現了一圖之內有六七姓甚至十四五姓的合戶者,這些合戶者,大都是已有戶籍的正戶為財而招進的新戶。這對移民和個別的土著來說,是雙贏的選擇,移民在入籍困難的情況下,擁有了戶籍,而那些招納移民入戶的土著則因移民的到來減輕了自己的賦稅負擔。但對整個土著族群來說,則并不是好事情。
其二是同姓認祖歸宗入戶。宗族是文化上的創造,袁州府的移民,便通過同姓聯宗的方式,與本地的同姓(若不同姓,亦可改變姓氏)宗族共同進行家族組織的建設,最終達到入籍的目的。
《移民、戶籍與宗族》給我們講述的清初以來移民在江西袁州府入籍、發展的故事,讓我們對移民在新居住地的生活會有切身的感受。其實,這樣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中也會經常碰到,如某個單位,當突然進入人數不算少而原有的資源相對沒增加的時候,這批新的員工可能就會遭到老員工“排斥”,與老員工之間可能也會產生“紛爭”。這樣的研究充滿了生命力,我們可以通過現實的生活去感知,它沒有采取讓枯燥的、分不出真假也摸不著頭腦的移民遷來遷去的數據展示在我們面前,而更多地讓我們看到、體會到移民生活的艱辛、困難的過程。
清代袁州府移民所面臨的入籍痛苦可能并不是清代移民都遭遇的問題。清代主要有三個移民輸入地,四川、臺灣及東北,地域社會的時空背景及國家的政策決定了移民在移入地的生活境遇、長時段的發展模式都有著極大的差別。以四川為例,經歷明末清初長時間的戰亂后,四川人口大量流失,清政府不得不采取“移民實川”的政策,對入川的楚、粵、閩、贛等外省移民實行極為優惠的政策,如給予土地、免稅甚至代為照看小孩。移民在四川并沒有遭遇入籍的難題(相反,地方官員還以招納移民的多少作為考成的重要方式)、也沒與土著發生爭搶學額的糾紛。所謂“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這些以移民為主要人口結構的地區,移民在社會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呢?這可能需要什么別的“袁州模式”來解答了。
(《移民、戶籍與宗族:清代至民國期間江西袁州府地區研究》,鄭銳達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九年版,2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