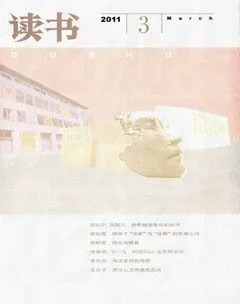楷
去年底,德國《時代周報》推出一期特刊,評介了德國五十位堪稱楷模的昔日人物。該報邀請了五十位作者推薦人選并進行熱烈討論,名單確定后,請他們分別為這五十位楷模撰寫文章,闡述遴選他們的理由。《周報》在前言中強調指出,這里不是在回顧各領域歷代大師和英杰,不是要再次指點和欽佩某個人的超凡業績,而是要推出一些人,他們的某些言語和行為,他們的個性和品格,他們的勇氣和技能,甚至于他們的某些秉性和弱點,對于今天和明天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換句話說,這里推出的一些人,不是要再現經典和偶像,而是要借鑒他們身上那些鮮活的思想和先鋒精神,也就是說,他們是今天缺少的人,是人們今天希望看到的人,是今天和明天所需要的人。
這五十人當中,有我們很熟悉的人物,比如歌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推選他的理由并非是他創作了蜚聲世界文壇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和《浮士德》,不是要張揚那為實現人生理想自強不息、不斷進取的浮士德精神,而是歌德那貫穿一生的對東方的興趣,他喜歡閱讀關于阿拉伯、波斯,以及關于印度和中國的游記。凡是有關上述地區和國家的文學譯述,他都先睹為快。他那如饑似渴關注東方的目光,他那對其他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不帶偏見的理解,他那對于德國文化和其他國家文化互相依賴、相輔相成的重要性的認識,體現了這位巨人的遠見卓識,使他成為提出“世界文學”這個觀點的第一人。他吸納了啟蒙運動借鑒東方思想資源的舉措,拒絕了否定東方的、狹隘的歐洲中心論。這位德國文學泰斗無疑是主張東、西方應積極交流,相互認識、學習和融合的先驅者之一。
《周報》在對歌德的評價方面視角的變化和重點的轉移凸顯冷戰結束,尤其是金融危機后,人們在對世界發展和人類進步的認識方面價值取向的變化,這一點更明顯地表現在對哲學家的推選上。五十位歷史人物中唯一的一位哲學家不是康德,也不是黑格爾,而是悲觀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理由是沒有任何人像他那樣,充分而又深刻地描繪過生存的苦難。他毫不留情地抨擊盲目的樂觀主義、貪得無厭的物質追求,以及極端泛濫的享樂主義。他大聲疾呼人生從根本上說毫無疑問就是痛苦。他發現了世界萬象之后那個盲動的、不可掌控的、無處不在的“意志”,指出如要使人生能夠忍受就要否定“意志”。為了解脫痛苦的人生,他將東方的超驗哲學引入西方,借鑒佛教思想建立一種憐憫的倫理,以內在的價值和精神享受來反對物質拜物教和消費主義。如果讓這位狂躁、粗野的人性批評家來面對當今世界的種種卑劣、愚蠢和荒誕的行為,那可有好戲看了,不信你就試試,在他面前講什么城市發展就要“大刀闊斧,無所畏懼”,就要“驚世蛻變,華麗轉身”。當今及未來世界需要的是徹底獨立的思想家,是不加任何雕琢的批評者。可惜今天再也難以找到這樣憤世嫉俗、怒不可遏的哲學家了。
推選名單中的科學家代表是“相對論”的創立者、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愛因斯坦。對今天而言,極具現實意義的不僅是他在理論上的貢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作為科學家所堅持的原則和他的人生道路。自大學時代起就全神貫注他感興趣的課題,從不浪費時間去為前程尋人脈,拉關系。有點閑暇則拉小提琴來放松和休息。他在自我設計方面可以說是個失敗者。畢業后自然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好在一個不起眼的專利單位謀一差事。在專業方面,不像當今許多青年人那樣,千方百計往高級科研單位和精英圈子里擠,他和他輔導的學生組成自嘲為“學術奧林匹克”的爭鳴小組。然而正是在這里,他的課題研究逐漸成熟,一九○五年震動物理學界的“相對論”問世。他不是那種精明地為自己打理前程的人,這反過來給了他創造性思考所需要的廣闊空間和自由精神。他是科學家但并不脫離社會,納粹的迫害、原子能帶來的驚駭、科學的責任和無奈,都不能讓他陷入歧途。他的政治態度的根基是他對人的熱愛。他是科學家但不自命不凡,擅長通俗而又風趣地闡釋深奧的科學理論。關于什么是“相對論”,他說:“與一個漂亮姑娘在一起待上一小時,好似才過了一分鐘;但在熱火爐上只待一分鐘,也像過了一小時,這就是相對論。”
《周報》推選出的演藝界人物首先是德國第一部有聲電影《藍天使》女主角的扮演者,她就是出生在柏林的瑪蕾娜·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