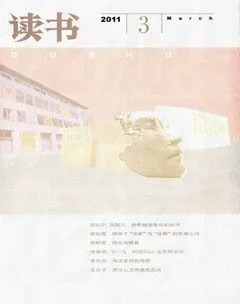俞平伯的憂郁
俞平伯在紅學(xué)上的貢獻(xiàn),自不必贅言。俞平伯的紅學(xué)研究開始于胡適一九二一年的考證論文發(fā)表之后,與胡適的文獻(xiàn)考證不同,他是文學(xué)考證派,關(guān)涉的是趣味。俞平伯在文獻(xiàn)上得到了顧頡剛的協(xié)助,所以他最早寫成的《紅樓夢辨》,似乎是與顧頡剛的討論,很多結(jié)論也在切磋之中。
俞平伯寫《紅樓夢辨》時(shí),接受了胡適的觀點(diǎn):后四十回是高鶚的偽托,即后四十回的真正作者是高鶚,高鶚和程偉元掩蓋了這個(gè)真相。俞平伯為了落實(shí)這個(gè)結(jié)論,決意從文本出發(fā)發(fā)現(xiàn)破綻,指出這是一個(gè)續(xù)貂的“狗尾”。高鶚欺瞞了讀者,他要指出高續(xù)“沒有價(jià)值”,這是他的出發(fā)點(diǎn)。
俞平伯的結(jié)論可以說是既定的,帶著主觀意圖研究后四十回,處處要滿足自己的先驗(yàn)看法,所以成竹在胸,應(yīng)該說比較容易寫成文章。
但是,情況并不樂觀。俞平伯是一個(gè)頑固堅(jiān)守自己文學(xué)趣味和文學(xué)感悟的人。本來想盡可能地說后四十回的壞話,“以八十回的內(nèi)容攻后四十回的虛妄”,但得出的結(jié)論卻令人匪夷所思。你看看:俞平伯說高鶚續(xù)得不好,不見得對,但又說高鶚是功多罪少的人,后四十回實(shí)在是《紅樓夢》的“護(hù)法天王”。高鶚的確是《紅樓夢》的“知音”,“未可厚非”。甚至指出“輕視高作”,就是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不知深淺”。這不是在創(chuàng)作上肯定了后四十回嗎?
從高續(xù)沒有價(jià)值,到高續(xù)不可替代;從高續(xù)是狗尾,到高續(xù)保住了悲劇結(jié)局;從高續(xù)是賬本到高續(xù)是精細(xì)的賬本;從高續(xù)擅出己意,到處處審慎有根據(jù);研究的目的是讓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不能兩立,無可調(diào)和,但結(jié)果是像顧頡剛所說的那樣,高鶚只是補(bǔ)苴完工了曹雪芹未竟的工作,高鶚保持住了悲劇,使《紅樓夢》超拔于其他小說之上的功績?nèi)珰w于高鶚。
上述文字滲透在《紅樓夢辨》的字里行間,如果你是一個(gè)精細(xì)的讀者,還會(huì)同意俞平伯——“高鶚完全失敗”——的出發(fā)點(diǎn)嗎?
俞平伯在通信的討論中指責(zé)顧頡剛充當(dāng)高鶚的辯護(hù)士,而自己呢,也是后四十回的辯護(hù)士。俞平伯明確地說:“不可輕易菲薄他(高鶚)。”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的文字是有斷裂的。當(dāng)他出離文本說明自己的意圖時(shí),他否定高鶚的態(tài)度異常明確肯定,他說高鶚“巧于作偽”;當(dāng)他深入文本感受、評價(jià)文字時(shí),他對高鶚又難掩贊頌之詞、處處辯護(hù),甚至說“萬萬少他不得”。也就是說,俞平伯在意圖和感悟上有矛盾,陷入了憂郁。
俞平伯要為后四十回找不是,否定后四十回,這是出發(fā)點(diǎn)。到發(fā)現(xiàn)后四十回還有不少可取之處,到認(rèn)真對待后四十回,細(xì)讀后四十回,這是轉(zhuǎn)變。再到和其他續(xù)書比較高度贊揚(yáng)后四十回,維護(hù)高鶚,認(rèn)為高鶚是曹雪芹的知音,這是結(jié)論。由此,我們可以明確地說,俞平伯不是“腰斬派”。那么,俞平伯臨終時(shí)為什么為“腰斬”而懺悔呢?其實(shí),很多新紅學(xué)的繼承人,只是得其皮毛棄其骨血,對高鶚變成了罵派,但把此看做是對俞平伯的追隨。
俞平伯是高鶚的罵派嗎?顯然不是,而那些罵高鶚的人,自以為繼承了胡適,特別是俞平伯的衣缽。你可以仔細(xì)讀讀,不管是胡適,還是俞平伯,他們都不是高鶚或后四十回的“罵派”。
后來,人們罵倒后四十回,以為肇始于俞平伯,自認(rèn)是俞平伯的繼承者,這使這位老者百口莫辯、不勝其辱。
還從文學(xué)感受上說事,俞平伯否定后四十回的言論,主要集中在:第一,寶玉變成了名教中人;第二,后四十回“文拙思俗”,單調(diào)得像賬單;第三,寫得過火,人物分寸掌握得不好。
寶玉參加科舉,就是皈依名教嗎?既然皈依名教,為何在光宗耀祖、闔府歡慶之時(shí),又不知所終出家了呢?這給了這個(gè)大家族多大的難堪!皈依名教,應(yīng)該不再和襲人、寶釵有爭論,但是即便是關(guān)于赤子之心,他們的爭論都不能停止,鬧得寶玉只能仰天長嘆、徒喚奈何。參加科舉,實(shí)在是寶玉完結(jié)俗緣的一個(gè)步驟,他根本沒有看重它,他應(yīng)付之是為了“不欠債”,一了百了。參加科舉的描寫在小說中沒有破壞賈寶玉性格的一致性和邏輯性。賬單說,就是說后四十回不像藝術(shù)文本,而像是挽結(jié)全篇的草草之作。后四十回的緊鑼密鼓,給人的印象是馬上結(jié)束小說完事,敷衍塞責(zé),而前八十回的鋪敘美景、敘事從容與詩情徜徉,至此戛然而止。對賬單說俞平伯有自我否定,這是一個(gè)精細(xì)的賬單,處處有出處,是對前八十回的呼應(yīng),高鶚未敢杜撰。第三個(gè)理由:分寸感。后四十回中賈母、薛寶釵、王熙鳳面目崢嶸以至猙獰,這是高鶚之罪。不過,細(xì)讀文本我們發(fā)現(xiàn)賈母對黛玉無情,前面的第五十七回就很無情:鬧得你死我活的寶黛之戀,賈母像不聽不聞的鴕鳥,任其拖延。這拖延,已經(jīng)關(guān)系到了寶玉、黛玉的生死,“風(fēng)刀霜?jiǎng)?yán)相逼”。這說明早在前八十回中,賈母,這個(gè)林黛玉在賈府中唯一的可靠之人也靠不住了。薛寶釵無情,前面寶釵就罵男人讀書不明理,越發(fā)可惡,不是罵寶玉嗎?前八十回里的寶釵也無情。薛寶釵和賈寶玉都罵讀書人,寶玉罵讀書人是充當(dāng)?shù)擉迹氣O罵讀書人是讀了書不去為官做宰。王熙鳳愛耍計(jì)謀,害死賈瑞、尤二姐使用了許多高智能、高難度的連環(huán)計(jì),再耍一次掉包計(jì)貽誤寶黛,對她來說不難,也順理成章。
后四十回過火,莫過于抄家過火。皇上抄家,這是可以隨便虛構(gòu)出來或者信手拈來的嗎?高鶚的家是否被抄過?高鶚有抄家之痛嗎?
抄家,可以說是自敘傳說證明作者是曹雪芹的一個(gè)鐵證,但是已有高鶚偽續(xù)的觀點(diǎn),新紅學(xué)對此如臨深淵,不敢踏進(jìn)雷池。原因全在于認(rèn)定后四十回是高鶚續(xù)補(bǔ)的。江南曹家接駕數(shù)次,榮耀無比,為新考證派津津樂道;江南曹家,也是被皇上抄家而倉皇北返的,緣何新考證派對后四十回這一段描寫噤若寒蟬。關(guān)于后四十回中抄家,最早的時(shí)候俞平伯也是否定的。寫《紅樓夢辨》時(shí)的俞平伯最早推測原文,賈府衰敗是漸漸枯干,是內(nèi)部殺起來的,而不是外部的抄家。但是,高鶚大膽,居然讓抄家完成大敗落、大悲劇,看來高鶚不懂前八十回,不懂探春的“內(nèi)部殺起”說的含義。俞平伯自信,根據(jù)他的藝術(shù)感悟和藝術(shù)分析,賈府是“漸漸枯干”。高鶚寫抄家,是“深求之誤”。高鶚寫抄家,是因?yàn)檫@樣在藝術(shù)上容易處理——“易寫”。
寫抄家,如果像高鶚那樣沒有抄家的親身經(jīng)歷和切膚之痛,卻能寫抄家,這需要怎樣的膽識?曹雪芹有抄家的經(jīng)歷,到了刻骨銘心的地步卻不寫抄家。如此對比,這不是在貶曹雪芹、贊高鶚嗎?
更重要的是,抄家片段寫的藝術(shù)成就極高。西平王要嚴(yán)格執(zhí)行皇上的抄家令,太監(jiān)趙堂官要擴(kuò)大抄家以渾水摸魚,而后來的“酸王”北靜王要袒護(hù)賈府,令太監(jiān)趙堂官叫苦不迭,真是一波三折、入木三分。賈府人罵錦衣兵是一伙強(qiáng)盜,和前八十回中王熙鳳罵宮里的人是外祟,同樣驚心動(dòng)魄。
皇上發(fā)旨,雖一次抄家,但旨令卻朝令夕改。這不可能是史實(shí),只可能是藝術(shù)虛構(gòu)。這樣的虛構(gòu),其意味耐人尋味:一是皇上“不著調(diào)”,說話隨便,亂出指示,弄得下人無所適從,也可以胡作非為。二是,假如這抄家是曹雪芹的原筆,則可以避免欲加之罪:影射。這與江南曹家被抄時(shí)的情形肯定大相徑庭:雍正抄曹家不需猶豫、異常果斷。這里的抄家,雷聲大雨點(diǎn)小。按說,在乾隆年間,文字獄盛行,曹雪芹膽敢以家事議論朝廷,真是膽大包天。
“我們兩人(顧頡剛)對于這一點(diǎn),實(shí)在是騎墻派:一面說原書不應(yīng)有抄家之事,一面又說高鶚補(bǔ)得不壞。”(《八十回后的〈紅樓夢〉》)豈止是“不壞”,而是“精心結(jié)撰”。林東海在《文林廿八宿·師友風(fēng)誼》中說:“俞平伯先生首先應(yīng)是個(gè)詩人,他以詩人的眼光和情愫去研討紅學(xué)和詞學(xué),而不是像長于邏輯思維的學(xué)者那樣去推理和判斷。”是的,從推理上看俞平伯前后矛盾,猶豫不決,而從詩人的眼光上看,他的憂郁里含有真趣,他不是腰斬派。
至于“蘭桂齊芳”,這是大河倒懸的一股細(xì)流,小歡喜掩不住大悲劇的整體氛圍,反而更襯托出綿綿悲音。曹雪芹善于悲中寫喜,猶如元春省親的喜中之悲,使悲愈悲,喜愈喜,悲喜對比,回環(huán)纏結(jié)。
上述三點(diǎn)反駁,并非針對俞平伯,而是順著俞平伯的文學(xué)感悟,將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之后的憂郁徹底化解:俞平伯在矛盾中有維護(hù)后四十回的文學(xué)立場。這是隱藏在《紅樓夢辨》中的真實(shí)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