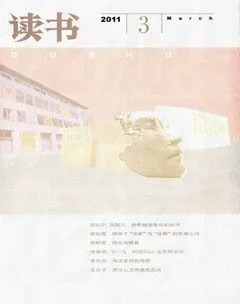童年之花
我出生的那年,動畫片《大鬧天宮》剛剛拍好。但是,我首次看到“齊天大圣”時,已是小學一年級——其間,孫悟空在中國黑漆漆的鄉村夜晚,打打鬧鬧已經七年。
我至今還難以形容,我第一次看到《大鬧天宮》時的驚異與震撼。孫悟空,這個上天入地的孩子,完全是一朵鮮艷的宇宙之花,在我內心的黑夜深處一次次綻放,并隨時會飛落在我的身旁。以至于很多年后,我一直堅信,在我去外婆家的路上,有一處碧綠的山間水庫,那就是孫悟空進入東海、去向龍王借兵器的入口。
童年是存在的深井。從此,我兒童時期保持的這個火光般的形象,與青苔的氣味,風雨黃昏的溫馨氣息,蚰蜒的緩慢爬行,銀河的光影,竹林里的紅月亮,緊緊糾纏在一起……隨之,是詩的萌芽。
前不久,在書店閑散翻書時,我意外被一套名為《動畫中國》的叢書吸引住——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經典動畫繪圖本,安徽少兒出版社出版。
《大鬧天宮》,《哪吒鬧海》,《黑貓警長》,《葫蘆兄弟》,這套叢書首批四卷,幾乎收錄了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五十多年來所有重要電影動畫,比如《寶蓮燈》、《三個和尚》、《小蝌蚪找媽媽》、《牧童》、《金色的海螺》、《好貓咪咪》、《天書奇譚》等等。
故事還是老故事,畫面還是老畫面。只不過為了保證清晰,畫面經過了細致打磨,重新描畫和上色。電影鏡頭變成了敘述的語言,富有樂感,朗朗上口。
在書架邊,我讀著讀著,許多內心深藏的熾熱形象,宛如童年遺失的火種,又轉瞬復萌……久而久之,以至于記憶與想象的邊界變得模糊,我幾乎分辨不出哪些是想象,哪些是回憶。
啊,國產動漫的經典時代,一個溫潤、端莊、美麗的時代,正漸行漸遠……
那是一個氣定神閑、經典輩出、緊貼民族藝術之根的時代。
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自一九五七年四月正式建廠以來,共攝制四百多部美術片,其中有四十八部先后在國內六十九次獲獎,有四十五部美術片在國際上七十三次獲獎。
其時,中國動畫片,獨一無二的民族元素與動畫影像的結合,構成了一道道神奇的風景,一度震驚了世界影壇。這些元素包括水墨畫、雕塑、建筑、服飾,乃至戲曲、民樂、剪紙、皮影、木偶、年畫等等。
這其中,最令人稱奇的是中國水墨動畫片——它們宛如一陣陣清新之風,吹在山水和田園,吹在果林、河流和農莊的上空。美輪美奐,恍如隔世。
水墨動畫,完完全全的中國風格,連片名都是精美的行楷書法,片尾年代都是“壬戌年”,并加蓋了雅致的印章……一只小雞,一片蘆葦,一帶遠山,一群游動的蝌蚪,每幀畫面都是一幅幅精美的水墨畫,墨色濃淡有致,線條婉轉,充滿動感和韻律。
今天,這些畫面,只依稀存在于齊白石、李可染、林風眠的畫冊中。
幾乎早年所有的動畫原畫,都在“文革”中悉數被毀,大部分原始膠片也都蕩然無存。以至于到二○一○年,為紀念張光宇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幅《大鬧天宮》設計稿,被做成藏書票,放在紀念筆記本的卷首。而在當時,《大鬧天宮》繪制了近七萬幅畫作。
其時,很多美術大師都參與動畫片創作。僅就視覺設計而言,這些大師的名字足以令人景仰——
水墨動畫片《小蝌蚪找媽媽》的原畫是齊白石,《牧笛》里的水牛形象則是李可染的親筆,《大鬧天宮》的美術設計是張光宇,《狐貍打獵人》的造型設計是韓美林,《鹿鈴》的美術設計是程十發,《哪吒鬧海》美術總設計是張仃,《鷸蚌相爭》借鑒了國畫大師林風眠的作品風格……
當時,動畫設計,多是藝術家一張一張用毛筆親手繪制。在今天,這個大師畫作寸紙寸金的年代,已是不可想象。更不可想象的是,如今人們日漸遠離自然,城里孩子連蝌蚪都不認識,鄉村也幾乎看不見野生的鯰魚、烏龜和螃蟹,你叫孩子們怎么親近《小蝌蚪找媽媽》?
“我們這一代人,您是再也揪不回去了。”難怪,前任上美廠副廠長張松林,在家里看兒孫們迷戀外國動畫時,感嘆不已。
“我們這一代人”,到底是怎樣的一代人呢?
萬籟鳴,《大鬧天宮》的導演之一,中國動畫的開山鼻祖,“萬氏兄弟”的長兄。萬氏四兄弟,曾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于一九二六年攝制了中國第一部動畫片《大鬧畫室》。一九四一年,他們又創作了亞洲第一部動畫長篇《鐵扇公主》。接拍《大鬧天宮》那一年,萬籟鳴已經六十歲。為了尋找片中諸多神仙的原型,他特意派人在寒冬臘月遠上北京,遍訪大大小小的廟宇。有時,為了設計一個動作,花甲之年的萬籟鳴往往會想得入神,會順手抄起一根哨棒,在廠院里和年輕人揮舞起來,以至有一次不慎掉入水池。“文革”期間,萬籟鳴因《大鬧天宮》蒙難,遭到隔離審查。一九九七年,九十八歲高齡的萬籟鳴先生安靜地離開人世。在老人的墓碑上沒有墓志銘,墓碑設計成一卷展開的電影膠片,一座云遮霧繞的花果山雕塑上,孫大圣手搭涼棚,寂然眺望。
張光宇,中國漫畫的奠基人,原中央美院、中央工藝美院教授。赴上海設計《大鬧天宮》時,也是年過六旬的老人。他給美猴王設計了著名的桃心臉。在其私淑弟子張仃看來,張光宇三十年代的漫畫就已深入千家萬戶,其社會影響之大,絕不亞于國畫界的齊白石、黃賓虹。張光宇晚年清貧,卻給后人留下了享用不盡的文化遺產。
張仃,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一九七八年出任《哪吒鬧海》的美術總設計。《哪吒鬧海》人物造型生動,色彩鮮艷,山水風景也極具中國神韻,對中國動漫影響深遠。二○一○年二月,張仃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歲。張仃的書案上,常年放著一個古裝兒童的石膏頭像,初看像敦煌石窟或麥積山寺廟里的雕塑,又非常富有現代感,這個石膏頭像正是哪吒。
這一代藝術家,深具文人風韻,交游廣泛,學養深厚,中西交融,多為通才。
上世紀二十年代,萬籟鳴就出任《良友》畫報的美編,他在水彩畫、水粉畫、油畫、鋼筆畫、剪紙、雕塑、木刻等方面都深有造詣。張光宇的裝飾藝術,在中國是一面旗幟,也是亞洲人的驕傲——其“內方外圓、“圓中寓方”、“方中寓圓”的造型觀念,是中國青銅器、玉器、金石書法的重要美學規律的傳承和發展,“張光宇風格”也成了“裝飾風格”的代名詞。張仃,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大美術家”、美術“立交橋”,他在漫畫、壁畫、郵票設計、年畫、宣傳畫、焦墨山水繪畫等方面都卓有建樹。張光宇、張仃還曾與梁思成一起,參加過國徽設計。張仃也是畢加索的中國知音,畢加索曾贈過他一本畫冊和一只和平鴿的繪畫。
二○一○年,也是特偉先生的離世之年——作為動畫電影“中國學派”創始人之一、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首任廠長,特偉的逝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特偉一生致力于探索中國動畫的民族風格,他是水墨動畫的初創者之一,其作品《驕傲的將軍》、《小蝌蚪找媽媽》、《牧笛》早已家喻戶曉。實際上,自一九八八年特偉的《山水情》之后,中國水墨動畫就終結了。難怪有觀眾感嘆:“特偉的離去,也許我只能在美式和日式兩種動畫片中度過余生了。”
五十多年,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數百部動畫片,的的確確是在“美”字上做文章,而這種美,又是徹徹底底的“中國之美”、“民族之光”——《南郭先生》,表現了漢代的藝術風格、格調古雅;《金色的海螺》,盡顯中國皮影戲、民間窗花的藝術特色;《聰明的鴨子》,乃折紙片,情趣盎然;《夾子救鹿》,具敦煌壁畫的古樸之風;剪紙片《草人》,彰顯中國工筆花鳥畫的形式……上述種種,全然土生土長,都與今天街頭巷尾流行的美、日動漫之風截然不同。
今天,當我們的孩子在迷戀日本動漫之時,他們是否意識到,日本動漫恰恰起源于中國,只是后來將其發揚光大了。
日本的宮崎駿,就是在看了《大鬧天宮》后,才萌發將動畫創造作為自己終身目標的想法。被稱為日本“漫畫之神”的手冢治蟲,抗戰期間,在上海看到了動畫片《鐵扇公主》后,大為贊嘆,決定放棄學醫,轉向動漫創作,并將動漫引入日本,創作了《鐵臂阿童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手冢治蟲來華訪問,唯一的要求就是拜見八十多歲的萬籟鳴。他坦承,鐵臂阿童木是受了“孫悟空”的啟發后創造的。見面那天,萬籟鳴畫下孫悟空,和手冢治蟲筆下的阿童木緊緊貼在一起。并且,手冢治蟲和宮崎駿,都對中國水墨動漫推崇備至。
今天,國家重視發展文化產業,大家都在談重振中國動漫。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因為各種復雜的原因,中國動畫已經迷失——其中,最明顯的,是失掉了本民族的風格與傳統。須知,一味的異國之風,一味的娛樂,一味的大資金投入、技術崇拜,終究離中國萬紫千紅的“花果山”越來越遠。
快餐和娛樂時代,現在很多中國孩子,已不能分辨出本民族的溫潤和雅致之美——事實上,國際上那些文化輸出最盛的國家,恰恰是最具民族意識的國家。
中國動漫如何發展,的確一言難盡。如何說故事,如何釋放想象力,如何探尋淵深的人性,如何培養宇宙情懷、世界情懷、人類問題意識,如何不把孩子當做低幼的說教對象,僅僅哄孩子玩……都是一個個問題。
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我們這個國度,有著數千年“寓教于樂”的傳統。最近,在閱讀《動畫中國》這套書后,我又重新回顧了一些中國經典動畫片。在看《鐵扇公主》時,有個細節使我警覺,那就是該片的開篇字幕——
“《西游記》,本為一部絕妙之童話。特以世多誤解,致被目為神怪小說。本片取材于是,實為培育兒童心理而作,故內容刪蕪存精,不涉神怪。僅以唐僧等四人路阻火焰山,以示人生路途之磨難,欲求經此磨難,則必須堅持信念,大眾一心,方能獲得此撲滅兇焰之芭蕉扇。”
由這個字幕可以看出,很多中國動畫片自一開始,就在“說教”中定位,把孩子對象化了。
實際上,適度的“怪力亂神”,恰恰是瑰麗想象、復雜敘事的保證——比如孫悟空,不正是因為他的怪異、勇力、叛亂、通神滅鬼之事,才使他威風凜凜、神采奕奕的嗎?
中國,有著浩如煙海的神話故事,民間傳說,文學名著,歷史傳奇,志怪小說,資源得天獨厚,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量體裁衣,面向未來,再創精品。
所謂精品,第一步還得重新銜接傳統,使好的技術服務于好的視覺、好的聲音,以彰顯一個民族生機勃勃的精神力量,使抽象的國家變得有形有色、韻味無窮。誠如茅盾當年給《小蝌蚪找媽媽》的題詞:“白石世所珍,俊逸復清新……何期影壇彥,創造驚鬼神。”
卓越的夢想者,正是善于呼吸過去的人。而童年之夢,童年之憶,在我們的名字周圍,堆積起我們所有的存在,以確保我們生命的連續性。
——期望中國孩子,在未來更好的動漫作品里,進入與世界合為一體的夢想,宇宙性的夢想……以便滄桑之年,還能道出靈魂的秘密住址,展開難以估量的記憶。
而此刻,《動畫中國》這套書,因其獨立的時代品質,因其對傳承民族記憶的責任,使我們重溫逝去時光的幽深魅力。我謹懷感激之念,歡呼這看似夕拾朝花,實則是嶄新的、鮮艷的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