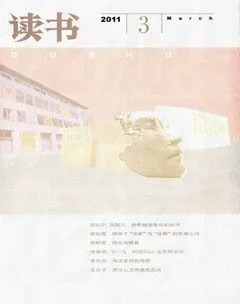自然生態下的知識人
一
幾年前,在網上讀過一篇旅行者的文章,他描寫了為了“開發”,草原自然生態被破壞的情況,以及作者對這種狀態的隱憂。文章中說,開車去內蒙古東部,走了幾個盟,途經二十多個旗。沿途所見,真正能保留一些原來生態面貌的,只剩內蒙古和蒙古國接壤的國境線一帶。的確,在那里才能體會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生態。用“體會”這個詞是準確的。腳踏上那兒的草地,就會感到踩在厚厚的一堆活的物質上。要是仔細觀察你踩下的那個腳印,在那么小的面積上,我感覺就能聚集著上百種植物和昆蟲。那些豐富的物種糾纏在一起,生長得又密又厚,幾乎就沒有重樣的。有些蕨類、灌木什么的,要上百年時間才能形成它們的根系。什么叫生物多樣化?這就是最典型的狀態。那都是在幾百年的自然狀態中生長起來的。看著那樣的環境,你真是會切身地感受到對它的破壞是一種什么樣的罪孽。可是現在,能保持那種生態環境的僅僅是沿著國境線的窄窄一條。稍微往內地走一點,就看到大片大片的草原被開墾成耕地,種上了莊稼。草原的面貌立刻變成了完全不同的樣子:上面覆蓋的植物變成了單一物種,或是麥子,或是油菜,看上去顯得整齊、單純,毛茸茸一片,顏色全是一樣的。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莊稼長得特別好。但草原上千年時間里形成的腐殖質層只有一尺多厚。開墾者先是用火一燒,把需要百年才能長成的植被燒得干干凈凈,然后把腐殖質犁開。那種土壤肥沃得只需要撒種,別的什么都不用管,秋天肯定大豐收。然而甜頭也就是三年,三年后就是苦果。一尺厚的腐殖質層下面就是沙子。破壞了原來的植被和根系,失去了植被的固定,再加上犁來翻去,表面那層土松得不得了,草原上的大風一吹,土就吹跑了。沙子就暴露出來,那就是通常所說的沙化。
大自然因為人類的急功近利造成了生態失衡,受到自然的懲罰,欲益反損。社會、人群有沒有“生態”問題,有沒有因為生態失衡而導致負面社會現象叢生的?我以為也有。例如九百多年前,蘇東坡寫給“蘇門六君子”張耒的一封信中,評論當時的文風、士風時說: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蘇氏說的“王氏”就是王安石。當時安石為相,不僅在政治、經濟的制度上推行一套新法,而且他又借宰相之力,推行自己的學術主張,變私學為官學。或說把自己的學術思想變成國家的意識形態,用以統一士大夫思想、使人同于己。他還借助科舉考試的力量,使之成為取士的標準,文人士大夫趨之若鶩,這種做法破壞了北宋建立以來的文化積累,正像草原的“腐殖質”被犁庭掃穴一樣。因此LtFlpC+Z8qnQYy+bNkpb2+GELgw12G1TGnQwGevHGOA=,盡管王安石自己是特立獨行的人物、其學術詩文也各有成就,但當他用自己作為原型復制人才時,破壞了原有的自然的士大夫群的生態,姹紫嫣紅、百花盛開的局面不見了,得到只是一片黃茅白葦。
《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雖然寫的是他們的生活學術經歷,但從中可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知識人群生態的演變過程,而且非常生動地再現了在這個變化中知識人的種種情態。
二十世紀初,隨著清王朝的解體,幾屆民國政府都屬于弱勢政府,對于知識人很少有控制力,再加上歐美思想的傳入,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知識人自我意識覺醒及其與社會的互動,逐漸形成了知識人群落的自然生態系統。趙儷生夫婦及他們書中所寫到的知識人群大多是在這樣一個系統里長成的。由于這樣的自然的生態系統適合知識人自我價值的實現,于是形成了一個被外人所艷稱的“天才成群地來”的時代。
高昭一用三個“主義”概括趙儷生,“自由主義”、“人文主義”、“理想主義”。其實這三點是那個時代過來的許多知識人的底色,特別是活躍在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知識人。在這種底色上,每個人由于出身、經歷和知識結構的不同,各有特色,用褒義詞來形容是豐富多樣,用貶義詞形容則是光怪陸離。但這些往往都是自自然然的,既非設計,也非打造。
今人很難理解的是知識人在上世紀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空前未有的貢獻,他們在教育、出版、新聞等領域所達到的高度直至今日仍然很難企及。我們還經常感慨,為什么西南聯大在那么艱苦、簡陋的條件下培養那么多世界級科學家、學者?自然生態中滋長出來物種,往往優于人們有意識、有計劃培植出來的。正如俗話所說“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們驚嘆大自然的偉力時,往往忽略了社會變化勢態的自然力。
二
趙儷生是位左派學者,一生信仰馬克思主義(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史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遠較其他領域為多,然而,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六十年代以后幾乎全部被打倒,使得“文革”當中毛主席多次說到他要“保護幾個史學家”,但連翦伯贊這樣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自殺了),這個本來符合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作為史學家,他所關注的領域也非遠離主流,例如五六十年代史學研究界最熱衷的“五朵金花”(指當時史學研究討論最多的五個專題——中國古代歷史分期、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土地制度、民族關系與民族融合、中國古代的資本主義萌芽)中趙儷生涉獵其中的就有三四朵,如中國土地制度、歷史分期、農民武裝斗爭、資本主義萌芽等。當時史學界有許多專家對這種討論毫無興趣,注重史料的考訂與研究(一九五八年被斥為“厚古薄今”)。與這些學者相比,趙儷生應該被主管史學界的領導看做“紅教授”、“紅專家”了。其實,遠非如此,他不是趕時髦的人,更不會趨奉,其研究成果很難與主流所認可的結論一一對應。因此他的研究領域屬于主流,但結論往往大悖主流。如講歷史分期不同意主流的戰國封建論,堅持魏晉封建論;講農民戰爭不突出農民與地主的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唯一動力,而承認統治階級在許多激烈的農民戰爭之后還有讓步政策;在歷史分期上強調亞細亞生產方式,明里暗里挑戰《聯共黨史》鼓吹的“五種生產方式”說。當然,這倒不是他有意背時,而是他堅持獨立思考研究的結果。這些雖說都是學術問題,但含有極強的政治性(那時的政治運動往往在史學領域發端),因此一九五七年被劃為“極右”,差點命喪夾邊溝,就不是偶然的了。
趙儷生不僅在學術上“另類”,在為人行事上,更是特立獨行。他在抗日戰爭時就參加了革命,但卻秉持獨立精神,不肯參加任何組織,這在今人看來非常奇特,可是在當時知識人看來卻是極其正常的。因此,他在華北大學直接挑戰副校長成仿吾,批評他不該以征服的勝利者自居,羞辱其他知識人;在科學院不同意郭沫若對于副手摧辱,而且訴諸媒體,也就不奇怪了,這正是他“自由主義”人格的一貫表現。趙一生持此態度而不變,被妻子稱為“天生的自由主義”。想一想,在那個以知識分子為整肅對象的時期,這樣的性格還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嗎?無怪直到了新時期,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時候,他仍然被有些領導視為“誰也掌握不住”的人,連一些榮譽職務也不肯給他,就是怕他把這些職務當做真正的權力去使用,讓大家下不了臺。
不過無論從哪個角度說趙儷生都是一個強者,不管遇到什么樣的急風暴雨,他都能挺住。在學術上,他開創了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并在中國土地制度史及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古代社會方面有杰出貢獻。不過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史學教師,有的老先生說,解放前史學界講課最好的是錢穆,解放后是趙儷生。他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培養學生上,被學生譽為“五絕教授”(一絕是板書,二絕是文獻,三絕是外語,四絕是理論,五絕是博而通),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其中高才捷足者,比比皆是。
不過趙儷生所選擇的道路在習慣于組織化秩序的時代還是充滿艱辛的,但他是“雖九死而未悔”的。在他晚年見到當年一塊打游擊的老戰友時,已經成為省部級高干的老戰友語重心長地勸他反思自己的選擇。他寫道:
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我和高昭一連續兩次到昆明開會。當年游擊隊的組織部長孫雨亭同志剛從省委副書記的任上退下來,擔任省人大副主任。他在翠湖飯店盛宴招待我夫妻,記得席間有麂子肉、鹿筋、猴頭等,最后上來“過橋米線”。酒過三巡,孫對我說:“老趙啊,當年有個事要跟你說清楚。那次晉南干部總結會之后,調整班子,你已經是公認的宣傳部長啦,可是到頭來還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為什么嗎?現在可以說破了,就是因為老朱是黨員,你不是。論工作,無論編報、講政治課,老朱都遠遠不如你,可他是黨員啊。我講這些是叫你打破平生不參加黨的戒律。你不入黨,黨不吃虧,你吃虧呀。”我回答說:“老孫,你說錯了。不是我吃虧,是黨吃虧。這類事實,替入黨做官論打造下堅實的基礎,這跟不正之風和黨干部腐化有密切的關系。”
這段對話很值得深思,它反映了相信組織化秩序還是堅持自然秩序不同的思考。
三
趙儷生筆下的知識人雖然都是學者,大多也是以文史研究教學為業,但他們面目各異,各有真性情。與強者趙儷生相對的是另一位大學者童書業,過去讀他的《春秋左傳研究》,佩服其思考、研究之細密。上世紀九十年代朋友以《童書業美術論集》見贈,讀了之后更是驚嘆其學問之博雅。特別是其論畫部分,如《中國美術史札記》、《繪畫史論集》、《唐宋繪畫談叢》、《談畫》等比我曾讀的《中國美術史》還好看,論述生動親切,看來與童博學、又精于此道有關。讀其書想知其為人,不過那時僅從其女童教英教授《美術論集》的“前言”對童先生有個極簡單的了解。得知如此大才,僅僅享壽六十,死于“文革”當中,令人唏噓。待讀了趙儷生回憶錄中的《一個絕頂聰明但被扭曲的人》,對童書業才有了個真實而全面的認識。趙先生是從童的“怕”寫起,他“怕失業、怕雷電、怕空襲、怕傳染病、怕癌、怕運動、怕地震、怕蔣記反攻大陸”。這“運動”指政治運動。每次政治運動一來,頭天開過吹風會,第二天便面如死灰。趙回憶更多的是童書業被外力“扭曲”的一面,因為生動而被讀者記住了,屢屢見諸征引。其實書中也記錄了童書業“本我”的一面。如他聰慧、記憶力之佳,更是令人震驚。
童的本我就是以學業為生命。幾十年來,在學術單位工作,也看到過許許多多不同類型的學者,思想境界高的,把學問看做個事業,努力為這個事業添磚加瓦;境界一般的就是以此為職業;更下者就是混飯吃。而像童書業把學問看做自己的生命,看做安身立命的基礎、舍此而無他的,不能說沒有,真是少之又少。趙寫道:
童書業最愛談學問。談到高興時眉飛色舞,手舞足蹈。不管聽的人愛聽還是不愛聽,他一直談下去,談到午夜以后。他最怕黑夜中出事,但談起學問來就什么都不怕了,因而造成過小事故,有時迷路,有時被警察收容。因此很多人討厭他談學問,徑直攆他走。我夫妻能有耐心聽他談,所以他認為我們二人是他終身好友,一到周末或星期天,就一定到家里來。……他談的,都是治學中新收獲的萌芽,或者說,是一些論文未成形前的毛坯。并且在這里又須加一筆,童有時很傻,但有時又很精。例如,他跟一個人談過某個他自己的“精義”,過些時候這“精義”不知不覺被人攝入該人的論文中去了。從此,他就不再到這家去談學問;我們問起來,他只把眼睛彎成蛾眉那樣瞇瞇地笑著,不出一語。再者,他總有一種偏執,認為我夫妻二人接近革命早一步,接觸馬列早一步,而他晚一步,從而對我們產生某種莫名其妙的信賴,仿佛我們聽后沒有認為大謬的論點,就是可以站住腳了。
這就是童書業,以學問為生命,他的生活的動力、樂趣都在于學問。他不僅熱情地與別人討論新知,讓別人分享自己新發現,即使自己發現被別人竊取,仍然保持著學者風度(不像現在有些學者偶有新發現,仿佛獨得之秘,那是深秘不宣的),而且積極地向他人學習自己不懂的東西。這也是現代知識人的圈子中不多見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正處在社會大變革時期,傳統的做學問的方法受到置疑,童書業便開始學習馬列主義。據說當時在解放前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當中,童書業是最先運用馬列主義方法、術語寫專業文章的,使許多熟悉他的學者感到詫異。當然,除了學問與書畫,這些在當年世人看來都是“封資修”,因而童書業不僅是一無所能,而且有害。在那個不要文化、鄙視文化的時代,童書業悲慘地被迫害而死是“又替人民節約了二百多元人民幣”。如果全體國人都這樣看,中國豈不又回到蠻荒時代。
四
趙儷生描寫了知識人圈子的眾生相,特別關注在社會變革中他們的命運。當然,社會變了,處在這個社會中的一切人都應該變,以適應新社會的需求,然而,由于那個時代的人們,一是求變太急,二是過多地運用“群眾運動”方式來推動這個變化,三是對于知識人整體思想意識估計的錯誤。于是,過早、過急地摧毀了知識人群落原有的生態,又未能及時地建立起新的社會生態,這樣不僅造成了許多知識人的悲劇,而且大大影響了新的知識人群體建設,從而造成知識人斷層與整體素質的下降。
上述這些做法都與向蘇聯學習有關。蘇聯作家阿·托爾斯泰在《苦難的歷程》中說到知識分子的改造,用“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堿水里煮三次”以形容,中國知識人道路艱辛有過于此。在如此激烈的折騰中只有特別強悍、或特別具有韌性者才能支持下來,如趙儷生,幾次面臨兇險,他都沖過來、或熬過來了。有時我突發奇想,如果賈寶玉(以賈寶玉的才學也應該算個知識人了)要活在知識分子改造的時代會發生些什么?實際上童書業就有點像賈寶玉,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是前清進士,曾在安徽省做道臺,署理臬臺(掌管一省的司法)。童出生恰逢這個家庭的鼎盛之時,家里有花木園林之勝,還收藏了許多金石書畫,甚至要請人替這些藏品編“庋藏目錄”。童是這個家中的嫡長子,自生下來就受到祖父母的寵愛,備受呵護。到學齡時,怕孩子受氣,不肯送外面上洋學堂,而是在家里請先生教授傳統知識。因此直到二十余歲的時候,童基本上沒有在正規學校中上過學,這樣他不僅沒有學歷,而且使他沒有與社會接觸的經驗,沒有社會閱歷,不通人情世故。學問很大,能在大學任教,能從事研究,但為人做事,卻像個小孩子,顯得十分幼稚。了解了這些背景,我們對趙儷生筆下的童書業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趙儷生說童書業最怕政治運動,回想一下在那個時代除了天生的棍子手、或劊子手誰不怕運動?連侯寶林那樣練達人情世故的藝人在臨終前接待記者時都說,他一生“一怕打仗,二怕運動”。更不用說幼稚而有些強迫癥的童書業了。在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之初就被內定為“一夜之間殺了一千個共產黨員”的歷史反革命,童書業檢查交代了九次,都沒有通過。后來他寫了《請求書》,承認自己是反革命,請求政府把他抓起來。他還寫了數萬字的《童書業供狀》,交代說:“是有一個受美國情報局指揮的,隱藏在大陸很久、很深的,以研究歷史、地理、繪制地圖為幌子的反革命集團,其最高首腦是顧頡剛,各地分設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楊寬,山東代理人是王仲犖,東北代理人是林志純,底下一句還有‘我和趙儷生也是其中的成員’。”史學界的著名學者大多網絡其中。如果當時真照此處理,真是史學界一厄。不過,那次“肅反”還比較理性,我從其女童教英《從煉獄中升華——我的父親童書業》中看到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中共山東大學委員會肅反領導小組”的“關于童書業教授問題的結論”中否定了那些荒唐的揭發和自供。“文革”是一場浩劫,各界損失都很大,史學界尤巨,史學界的許多名宿從肉體到精神都受到極大侮辱,死于運動者也不少,童書業也在其中。
因為求變太急,深信強力、行政力量、群眾運動的聲勢可以改變一切,結果對于知識分子的改造不僅僅傷害了許多知識人,而且毀壞了知識人群落原有的自然生態。
(《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第一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