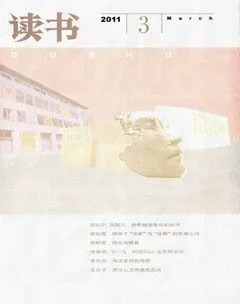命運多舛的國歌 德國文化史隨筆
二○一○年南非足球世界杯已落幕。早在世界杯開幕前,德國隊就已經曝出新聞,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德國隊入選二十三人的大名單中,有十一名球員有移民背景;而其中十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賽前奏國歌時將不會開口唱德國國歌。國家隊隊員是否應該唱國歌?德國“足球皇帝”貝肯鮑爾明確地說:“過去我當教練時,賽前唱國歌是義務。我把國歌歌詞分發下去;那個時候對于運動員來說,剛開始的確不大習慣。但是哨子響之前唱國歌,會增強自我意識和共同體的感覺。”而現任德國隊教練勒夫則說:“如果更多的人一起唱國歌,我們會很高興。但是我們不會強迫任何人去唱國歌。”這個事件有兩個看點:第一,身為國家隊的隊員,代表國家隊比賽時公開表示不唱國歌,這本已是蹊蹺,大概也稱得上“舉世無雙”;第二,這個事件在德國雖然也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但總的說來波瀾不驚,大家見怪不怪,這就更為耐人尋味。
二○○六年,《圖片報》發出倡議,號召讀者參與創作國歌:“為了響應聯邦副總統沃爾夫岡·蒂爾澤(社民黨籍)為德國國歌創作更多歌詞的號召,《圖片報》的讀者們展開了創作大賽。”一時間,許多人躍躍欲試,數以百計的人們參與其中,《圖片報》“精選”了其中的十余首刊出,以饗讀者。這些讀者創作的歌詞中,有不少洋溢著愛國情懷,但也不乏嬉笑玩耍的搞笑之作,如“足球世界杯版”、“餐飲版”的德國國歌。
公開把國歌拿來調侃與搞笑,而在社會上并未受到猛烈抨擊,更未受到法律的制裁,這種情況在德國并不鮮見。早在一九八六年,曾經有一位藝術家為德國國歌重新填詞,發表在一份德國雜志上。這首“一九八六年版德意志之歌”是一篇諷刺作品,作者在歌詞中極盡笑罵之能事,對德國國歌進行調侃,激怒了許多人,事情一直鬧到德國憲法法院上。德國憲法法院做出的判決卻讓人大跌眼鏡,判決認為,對國歌進行戲仿是可以的,并無不當之處,把黑、紅、金三色旗比做小便時的水流也是合法的。憲法法院援引德國的藝術保護法,認為這首歌詞屬藝術作品,其中的戲仿是一種藝術手法,故不在受法律懲罰之列。
國歌是民族國家的產物。作為文化的一個符碼,國歌表達和傳達民眾的是民眾對于國家和民族的感情和認同。一七四三年,英國人亨利·加雷創作了一首國王頌歌《上帝保佑國王》,后成為英國國歌,也成為國歌的一種范式。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中,《馬賽曲》應運而生,這種新型國歌承載著意識形態內容,又為國歌創作樹立了另一種類型。對于德意志地區而言,這兩種模式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普魯士王國的國歌《以勝利祝福你!》甚至采用了英國國歌《上帝保佑國王》的旋律,填上了歌頌普魯士國王的歌詞而成。而到了十九世紀,德國的民主和統一運動風起云涌,《馬賽曲》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模式大受爭取民主自由和民族國家的各種政治力量的歡迎。在德國國歌的產生過程中,各種各樣的嘗試層出不窮,形成了一種競爭態勢。有的候選國歌曾經一枝獨秀,獨領風騷;但是曾幾何時便風光不再,成了明日黃花,只有詩人霍夫曼·封·法勒斯雷本(一七九八 —— 一八七四)于一八四一年創作的《德國人之歌》歷經幾起幾落之后獨領風騷,最后終于修成正果,被定為國歌。
法勒斯雷本是一個自由派人士,支持統一運動,要求在德國實行民主制。一八四一年,他在當時處于英國治下的赫爾果蘭島上寫下了這首著名的《德國人之歌》,想通過這首詩表達他的德國情結,希望德國實現民族統一和民主政治這兩個當時對于德意志最為緊迫和重要的任務。當時出版商坎佩也在赫爾果蘭島上;在客棧,他聽到法勒斯雷本朗誦這首詩,興奮不已,當即以四個金路易買下了這首詩并在漢堡刊印發行。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期間,《德國人之歌》迅速走紅,被廣為傳唱,儼然成為沒有民族國家的德國人的國歌。但是隨著革命的失敗和君主們的卷土重來,這首歌便被打入冷宮,不見天日。
一八七一年,第二帝國成立,德國人終于有了一個民族國家,全體德國人擁有了共同的“祖國”,但是這首歌也沒有看到光明。俾斯麥不遺余力地強調德國沒有擴張意圖,以安撫四鄰,保持歐洲的均勢。他擔心《德國人之歌》飽含的民族主義情緒會給外國,特別是列強以恐懼。此外,俾斯麥是民主主義的死敵,法勒斯雷本的民主主義思想自然得不到他的青睞。直到一八八八年,德皇威廉二世登基,新皇帝改弦更張,《德國人之歌》的命運才峰回路轉。一九一二年,德國與西方的沖突加劇,《德國人之歌》也步步走紅,一躍成為當時德國人演唱頻率最高的歌曲之一。而且這首歌的名稱也產生微妙的變化,從《德國人之歌》(Das Lied der Deutschen)演變成《德意志之歌》(Das Deutschlandlied),在后來的歷史記述和人們的說法中,這兩個名稱都經常被采用。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人之歌》也隨之經歷了一個高潮。戰爭開始后,德國士兵高唱著“德意志高于一切”投入戰斗,發起沖鋒,《德意志之歌》儼然成為激勵德國士兵的精神利器,其他的愛國歌曲難以與之爭鋒。但是接下來,這首歌幾起幾落,引起爭議無數。
一九一九年,戰敗的德國百廢待興,而新生的魏瑪共和國則命運不濟,處在各種政治力量和各種意識形態的交叉火力網中心,亟須找到能夠凝聚全民族的精神力量。除了黑、紅、金三色旗之外,《德意志之歌》就成了為數不多的精神資源之一。其時,德國內部的政治斗爭不斷激化,保守主義陣營和軍隊等右翼勢力與左派的沖突不斷。為了不讓民族傳統為右派獨占,也為了從《德意志之歌》里開發愛國主義資源以維系國家和民族的共識,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一九二二年,社會民主黨籍總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克服重重阻力,力排眾議,勉強把《德國人之歌》定為國歌。但是《德國人之歌》的“扶正”并不意味著這首歌從此便一帆風順,高枕無憂,艾伯特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來自本黨的阻力。社會民主黨及左翼政治力量認為,《德國人之歌》所表達的是市民—資產階級陣營的理想;如果把《德意志之歌》定為國歌,有放棄自己的政治立場、向右派投降之嫌。所以,盡管在艾伯特的努力斡旋之下《德意志之歌》被定為國歌,但是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對此始終持抵觸態度。
一九三三年,納粹上臺。《德意志之歌》所經歷過的最大的麻煩,正是來自第三帝國時期它所受到的“禮遇”。第三帝國開始時,希特勒給予這首歌以高度評價,因此這首歌在納粹時代受到禮贊,作為國歌繼續被沿用下來。此前,民族社會主義分子、希特勒的黨衛軍的一個小頭目赫爾斯特·維塞爾創作的一首納粹戰歌《戰旗高舉》在納粹德國也頗為流行。于是納粹玩了一次移花接木、暗度陳倉的把戲:把《德意志之歌》的第一段與《戰旗高舉》拼裝成一首歌,并立為國歌,留下重重后患。
“二戰”結束后,鑒于《德意志之歌》與納粹的淵源,占領軍當局發布命令,宣布《德意志之歌》為禁歌。但是,這時的德意志民族背負著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整個民族都被視為惡人,所以急于證明德國亦有好的傳統;于是從傳統中尋找精神支柱,成了當務之急。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后,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德國也需要一首國歌,因此國歌的問題顯得迫在眉睫。但是德國上下對于《德意志之歌》的態度卻大相徑庭。有鑒于此,一九四九年五月頒布的德國《基本法》對這個棘手的問題采取了回避的方法,未對國歌做出明確的規定。總理阿登納及其基督教民主聯盟極力主張恢復《德意志之歌》的國歌身份,這一主張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而社會民主黨籍的總統臺奧多爾·豪斯則持反對態度,總理與總統之間展開了一場“國歌之爭”。政治家們各執一詞、相持不下,國歌的問題一拖再拖,但是現實的需要已經使國歌的問題變得日益緊迫。
幾場國際體育賽事上,聯邦德國因為沒有國歌而大失顏面。一九四九年在科隆舉行的一場國際自行車比賽上,樂隊先是奏起了比利時國歌,接下來奏起了瑞士國歌,輪到奏德國國歌時,樂隊因為無歌可奏,只好奏了一首一九四七年科隆狂歡節上的流行歌曲《我們生長在三個占領區》。善良的比利時運動員不知就里,以為這就是德國國歌,于是在奏響這支狂歡節流行歌曲時立正敬禮,令德國人哭笑不得。而在這之前,在柏林舉行的一次體育賽事上,樂隊指揮因為無國歌可奏,只好演奏了一首流行歌曲《慕尼黑有一家宮廷釀酒坊》的旋律。一九五○年五月,德國隊和瑞典隊在斯德哥爾摩舉行了一場足球比賽,瑞典舉辦方播放了在德國尚存爭議的《德意志之歌》,輿論為之嘩然。但事后瑞典方面對外宣稱,這是一個事故,是組織者選錯了唱片。凡此種種,令本就痛苦不堪的德國人大失顏面。又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在國際體育賽事或其他公共活動上,組織者也播放過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的《歡樂頌》,以替代缺席的國歌。總理阿登納本人出訪美國時,在芝加哥也經歷過類似的尷尬場面。因為新生的聯邦德國還沒有國歌,芝加哥的接待方只好播放了一首流行歌曲《海德維茨卡船長》以充數。
這些事件對政治家們施加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阿登納則借此機會為《德意志之歌》正名。他對占領軍當局說:“通過這些事件,聯邦德國在德國人自己的眼中也變得有些可笑。”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豪斯與阿登納多次通過信件展開了一場國歌之戰,最終阿登納勝出,豪斯被迫做出妥協,同意《德意志之歌》的二次“扶正”。豪斯和阿登納的來往信件公布于聯邦德國政府的公告上,但是卻沒有在國家的法律文件里公布,使得國歌的地位頗為尷尬,“妾身未明”給德國國歌后來的命運又平添了幾多麻煩,也引起了無數爭議。
《德意志之歌》立為國歌后,麻煩并未就此終結,“國歌之爭”之后又開始了歌詞的“段落之爭”。這就是:三段歌詞是否全部采用,抑或只采用其中的一段?三段還是一段,這是個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其實不是新問題。早在一九二二年,艾伯特力排眾議確立《德意志之歌》為國歌時,就已建議只唱歌詞的第三段。但是直到一九四五年,實際演唱的只是國歌的第一段;而且第三帝國期間,第二段和第三段實際上被“閑置”,尤其是第三段受到納粹政府的冷遇。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總統豪斯就對此發表過意見,認可第三段的內容,反對沿用第一段和第二段。他認為,因為第一段里列舉的地名馬斯河、梅默爾河、埃施河和貝爾特湖,均不在聯邦德國境內;如果再唱第一段,勢必給人以復國主義的印象。就連力主恢復《德意志之歌》的阿登納,在向占領軍當局陳述恢復《德意志之歌》的理由時,也認為第一段“畢竟出自一百多年前”,所以“如此陳舊,以致每個明智的人決計不會唱”;第二段則“有些愚蠢”;只有第三段的內容包含了“現在還適用的真理”,而且在納粹時期第三段實際上是被禁止的,這就給第三段之被采用提供了合法性,所以新德國的國歌只采用《德意志之歌》的第三段,云云。德國政府的表態也是含糊其辭、語焉不詳。德國政府附在豪斯—阿登納通信集的說明里說道:一方面,德國政府認為德國國歌是完整的《德意志之歌》,另一方面,又認為出于國家政治的考量,在代表國家的活動上只應演唱第三段。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間,國歌的問題在德國社會又起波瀾,法學家們對《德意志之歌》作為國歌是否合法的問題展開論戰。有些法學家提出質疑,認為一九五二年豪斯和阿登納的通信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德國現在的國歌不合法。德國社會也對法學家們的爭論做出反應。 一九八六年夏天,巴登-符騰堡州文化部長格哈德·邁耶爾-福菲爾德公開發表言論,認為在學校里教授國歌時,應當三段都教授。他說:“無可爭議的是,根據臺奧多爾·豪斯與康拉德·阿登納的通信集所確定的,國歌應當由三段歌詞組成。因此我們經常說,教授第一和第二段歌詞,屬于教師的教學內容范圍。當然,在講授國歌時,同時介紹其歷史背景,而且是以兒童聽得懂的方式來講解,說明為什么國事活動時不唱第一和第二段,也是教師的職責。”一石激起千層浪,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激烈的爭議,德國的左翼與右翼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展開激烈論戰。在左派占優勢的德國媒體中,邁耶爾-福菲爾德的言論招致猛烈的抨擊,巴-符州議會里,左派政黨甚至要求把邁耶爾-福菲爾德趕出州議會。一九八九年春天,德國黑森州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
一九九○年,民主德國加入聯邦德國,德國的統一大業終于完成。但是德國國歌的問題又起爭端:代表新德國的國歌究竟應當是什么?是《德意志之歌》,還是布萊希特的《兒童頌歌》?是《德意志之歌》的第三段,還是所有三段?然而最后這些討論未能產生明確的結果,德國國歌仍舊是法勒斯雷本的《德國人之歌》,段落之爭并未結束。時至今日,盡管多數人接受了《德意志之歌》,但是分歧繼續存在。德國國歌在德國的處境也仍然有些尷尬。
《德意志之歌》最終一枝獨秀、修成正果,當歸功于法勒斯雷本的政治敏感度和文學創作才能。除了配曲和歌詞的藝術性之外,這首歌的價值更在于其內容,在于它表達了時代的要求,以及德國人的民族訴求。這首歌的第三段里,“統一、法權和自由”的政治三位一體,濃縮了當時德國民主運動的全部理想。“統一”的意義自不必說,“自由”的意義也不言自明,而“法權”則表明法治國家的重要性,而且極其符合德國人對于秩序的崇拜。無論統一還是自由,都要在法治的前提下實現,民主國家是法治國家,只有實現了法治,自由主義或民主主義才能獲得生存的基礎。
這首歌最為人所詬病的是第一段中的“德意志高于一切”。這句話本來是指在封建割據的德意志,統一的民族國家應當高于各個邦國,“德意志”遠比普魯士、薩克森、巴伐利亞或是魏瑪等邦國重要。這個理想在當時其他人的作品里也可見到,如阿恩特那首著名的《何處是德意志人的祖國?》。阿恩特在詩中寫道:“何處是德國人的祖國?/是普魯士嗎?是施瓦本嗎?/是爬滿葡萄藤的萊茵河嗎?/hhgqY8brPvGDrLqHqt61OQ==是海鷗翱翔的貝爾特湖嗎?”然后詩人以副歌的形式反復否定:“不對,不對,/他的祖國要比這些地方更大。”德國統一的最大障礙來自各個邦國的君主以及各種地方勢力,所以詩人們發出號召,為了民族國家,德國人應當放棄邦國利益,放棄地方利益,犧牲小國而著眼于大國。但是在歷史的發展中,德國從一個碎片化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國,從爭取民族統一、不被外國列強欺侮,到成為列強、實行經濟、政治和軍事的擴張,此時的“德意志高于一切”就變了味。“一戰”期間,德國士兵在朗格馬克高地正是高唱著“德意志高于一切”向敵方陣地發起沖鋒;“二戰”期間,德國軍隊正是高唱著“德意志高于一切”去侵略他國、把戰俘和猶太人驅趕到集中營。所以,“德意志高于一切”不可能再是“目光向內”的,而必然是“目光向外”的。
除了認同的困境之外,經歷了第三帝國的集權統治之后,目睹納粹以國家和民族的名義犯下的罪行,不少德國人對于“國家”、“民族”、“祖國”一類概念及其代表的機構都相當警惕,特別是對于民族主義可謂深惡痛絕,而愛國主義也因此受到株連。像《德意志之歌》這樣倡導愛國主義的國家符號,在許多人看來,有以國家的名義強化國家、限制自由的嫌疑,頗為可疑與可憎。所以一部分德國人既需要國歌,但是又在內心里對任何形式的國家符號產生抵觸,而對于《德意志之歌》這樣與納粹有染的國家符號,就更加拒絕。
今天,圍繞德國國歌的舊賬未了,新賬又來。統一大業完成二十年后,當今的德國人接受國歌的障礙早已不像其父輩或祖父輩那樣大,但是又增加了移民問題。今天的德國已不再是單一民族的國家(其實過去也不是),居住在德國的人口中,移民已經占到近10%。不管德國是否承認是移民國家,事實上德國已經是一個移民國家。有的移民已經在德國生活了四代,但是在“德國人”的眼里,他們仍然是“外國人”。即便加入了德國籍、持有德國護照,仍然只是“持有德國護照的德國人”。“老外”們清楚地感到德國社會對自己的排斥,心理上自然產生反彈。二○一○年南非世界杯前夕及世界杯上,移民球員拒絕唱德國國歌的事實,就是這個現實的反映。
動蕩的歷史、分裂的認同、《德國人之歌》的坎坷道路,從《德國人之歌》到《德意志之歌》,從一首政治歌曲到德國國歌,一首歌的歷程清楚地折射出德國近代史的軌跡,形象地敘述了德意志民族走過的道路,德國人的國家—民族認同的危機和困境盡顯其中,歷史不斷地介入當代。然而歷史問題未了,移民問題又來了,《德國人之歌》何時成為“同一首歌”?國歌國歌,怎一個“尷尬”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