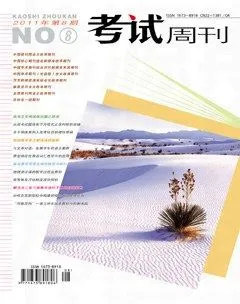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角下對語法性屬的認識
摘 要: 關(guān)于語法性屬問題的討論,已有許多不同的理論解釋。本研究從女性主義角度對語法性屬問題進行研討。關(guān)于語法性屬劃分原因問題的討論是本文關(guān)注的焦點所在。本文首先簡單介紹了語法性屬的相關(guān)研究,然后提出了女性主義理論用以研究語法性屬問題。語法性屬問題的研究是一項復雜的工作,無法取得統(tǒng)一見解。據(jù)此,本文提出以下初步結(jié)論:語法性屬是對社會性別的象征;語法性屬對社會性別的象征是由男人規(guī)定的;中性詞的出現(xiàn)是一種妥協(xié)。
關(guān)鍵詞: 語法性屬 女性主義 陰性 陽性
1.文獻綜述
對語言與性別關(guān)系的考察最早出現(xiàn)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當時人們?yōu)榱私忉屨Z法中的“屬性”概念提出了一種假設(shè),即認為語法范疇是對生物學范疇的象征。這種認識來源于當時人們頭腦中普遍存在的萬物有靈論和神人同感同欲說。當時處在泛靈論時期,宗教還沒有產(chǎn)生,人們對世界的認識還很模糊。古希臘、羅馬人認為萬事萬物和人一樣是有生命、有感覺的,所以人分男女,萬物也分男女,神也不例外。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他們才認為語言中的名詞性屬是對生物學性別(自然性別)的象征。盡管在語法的某些方面并不能證明是人類的性別決定了語法中的性屬,但這種觀點還是得到了一致承認,甚至影響到以后的一些語言學家,如格里姆和洪堡特等。它在語言學理論中曾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除此以外,研究者們還根據(jù)自己非語言方面的經(jīng)驗,認為陽性名詞代表著語言意義的力量,充滿積極的色彩,而陰性名詞則帶有消極和從屬的意味。實際上,陽性名詞代表積極意義,陰性名詞代表消極意義并不是對生物學性別的象征,而是對社會性別的象征。自然并沒有規(guī)定積極的陽性和消極的陰性,是社會對陰陽作出了不同氣質(zhì)的區(qū)分。簡言之,古希臘、羅馬人對語法性屬模仿自然性別的論斷是錯誤的,語法性屬是對社會性別的象征。
在一些根本就沒有屬性范疇的語言中,古希臘、羅馬的假設(shè)就難圓其說。于是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觀點,轉(zhuǎn)而用語法、句法方面的內(nèi)容來解釋語法屬性,并且承認屬性范疇可能影響操某種語言的人對該種語言的詞匯與概念的掌握,因為它可以使人聯(lián)想到自然界中的性別差異。這種觀點認為,是擬人化的手法賦予用陰性名詞所表示的事物以女性的特征,用陽性和中性名詞表示的事物以男性的特征,使它們分別帶上了正面和反面的色彩。這種觀點不僅指出了語法性屬的模仿性質(zhì),而且進一步提出這種語法性屬會影響人的世界觀,會在操有語法性屬的語言和沒有語法性屬的語言的人們中間造成區(qū)別。本文嘗試從數(shù)學、哲學的角度具體分析這種區(qū)別。
20世紀初,馬丁納(F.Mauthner)從東南亞當?shù)卣Z言中性別因素的作用角度來觀察歐洲諸國的語言。1913年,馬丁納指出,是社會和歷史原因決定了語言中存在有性別差異。經(jīng)過進一步研究,馬丁納指出,創(chuàng)造語言的新用法是男性的特權(quán),女性只能接受由男性創(chuàng)造的語言。
20世紀70年代初,魯賓·萊考夫(R.Lakoff)通過研究語言中的性別差異現(xiàn)象,發(fā)現(xiàn)男女之間因性別而引發(fā)的一些語言差異,實際上是現(xiàn)實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現(xiàn)象在語言使用中的具體反映。他在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一文中指出,在語言所反映的世界圖景中,男性居于中心的地位,而女性的形象卻是殘缺不全的[1]。這方面的代表除萊考夫外,還有特魯吉爾、齊墨曼、普什、特洛梅爾-普羅茲等人。
20世紀以來的對與語言性別差異的研究對本文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但這些研究都是從語用學的角度來考察男女對語言的不同使用情況,而本文著手解決的是語法性屬中的陰陽性問題。
2.女性主義
貫穿女性主義始終的內(nèi)容就是對男性中心主義的揭示和批判。男權(quán)制是女性主義中的一個重要術(shù)語,不同的人對“男權(quán)制”有不同的定義。但其共同點是都認為男權(quán)制是一種以男人為中心的、男人壓迫女人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男人處于主體地位,男性被賦予絕對的權(quán)威和價值,而女人處于被支配的客體地位。男權(quán)制主要包括男權(quán)統(tǒng)治、男性認同、男性主體和男性思維[2]
雖然女性一直處于從屬的被壓迫者地位,但這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社會和文化所強加給女性的。西蒙·波娃說:“一個人并不是生而為女性,而是變成女性的。”[3]男女嬰兒呱呱墜地除了生理差異,本沒有什么其他差異。可是隨著他們的成長,男孩子變得陽剛,女孩子變得陰柔,這全是教化的結(jié)果。如果沒有教化,男性和女性在氣質(zhì)上應(yīng)該是差不多的。雄獅和雌獅一樣殘酷,公鼠和母鼠同樣怯懦,但男人和女人卻是那么的迥異。這種迥異不是自然性別的結(jié)果,而是社會性別的產(chǎn)物。
自然性別是人天生的具有的性別,是先天性的。社會性別是人在后天教育中逐漸形成的。社會對不同性別的人的教育具有不同的模式,男性按男人的模式培養(yǎng),力爭做一個頂天立地的陽剛男子漢;女人按女人的模式培養(yǎng),力爭成長為溫柔賢惠的陰柔淑女。人類的發(fā)展史和文明史之所以對男女兩性的自然差異作出選擇,之所以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對人的生命現(xiàn)象中所謂的“陽性”素質(zhì)作出正面的價值判斷,應(yīng)當客觀地理解為,這樣的選擇有利于人類作為整體的生命延續(xù),它是人類作為整體在生存斗爭中不得不作出的選擇,是人類群體生活社會化的需要,是社會分工、提高效益的需要[4]。社會性別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對性別的劃分,更在于對性別的約束。在這個前提下,性別其實是一種隱喻、一種現(xiàn)象[5]。女權(quán)主義就是要為社會性別中的女性謀求自由與權(quán)利,因為在以往的社會中,女性一直處于被壓迫、被支配的地位,她的一切都要依附于作為社會主體的男性。她的命運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男性手中,不論在家庭還是在社會上,她都是低劣的“第二性”。
一切非天然的事物都是可以改變的,法律、道德、倫理概莫能外。社會的、人為的事物不僅是可以改變的,而且是時時都在改變的。女性已經(jīng)被壓迫了太久了,改變的時候到了。女權(quán)主義者就是要反對男權(quán)社會,爭取女性權(quán)利,恢復女性自由,其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xiàn)男女真正平等。所以,女權(quán)主義從本質(zhì)上說,是心界對于物界的征服,精神對現(xiàn)實的抗爭——一切對物欲化人生的拒絕都是這場運動的體現(xiàn)。“至于它的女性性別,只能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個不太恰當?shù)臉撕灐保?]。從這個意義上講,女性主義已經(jīng)超越了她的女性性別含義,成為一種具有普遍價值的思想理論。女性主義思潮因此得以進入科學研究的眾多領(lǐng)域,成為一種看待世界的新視角,并成功地影響了文學批評、翻譯理論、社會學、人類學、符號學、語言學、法學、科學哲學、健康學和哲學等。本文擬運用這種女性主義的思想理論來分析一些語言中存在的語法性屬現(xiàn)象。
3.女性主義下的語法性屬
許多語言中的名詞具有陰陽性(或陰陽中性)的劃分。對某一名詞性屬的辨別固然有一些技術(shù)上的技巧,但深究一步,為什么某個詞屬于陽性而不屬于陰性(或中性)?對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人可以給出確切的回答。有些人甚至認為這個問題是愚蠢可笑的,不值得思考研究,因為語言有時很難說清。不過語言是人的發(fā)明,也是人在使用,它不是天然存在的,所以語言中的一切現(xiàn)象也都應(yīng)該有個人為的原因。
在語言中的詞語被劃分為陰陽性的時候,這個世界是男人的世界,男人是這個世界的主體。由此帶來的無可避免的結(jié)果便是,這個世界具有強烈的男性色彩。世界的一切都呈現(xiàn)在男人的眼睛里,而男人則按自己的主體地位去描述整個世界。語言是世界的一部分,男人就從自己的主體地位出發(fā)去改造語言。
男人是這個社會的主人,他不認同的事物都被樹為“他者”,而最重要的他者當然是女人。所以其他一切相異的事物都被比喻成女人。這就是為什么在幾乎所有的藝術(shù)中,女性總是相異性的化身。在語言中,這種相異性通過名詞性屬的劃分表現(xiàn)出來。其實名詞的語法性屬也是一種比喻。
男人將自己視為世界的主體,當他看到另一個男人的時候,他想,這個人和我一樣,也是世界的主體。當他看到一個女人的時候,他想,這個人和我不一樣,這是一個異于我的人,這是一個“他者”。男人把在他面前樹為主要他者的理想女性化了,因為女人是相異性的有形象征[7]。
男人將自己稱為陽性,并將這種概念擴大化,以至于認為和他相似的事物都成了陽性。當他抬頭看見太陽的時候,他想,太陽和我一樣,因此太陽是陽性。當他看到一個女人的時候,他知道,這個女人是一個異于自己的他者,因此女人就是非陽性,即陰性。當他看到一扇門的時候,他想,這扇門和我不一樣,也是異于我的他者,因此,這扇門也是非陽性,即陰性。我們經(jīng)常疑惑,女人和門之間到底有什么相似之處,以至于門和女人一樣,都是陰性?我想,現(xiàn)在我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女人和門都異于男人。
詞語的陰性和陽性并是不根據(jù)與男人更相似還是與女人更相似而規(guī)定的,而是根據(jù)男人是否與這個事物認同而規(guī)定的。男人認同它,它便是陽性;男人不認同,它便是陰性。所以,陰性并不是根據(jù)它本身定義的,而是根據(jù)陽性定義的,它僅作為陽性的對立面而存在。
也許有人會反駁,你在這里用男性的視角來說明陰陽性的劃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同樣的方法,用女性的眼光也照樣可以得出相同的結(jié)論。這話在邏輯上是正確的,但邏輯上正確的事情在現(xiàn)實中卻沒有發(fā)生。因為,這個世界一直是男人的世界。
除了陽性詞和陰性詞外,在有些語言中還存在中性詞。使用兩性語言的民族堅決地把世界分為“我”與“非我”,而使用三性語言的民族在“我”與“非我”之間還有一個“似我非我”的部分。這個“似我非我”的部分就是中性詞。語言中的中性詞就像社會上的“中性人”,男人們無力辨明它是與自己相似還是相異。所以中性詞的出現(xiàn)是一種妥協(xié),是一種男人們無法分辨的模糊狀態(tài)。
4.結(jié)語
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三點新發(fā)現(xiàn):第一,語法性屬的陰陽性并不是對自然性別的模仿,而是對社會性別的象征;第二,語法性屬對社會性別的象征是由男人規(guī)定和確認的,以往的研究對這一點沒有明確指出;第三,中性詞的出現(xiàn)是一種妥協(xié),中性是一種模糊狀態(tài)。對于語法性屬問題,還沒有從女性主義的角度進行過研究,本文第一次將女性主義理論應(yīng)用于本問題,希望從新的視角研究這個問題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并對以后的研究有所啟迪。
參考文獻:
[1]楊永林.社會語言學研究·功能·稱謂·性別篇[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124.
[2]李銀河.女性主義[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6.
[3]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516.
[4]裘其拉.腦想男女事[J].讀書,1995,(12):34.
[5]趙蓉暉.語言與性別[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37.
[6]韓少功.性而上的迷失[J].讀書,1994,(1):28.
[7]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