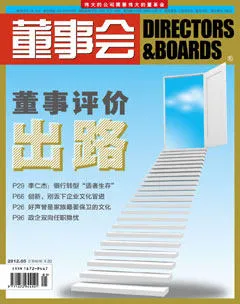海航:流沙上的金融帝國
2012-01-01 00:00:00饒育蕾
董事會 2012年5期

海航再一次地引起了社會的關注。過去一年來,海航在國內外收購活動頻繁得讓人目不暇接,人們關注其資金鏈的狀況,質疑其是否會走德隆的老路。其實,這種質疑十多年來一直伴隨著這家非國企,正是在這種質疑聲中,海航奇跡般地發展壯大,是什么鑄就了成長神話,其成長奇跡能否不斷地自我復制?
金融化:融資依賴功與過
融資能力無疑是海航超速發展的法寶。這家1000萬元起家的公司,在中國航空市場中“如果不做大,就會被吃掉”的危機意識下,不停通過融資得以發展壯大。創業之初的海南航空通過股份制改組,于1993年在STAQ系統上市,通過法人股募集2.5億元資金,憑著這筆資金獲得6億元貸款購買了第一架飛機。從此,海航走上了外部融資依賴的金融化發展道理。
海航采取“一機兩吃”的結構性融資模式:將飛機進行抵押貸款,同時將有關航線的未來收益權再度質押貸款。這種模式下,飛機采購變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融資平臺。海航的采購部門“買飛機壓力很大”,常常為飛機預付款和租金的周轉而焦慮不安,因為“只要來了飛機,就拿去變成錢”。海航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標之一就是各部門的融資情況,要求各部門“借的錢越多越好”。
在強烈的擴張沖動驅使下,與國內外資本市場成功對接,為海航的擴張提供了資金保障。海航“幾乎抓住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所有機會——法人股、STAQ、A股、B股、外資股、H股,整個兒是中國股票大全!”
如果說海航發展的早期以單一的債務融資為主,那么近年來則實現了融資渠道多元化和并購式擴張。海航金融化的邏輯是:用20%左右的資本控制別人100%的資產,再以100%的資產向金融機構進行質押貸款,資金越滾越大,等到資產溢價足夠大的時候就出手,把以前所有的窟窿都補回來。金融化的手段運用和外部融資的依賴,這家僅有20年歷史的企業已擁有8家上市公司、8大業務板塊,形成覆蓋航空、物流、金融、旅游、實業、商業、機場管理等領域的產業集團。
外部融資依賴既成就了海航,也讓其兩次陷入財務危機。一次是2003年SARS疫情下,負債率高達90%的海航集團陷入債務危機。旗下上市公司海南航空成為集團的救命稻草——海南航空2003年14.74億元巨虧超出其它三大航空公司5倍以上,幾乎將公司組建以來所有盈利吞噬殆盡,這其中的4.4億元是與海航集團的關聯交易。第二次是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海南航空于2008年再度巨虧14.24億元,海航集團因將虧損轉入股份公司,反而實現盈利9699萬元,并得以在隨后發行28億元公司債,拯救了因大新華航空上市失敗而瀕臨斷裂的資金鏈。
這種金融化運作以及大規模收購擴張模式,使海航的發展存在內在的不穩定性,雖然集團已形成多元化的龐大融資體系,但更為龐大的融資需求使公司時刻處于嚴峻的考驗之中。
資本運作:財富增長幻覺
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以上市公司為旗艦進行資源整合和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把飛機、土地、股權等一切非流動的資產進行抵押融資或通過置換交易而實現增值,并在循環往復中實現規模的不斷擴張。得益于過去數年中國房地產價格暴漲,海航以高額融資成本所收購的大量資產項目,幾乎無需經營便可獲取高額溢價。
資本運作更是得心應手。2004年、2005年集團下屬海南航空和西安民生投入6億多元建設北京科航大廈,分別于2007和2008年將工程以成本價轉讓給海航集團。2008年12月,海南航空則以17.28億元向集團收購了科航大廈95%的股權。類似的操作還有燕京飯店。兩筆轉讓金額共計23.47億元。高額的關聯交易溢價為海航集團沖抵了因金融危機而導致的巨額虧損,創造了報表盈利以滿足其融資的要求。這樣的交易頻繁而復雜,統計顯示,自2008年以來,除美蘭機場外,上市公司總共發生了157起關聯交易,涉及金額296.3億元。
大手筆資本運作的背后有著一個又一個龐大的融資計劃,而融資計劃背后則是無節制的投資,這種循環使海航時刻處于資金饑渴的狀態,自身的造血功能遠不能滿足其超常規的發展。融資-擴張-再融資-再擴張的發展模式,使公司陷入依賴外部不斷輸血的自我捆綁式的怪圈。
資本運作所產生的資本增值,從本質上來講,并不是真正的財富創造,而是財富的虛擬化增值,是被市場所認同的財富幻覺:只是把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整合到這個企業帝國,共同營造一個繁榮的景象。這種大氣磅礴的氣勢會將所有的問題都掩蓋起來,只有當潮水退卻時,潛在的問題才會暴露出來。當突發性黑天鵝事件爆發時,這種由樂觀情緒支撐的、擊鼓傳花似的財富增值會在一夜之間化為泡影,最終的清算將會到來。人們將會看清整個虛擬化過程破裂之后,誰能繼續生存下來,誰的財富將被洗劫一空。
社會公眾投資者甚至根本不知道誰掠奪了自己的財富,以為這僅僅是市場的無情而已,以為只能怨自己判斷不當、運氣不佳。試想一下,2003年、2008年海南航空兩次巨虧后,社會公眾股東能否像大股東海航集團那樣,通過隨后的外部融資讓自己重回財富起點?
海航是一個標榜社會責任的公司,強調“塑造社會責任感,實現中國商道文化精神”。然而,社會責任不僅是獲取財富后所表現的一種姿態,也不僅是公司經營活動中提供優質的服務,還應該體現在財富獲取過程中是否讓弱小股東得到公平的待遇,是否對整個資本市場的健康負有責任。利他、慈悲、智慧是集團所倡導的“發心”,對處于信息劣勢的個人股東的責任,對資本市場公平的責任,是否應該列入其社會責任的范疇?
實業經營:造血功能不足
海航對德隆的反思是,一定要資本運作與實業經營兩條腿走路。為避免重蹈覆轍,海航強調兩條腿走路,注重實業的現金流。值得肯定的是,海航很多板塊的實業是精進的、服務是一流的。
然而,實業領域的收益率和成長率遠不能與資本運作的收益相比擬。雖然集團2011年營業額達到1200億,現金流狀況良好,但盈利卻是微薄的。根據中金公司分析,海航集團2010年、2011年總資產回報率分別為0.48%和0.71%,這個數據既低于美國《財富》雜志2011年公布的“美國500強”總資產利潤率2.09%,也低于2011年我國央企的3.2%。
如此低的總資產回報率,既說明集團存在大量閑置的或低效資產在吞噬利潤,也表明經營現金流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其自我造血功能遠不足以支撐龐大的擴張購并計劃,擴張所需要的資金嚴重依賴外部融資。
基于外部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內部資金需求的壓力,集團在2011年中啟動了內部調整轉型,對一些與集團戰略性支柱產業關聯度不強、發展空間不大的企業和項目實施關停并轉。在3-4個月內關掉了230多家公司、400多個項目,撤消了華南、華北、東北等眾多區域總部和平臺公司,以遏制投資沖動。
然而海航收縮的目的,是以更加激進的方式向海外擴張。集團的發展方向是“由單純的生產服務型向生產服務與投資管理并舉,進而向以投資管理為主導的模式轉變”。低效資產的處置固然能夠變現資產、釋放資金,但集團以更大范圍的資本運作、更高速度地向海外擴張,其可能產生的財務空洞將更加難以避免。
“超級X計劃”:似曾相識的豪邁
一份海航內部資料表明,海航正在執行一項“超級X計劃”,即“2015年以6000億元進入世界前100強,2020年1.3萬億元進入世界20-30強,2025年以1.6萬億元進入世界前10強”。歸納起來就是,“未來5年集團收入達到萬億,成為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電網之后第四家萬億級企業”。
這個目標是集團發展的共同綱領,是集團未來成就的標志,是一種理想,一種全員上下共同追求的精神境界。然而,這樣的豪言壯語我們太熟悉了。
巨人集團總裁史玉柱在反思自己決策四大失誤中的一條就是“盲目追求發展速度”,其當時的產值目標定位是:1995年10億元,1996年50億元,1997年100億元;猴王集團創始人易繼純被稱為“易大膽”,猴王集團早期舉債擴張取得的成功強化了其投資策略的冒進,雄心勃勃地推出了“三百”方針:建100個企業,開100家商店,搞100個公司;大宇集團的金宇中1993年提出“世界化經營”戰略目標時的海外企業只有150多家,短短5年內增至600多家,平均每3天增加一個企業;孫宏斌依托資金快速周轉理論造就了“順馳模式”和“順馳速度”,其2004年6月提出的戰略目標是“趕超萬科、成為全國第一,3年后做到300億甚至500億,10年做到1000億”;安然僅用10年的時間,就從名不見經傳的公司發展成全球最大的天然氣經銷商、世界最大的電力交易商,在全球擁有3000多家子公司,控制著全美20%的電能和天然氣交易,位列世界500強中的16位……
面對前人的教訓,人們常常會樂觀地認為自己是例外。美國學者詹森認為,經理們都有擴大公司規模的意愿,因為其權力隨著控制資源的增加而增加。銷售額是最能被清晰觀察的經營成果,給人直接的推動力和約束力,最容易直觀激勵企業員工的斗志和熱情。然而,它卻偏離了理性的價值尺度,可能將企業引入誤區。
企業的成長發展具有內在的客觀規律,依賴外部融資能夠獲得炫目的發展,卻像一個被神化了的泡沫,不具備真正抵御風險的能力。作為資本運作的奇才,杰克?韋爾奇自己卻說,“我對公司最大的貢獻是拒絕了1000次至少看上去很值得投資的機會”。
“萬億目標”:融資枯竭風險
海航規劃的“萬億目標”可能成為難以承受的負擔,可能將集團逼入融資枯竭的境地。以集團2011年1176億元銷售額和2665億元資產規模為基數,假設維持2011年的總資產周轉率0.4413和總資產回報率0.71%不變,我們不妨對“超級X計劃”的融資需求進行簡單的匡算。
估算結果表明,要達到規劃的銷售額,2015年、2020年、2025年的資產規模將分別達到1.36、2.95和3.63萬億;假設全部盈利都用來發展,公司未來三個五年計劃的融資需求分別約為1萬億、1.5萬億和5612億。這意味著,海航2012-2015年平均每年需要融資2500億元,而2016-2020年每年需要3000億;在未來的近10年內,集團每年都要建設一個如今規模(2665億)的海航!
毫無疑問,海航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資金緊迫。雖然擁有體系龐大的融資平臺,但過于龐大的融資需求將使海航處于超乎想象的資金緊張。過高的融資依賴使海航各種融資平臺都有融資枯竭的危險。
股權融資的局限。海航的發展離不開經驗豐富的投資人,包括早期的共同創業者,定向增發或股權收購過程中加入的投資人等。資本的逐利性使其在投資時就設計了退出的時機和渠道。海航大新華“紅籌上市”是典型的退出模式設計。一旦在香港上市成功,海南省發展控股公司、索羅斯基金等早期投資人都得以在資本市場成功退出,不過大新華航空上市遇阻使海航集團陷入空前的債務危機。目標不同的股權資金必然有其融資的局限性,既不可能在量上滿足海航極度的資金饑渴,也不可能與其結下生死盟約。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公司越是資金饑渴,越是難以獲得它的青睞。
資本市場融資的落寞。海航集團通過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復雜的關聯交易,將資金源源不斷地輸入集團。以海南航空為例,自1999年上市13年來,它通過IPO、增發、配股以及可轉債發行一共募集了95.36億元資金;期間僅有5年分紅,分紅總額僅為3.76億元,占募集資金的比例僅為3.9%。海南航空上市后的復權漲幅僅為65.97%,與萬科A同期846.59%漲幅相比相去甚遠。
海航慣用“重組上市-放水養魚-利益輸送”的方式轉移上市公司的資金。然而,“提款機”的質疑既受到投資者的反感又引起監管層的關注,增發配股等再融資自然受到冷落。過去一年間,海航集團旗下上市公司的股價均大幅下跌,跌幅超過30%,有的甚至腰斬。2011年3月,西安民生公布定向增發方案后,股價一路下跌,被市場看成是“垃圾題材股”。2012年1月29日,海南航空欲募資80億元,其中60.84億用于償還銀行貸款的方案同樣引發股價一路下跌,有些機構投資者明確表示不會參與定增。
抵押貸款融資的約束。海航將抵押貸款融資發揮到了極致,一旦購置了土地、飛機等固定資產,就會將其抵押給銀行或信托公司融資。質押上市公司股權獲得銀行貸款也是重要的途徑,海航旗下上市公司股份大部分都被質押。例如,截至2010年末,大新華航空公司所持的海南航空17.16億股中的16.06億股被質押,質押比例為93.6%;而海航集團在西安民生、易食股份、ST筑信、綠景地產的股權則100%被質押。僅2011年以來,海航集團控制的上市公司、海航資本、海航商業、海航置業等就累計進行了11次股權質押,質押總股份數達到7.9億股,市值估計達60.37億元。
出于風險的考慮,包括建設銀行在內的多家銀行已停止對海航集團的貸款,未跟海航建立合作的銀行大多數不考慮跟它合作。某些銀行由于“海航的主業過于模糊,不斷并購更像是黎明前的瘋狂”而懼怕風險,無法放心踏實地與其合作。
金融資本融資的尷尬。海航集團通過旗下的“海航資本”開展投資銀行、租賃、信托等多項金融業務,但其核心業務還是為集團提供融資服務,發行企業債和設立信托計劃是最常用的融資手段。
信托計劃方面,海航集團通過信托公司在2009-2011年共發行16個信托計劃。集團還常向員工發行信托產品籌集資金,內部信托計劃常與一系列資本運作相聯系,其典型的模式是:旗下上市公司參與項目初期建設——集團以成本價收購——借用內部信托融資完成項目——高價賣給上市公司,通過這種方式向集團公司輸送資金。由于利益輸送動機明顯,這樣的收購事項曾遭上市公司股東大會否決,從而使集團的計劃受阻。
企業債方面,海航集團通過海南航空、海航商業控股等主體發行了各種債券。然而,最近中金公司發布的固定收益研究報告,對由海航香港為發行主體、由海航集團擔保的5年期利率7.5%的點心債做出了“回避”的評價。其理由是,盡管海航集團規模很大,也有一定的現金流產生能力,但債務負擔較重,融資需求很強,由于外部融資環境惡化,尤其是股權結構和關聯方關系復雜,因而對其信用基本面持謹慎態度。
政府資源利用的壓力。綁定地方政府可謂海航擴張的重要戰略。為獲得更多低成本的資源,海航集團先后與海南、甘肅、河南、浙江、天津、北京、陜西、重慶、貴州、湖南、云南等上百家省市地方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通過融資租賃的方式與地方政府合作參與基礎設施建設。
海航讓自己的產業向國家政策和發展戰略靠攏,獲得了地方政府的普遍認可,并以融資租賃的方式向地方政府提供資金,投資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為自己搭建更大的融資平臺,獲得大量政府廉價資源、政府注資、稅收優惠等政策性支持。
借助國家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進軍地方,從戰略意義上講是很積極的,但這將需要集團投入大量的資金,遍地開花的基礎建設資金需求將嗷嗷待哺,大量資金不得不通過抵押貸款的方式來滿足,必然導致負債率的大幅上升。此外,政府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周期長,在國家房地產調控政策環境下,土地或建設項目的變現能力相對較弱,這也是對海航集團資本運作和外部融資能力的極大考驗。
海航期待:有機增長的回歸
繁榮昌盛,這是所有企業期望達到的目標。企業可以穩健地從昌盛走向更加繁榮的昌盛,但也有大量盛極而衰的例子。海航的運作模式里有GE的影子也有德隆的質疑,人們關注的是,海航究竟會是“GE第二”還是“德隆第二”?其實,我們期望的答案是“海航第一”,期待它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獲得永存。
“數一數二”戰略能在GE卓有成效地貫徹,是以其歷經百年發展形成的完善內控機制為基礎的。這一機制在不斷強化概念戰略積極導向的同時,也不斷削減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而迅速暴斂巨大財富的德隆顯然不具有GE內控管理上厚重積累的優勢。德隆進入金融業的目的是插上一根資金管道,為其大規模擴張沖動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供給。由于其所邁進的新領域不能迅速獲得彌補資金缺口的收入,不僅使金融業務難以支撐,而且使實業也深受其累,一旦資金管道枯竭,實業也隨之消亡。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自身的成長規律,都有成長的極限,企業更是一個有機的實體,有著自我成長的軌跡。當人們驚嘆于蒙牛“一頭牛走出了火箭的速度”時,它卻因三聚氰胺事件而遭受現金流危機,成為“哭泣的老牛”。SARS、三聚氰胺已然成為過去,海航是否為高速前行途中的下一只“黑天鵝”做好了準備?
一個孩子剛出生,人們會為他每天看得見的成長而驚喜,但成人以后,繼續長大和長高卻違背了人類成長的客觀規律,我們更注重的是其心智的成長和能力的提高。人們也一直尋求長生不老的秘訣,但在客觀世界面前人類永遠都是渺小的,要讓自己永恒,或許得把自己修煉得像常青樹那樣,看似靜止卻內在地澎湃著永恒的生機和能量!
戰略性地休整集團的擴張步伐,整固現有產業,更多地注重實業領域的財富創造,回歸有機的成長軌跡,這是人們對海航的期待。
(作者系中南大學商學院金融系主任,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