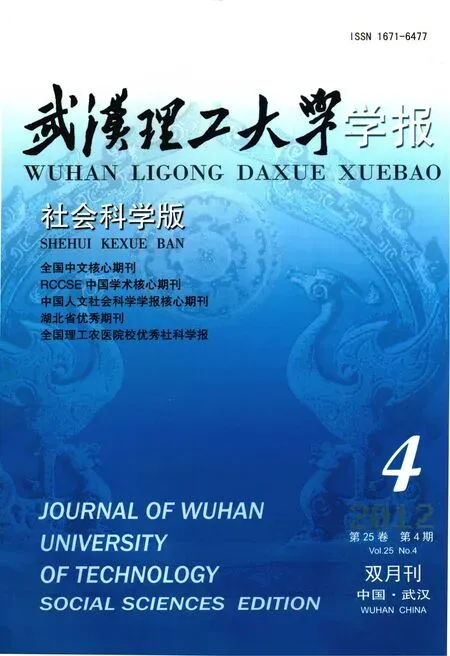基于意義建構信息利用偏差彌合的釋義
曾 丹
(武漢理工大學圖書館,湖北武漢430070)
一、引 言
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時代,信息使用無論從概念上還是經驗上均對圖書館和信息研究提出了挑戰,例如,如何瀏覽與工作有關的網頁?參考咨詢館員在開展信息服務時如何產生有益的效果?當人們利用從不同來源和渠道獲取的信息時會有何種過程發生?這些我們往往很少從理論上去探尋它。本文試圖通過意義建構的設計思路對信息使用過程作一探討。Brenda Dervin在1976年提出情境導向的替代性研究典范。此替代性的典范認為,信息是否有意義是由使用者來定義的,唯有在信息對使用者而言有意義的情況下,信息才能發揮其功能。因此,要了解使用者的信息查詢行為,不能單就其透過哪些策略,使用哪些資源來了解,更應該探討使用者在哪種情境下,找尋何種正確的信息,會利用何種策略,以及其原因為何等問題。意義建構理論可以定義為,無論是內在行為(即認知)還是外顯行為(即過程),都允許個體在空間和時間上設計或建造自己的行為。意義建構的活動主要包括:信息的尋找、處理、建立和使用。意義除了包括知識、信息的因素,還包括如概念、直覺、反應、評估和問題等能反應個體對情境解釋的主要因素。意義建構是一個過程,意義是該過程的產物。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意義建構的行為是種溝通行為。意義建構理論意指發展一套方法,研究人們在每天經驗中所發生的意義建構活動[1]153。環境與個體角色的組合形成了信息查詢行為的情境基礎,而信息查詢行為的直接動力源于在這些基礎的交接處形成的某些行為障礙以及次結構的相互作用而引起[2]。信息行為建構的取向非常豐富,但其核心只有一個,那就是以用戶為中心,強調個體對信息的積極探索,主動發現,以及強調個體在信息行為過程中對信息意義主動建構的關鍵作用[3]。
二、意義建構在信息使用研究中的影響
在圖書館和信息研究中,信息使用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在信息需要和查尋的情境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意義建構理論對信息使用的研究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由Dervin在1972年提出和Nilan在1986年提出的用戶中心論在信息需求、查尋和使用的研究中被廣泛接受。如Taylor[4]大量借鑒了Dervin[5]提供的信息使用的實證結果,但他沒有反映出用意義建構界定信息使用的概念。Pettigrew,Durrance,and Unruh[6]提供了一個最新的案例,他們借鑒意義建構分類,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界定了在線社區網絡使用。意義建構種類的歸納有助于各種特定實證研究結果的映射,實驗表明,情境是信息(或差距)的需求,障礙是用戶在表達需要和尋求信息和結果中遇到的問題,幫助是用戶通過信息查尋過程獲得的。然而,信息使用(如gap-bridging)的概念并沒有反映在上述研究的更多細節中。1976年Dervin發展的的意義建構理論,“由系統為中心轉移到以用戶為中心”成為10年后用戶信息研究典范轉移的核心。意義建構把數據收集和分析技術,在20世紀最后幾年,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方法論。伴隨信息行為研究的興起,該方法論為信息的需求,尋求,背景和過程提供了導向。后期的方法論更加突出強調“動詞”(verbings),包括信息尋求和使用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各種變量(如:時間,空間,關聯,相似)。與初期圍繞個體信息需求的情境、鴻溝及使用的研究相比,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而且,意義建構方法同樣適用于不同的認識論,比如使用述說分析能進一步強化意義建構的解釋力。
三、Dervin的意義建構理論
Branda Dervin于1972年提出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意義建構理論,即研究個體如何從經驗中建構意義的方法,而此方法被用于研究所謂的信息需求與滿足的經驗,也就是研究人在情境中的意義建構,如信息查尋、信息使用、信息判斷是否產生效用等等。其認為知識是由個體建構而成的主觀產物,只有通過觀察才能理解并實現與他人的信息共享,信息尋求是主觀的建構活動,在線檢索的過程是由于互動的本質、檢索提問從而產生多種情境下形成不同的意義建構的過程。意義建構理論是一種通過傾聽用戶,了解用戶來解讀他們過去的經驗、目前的情境、未來可能面臨的境遇,以及使用者在所處情境中如何建構意義和制造意義。意義建構方法論是運用時序與結構式訪談法技巧(即便是中立提問也強調討論的結構),以減少詮釋的可能性。前者詢問受訪者描述其信息尋求順序,并根據情境-鴻溝-使用的基本模型,分析其尋求的結果;而后者運用中立提問訪談技巧,引導用戶借由自己的陳述表達其信息需求。Dervin意義建構理論以隱喻圖式的方式提出,包括情境、缺口、橋梁、結果等四要素,并圍繞這四要素進行實施。Dervin以三角形圖式表示其理論,其中情境指時間和空間,界定了信息問題產生的背景;缺口指因信息不連續性而形成的理解差距;結果表示意義建構處理后的運用;橋梁則為縮小或消除狀態與結果之間差距的手段和方法。新的意義建構模型在三角模型基礎上被提出,橋梁作為中介或行為,在消除或彌合狀態與結果之間的差距上,其作用得到了直接體現。圖式,是指個體對客觀世界的理解和思考的方式。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心理活動的框架或組織結構。圖式是認知結構的起點和核心,或者說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基礎。因此,圖式的形成和變化是認知發展的實質。見圖1,圖2。

圖1 Dervin的意義建構三角

圖2 Dervin的意義建構模型
在信息尋求行為研究中,我們可以這樣理解Dervin的意義建構理論:個體在某個情境中停頓下來,由于某種認知偏差使其產生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意義建構者就有可能利用“信息尋求”這一“橋梁”來不斷獲得信息,把其面對的差距填平,從而到達“橋梁”對面。這個模式可能是時空中某個特定的事件,或是認知上某種特定的狀況。對某人來說屬于鴻溝的,對另一個人可能不是。這一刻屬于幫助的,下一刻可能不是。所以這不是一個線性的歷程,也并非為著某種目的而進行,而是對有序和無序的現實進行往復意義建構,從而使個體不斷由一個認知狀態過渡到另一個認知狀態。Dervin模型強調經驗的累積和環境-差距-幫助的循環互動。經驗豐富的用戶可以在差距和幫助之間快速獲得聯系,通過精確的信息查詢獲得信息,填補知識差距,進而解決問題。通過教育可以達到經驗的傳承和共享,縮短盲目搜索的過程。
(一)研究視域
Dervin理論把信息的尋求及其結果看作是搭建個體(信息用戶)認知缺口(差距)的一座橋梁,并認為在一次完整的信息查找行為過程中,可以包含多次認知缺口(差距)的“彌合”,因此,德爾文的“意義建構”理論已使信息行為研究進入了認知領域,并體現出時空的概念含義。
(二)研究視角
Dervin模型與其他模型具有明顯的不同,它是“從信息論的角度”對信息行為進行的描述,其目的是提供一個如何通過探究情境來探索整個信息尋求行為的框架。我們已有這樣的共識:信息即負熵,其功能在于減少不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信息的獲取及利用正是起到了最終減小或消除認知上“不確定性”的作用。
(三)研究關注點
Dervin意義建構理論認為,信息是對有序和無序的世界進行意義建構的工具。信息需求的產生同個體現實所處的認知結構(情境)密切相關,更確切地說,是與認知上的不確定性密切相關。而信息查找和信息使用結合在一起作為一座橋梁,幫助個體實現由認知上的“不確定性”向“確定性”轉化。用“復雜系統”的觀點來看,信息行為的研究已經超越了情報學學科的范疇,而被置于更為深刻的背景之下。它關注的是能夠解釋問題情境本質的與信息行為相關的質疑方式,信息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減少或消除使用者的不確定性以及迷惑,因使用信息而產生的結果的本質等等。它將研究者的注意引向用戶尋求活動的首要原因在于認知不適[7]。
四、意義建構的基本假設
盡管出現了一些重點的轉移,但意義建構理論提供的是一個方法論。不是一種簡單的“信息查尋行為模型”,而是“一系列的假設,一種理論的探索,一種方法論上的方法、一套研究策略以及一種實踐”[5]。而關于信息本質、信息使用的本質、信息傳播溝通的本質等一套元理論假設和主張,它被看作是情報學領域的“元理論”,即對構成某一知識領域理論框架的依據所進行的分析和認識。另外,德爾文的“意義建構”理論還涉及到波普爾的“世界3”(信息系統)和“世界2”(主觀認知),其研究問題的方法也可納入哲學的范疇,可以認為,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奠定了信息尋求行為研究的基礎。生活是由一連串的行動所構成;信息搜尋是從人的自由行動受到阻礙時產生的;當人面臨問題,內在知識不足以理解外在事物時,便形成知識的差距;為彌補差距,需要從其他人或資源獲取幫助,就會去尋找信息。該理論的哲學基礎在于Richard F.Carter有關“不連續”的假設。意指人們每天的生活情境一直在改變,每一種改變對他的意義均不同。Brenda Dervin則以當個體在生活中碰到阻礙時,其解釋問題的方法、定義阻礙的策略、如何跨過該阻礙等步驟,來描述意義建構的過程。阻礙產生和去除的定義完全視個體和情境因素而定。所以,意義建構理論可以說是“情境-阻礙-使用者/幫助”等一連串的過程[1]153。意義建構理論的核心假設包括:第一,信息使用是一種建構,而不是一種傳遞。在意義建構的不連續的假設中,信息被概念化成人類在時空中某一特定時刻下所產生的意義。它假定“如果確實有某種次序存在,它是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產生連續的狀態”,同時也非人類觀察所能得到的。第二,對信息使用和信息系統的認識不是從觀察者的角度而是從使用者的角度。第三,信息使用不是一種恒定的狀態,而應被視作一種過程。意義建構關注行為,所以它假定個體在信息與系統使用過程中需要學習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們在他們的世界中建構意義時所采取的步驟[8]。Dervin特別關注研究信息使用的替代手段,她認為信息需求是人(思想或身體)的行動在無法正常執行的情況下或被阻礙的狀況下出現在大腦中的問題,這就是認知或知識的斷帶。在她看來信息使用即是要架起逾越斷帶的橋梁。該理論可以解釋為允許個體設計和建構自身時空運動時來自內部的認知和外部程序上的行為[9]。“意義建構”具有普遍性,主要是從個人每天生活之中面臨到問題情境時所采取的認知策略出發,讓個人在特定時空下建構或設計自己的動作[10]。意義建構認為,個體是存在于一個不斷變換的時空下,建構的動作就是策略,而這些建構的動作可以是曾經使用過的想法的重復,也可以是面對新情況出現時設計的策略。假設個體的信息是由個體針對不同情境反映出來的,個體信息的使用是在試圖彌補差距或不連續的狀態。在時空的某個特定時刻,面對不同的差距,個體會使用不同的策略。因此,從方法論角度來看,它是研究人類自身在經驗中如何建立意義建構的過程[11]。
五、差距-彌合:源域表征
意義建構概念化的多種情景運動狀態,揭示了信息接收者確定在一個特定時刻自我停止或行動的方法[12]242-243。意義建構一個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假設就是關注現實世界的不連續性,由于現實世界中存在跨越空間、時間的變化和人們如何建構跨越認知差距的橋梁來解釋其間的差異,總是可能得到多重解釋[13]。這個差距在本質上是主觀的,它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的時刻,個體通過不斷的信息交換重新評估他/她的研究方法。差距代表問題或在上述情境下要求闡明的問題。回答這些問題可以被看作是個體試圖建造跨越差距橋梁的構造活動。圖3描述了間隙-彌合的情況[12]238。

圖3 面對偏差(GAP)的情境
由于空間限制,這里描述的差距-彌合參照只有一種類型的運動狀態下的情境,即在“沖刷”的境況下道路突然消失。在“沖刷”情況下,個體必須停下來找到一個新的開始。首先,可以設想,信息接受者,停在差距的邊緣,將確定其主要需求。面對差距,明確差距,試圖彌合差距,隨后考慮采用的戰略和戰術。面對差距,信息接受者開始評估“障礙”的特性:他或她可能有多種預期結果的假設(各種幫助,可能的障礙等)。
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遭遇差距是很重要的:從信息接受者的角度看,無論差距大小,他或她均會設想如何得到可能的幫助。這個期待為采取下一步驟提供了動力。因此,我們可作出分析區分項目(a)基于以往的經驗以及與他們相關的預期假設來規劃差距-彌合,以及(b)縮小差距。當然,這些階段可能會重疊的。
彌合的構建見圖4[12]238。

圖4 彌合的構建圖
正如圖4所表明的,“信息”橋的構建包括識別,查詢,并結合了諸如思想、信仰以及敘述各種元素。可以這樣認為,特別是在一個相當大的差距的情況下,橋梁建構中可能會經歷幾個階段;橋梁建構者組合和塑造不同的元素,他或她可能站在部分建好的橋上同時望向差距的另一端。當足夠數量的元素被發現和組合,一個足以跨越差距的橋梁已經構建。
圖4必須是簡化的,可以認為差距-彌合始終是有目的和目標定位的。然而,間隙縮小可能會有多各種途徑,它可能是完全反復無常的。圖4不足以具體闡明意義建構隱喻的源域特性。我們將繼續分析間隙橋接概念的論證,可能有助于從意義建構的角度澄清信息使用的特性。一般情況下,差距-彌合,如圖4所示的隱喻表明,信息的利用是一種高度語境的活動。信息的利用依賴于何時何地發生的和已遇到的何種差距。此外,隱喻暗示著無論何種差距問題都是能夠彌合的(例如通過繪圖表達想法或認知)。圖3與圖4還表明,面對差距和差距-彌合,涉及的不僅僅是信息查詢和利用被當作一個有序現實的事實說明,而是更廣泛的問題。根據假設,在構建跨越現實差距的橋梁時要結合認知因素與情感因素。上述解釋表明,差距-彌合隱喻使得信息使用現象,是通過提供一個框架得到理解,這個框架提出了有關信息使用情境的具體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隱喻對橋的特性提出了有關的建議,例如何種認知和情感要素可以參與信息使用的過程。
然而,分析源域和目標域概念間聯系是困難的,因為就其本身而言,“修改”(作為一種塑造或構建活動)被用作隱喻的意義。我們試圖借助隱射其他具有鏈接目標域概念(修改)功能的隱喻(建構),使源域概念(差距-彌合)更容易理解,事實上,這種設置很容易變得模糊。上述解釋更多地反映了信息使用現象概念把握上的困難。
Dervin的信息使用方法更多植入了動態的“進行時”觀點。意義建構采用不同的動態的“進行時”處理“建構”橋梁,并得到結果[13]。這個特性的主要內容在圖4中被貼切而具體地描述。尤其是,意義建構關注的動作,也就是,人們以何種方式制造或使用“認知、思考和結論,態度、信念和價值觀,感情、情緒和直覺和記憶,故事和敘事”[12]239。
因此,verbing被假定為一般水平的分類,這種分類是想法“建構”和多版本的現實生產的實踐。可以推測,信息設計最終是基于名詞和動詞或“僵化”和“流動性”之間的思辨[13]。名詞代表相對穩定的現實表現;而動詞意味著這些事實被近似看成是某種可塑性與挑戰性的方法,因此,特定的情境是可設計的。
六、意義建構存在的不足
Dervin通過確定和使用“意義建構”的思想,將信息使用同用戶主體更緊密聯系起來,在觀念上從系統驅動轉向了用戶驅動。即使信息科學的理論研究在認知領域的高屋建瓴下,取得了重大進步,但基于"認知"的信息科學僅僅是個體的心理結構或內心世界的表象,沒有充分反映信息行為的所有過程和事實。信息認知觀過度強調內在的表達和極端個體主義,對于信息使用和處理的這一社會維度,未給予足夠的關注與重視,從而造成認知觀的社會視野極度狹窄。因此,個體用戶和系統自身的社會情境均自然地被忽視。
意義構建不僅是個體的,而且是社會性和集體性的,人們使用的概念和意義決非單純個體的,而是共同文化的產物,是一種社會建構,因此可以認為社會維度的缺失是信息學認知觀的一個的缺陷。從廣義上講,在系統觀指導下的信息科學領域由于對認知維度的長期忽視,導致了信息科學落后于時代的發展,才更突顯認知范式的重要性。只有當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認知情境”時,才有可能引入社會這一維度,去綜合地考察一個“綜合認知情境”[14]。
七、結 語
意義建構強調個體理解,而非協同認知,它不能解釋群體與組織性的程序傳播與信息交換。然而,意義建構的研究并不僅限于個體認知,同時把時間、空間、權力、文化、個體與協同等動態影響也加以考慮。雖然其方法論在群體研究上有操作的難度,但可以與其它一些理論的質性或詮釋研究相結合,而產生最大的優勢。差距-彌合是一個開放式的和隱喻建構理論,為信息使用而產生的各種現象提供了認識。在未來,差距-彌合隱喻會有一個潛在的進一步規范和限制的需求。此外,以描述不同設置狀態下差距-彌合的各種表現形式的實證研究結果,對信息使用將是一種有益的分析。將差距-彌合的概念與其他信息使用方法做更詳細比較很有必要的[15],如提供社會建構的觀點。總之,把意義建構放在一個比較的視野會更清晰地揭示其潛力,將其自身的發展作為一種信息使用的方法,幫助研究者把研究的焦點從歸類轉移到程序,使研究能反映更為復雜的信息行為。
[1] Reijo Savolainen.The sense-making theory-an alter native to intermediary-centered approach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M]∥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eds.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History,Emprical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London:Taylor Graham,1992.
[2] 喬 歡,周 舟.意義建構理論要義評析[J].圖書館雜志,2007(5):8-10.
[3] Dervin B.On studying information seeking methodologically:the implications of connecting metatheory to method[J].Information Process &Management,1999,35(6):727-750.
[4] Taylor,R.S..Information use environments[M]∥B.Dervin &M.J.Voigt(Eds.).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Vol.10.NJ:Norwood,Ablex,1991:217-255.
[5] Dervin,B.An overview of sense-making research:Concepts,methods and results to date[Z].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Dallas,TX,1983.
[6] Pettigrew,K.E.,Durrance,J.,&Unruh,K.T..Facilitating community information seeking using the Internet:Findings from three public library community network system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2,53(11):894-903.
[7] Niedwiedzka,Barbara.“A proposed general model of information behavior”Information Research,2003,9(1):paper164[EB/OL].(2011-01-10)[2012-01-12]http:∥informationr.net/ir/9-1/paper164.html.
[8] Shera.J H.An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Library Science[Z].The Foundations of Access to Knowledge:A Symposium.Syracuse University,1968.
[9] Luciano Floridi.On Defin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s Applied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J].Social Epistemology,2002,16(1):37-49.
[10] B.C.Brookes.Foundation Science,PartⅥ:the Changing Paradigm[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981,3(1):3-12.
[11] 賀 穎,張慶一,陳士俊.知識結構的間隔與情報思維方式[J].圖書與情報,2007(5):47-51.
[12] Dervin,B.&Frenette,M.Sense-making methodology:Communicating Communicatively with campaign audiences[M]∥In B.Dervin &L.Foreman-Wernet(Eds.)Sense-making methodology reader.Selected writings of Brenda Dervin Cresskill,NJ:Hampton Press,2003.
[13] Dervin,B.On studying information seeking methodologically:The implications of connecting metatheory to method[J].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1999,35(6):727-750.
[14] 蘇瑞竹.論情報學的認知觀點[J].情報科學,2000(6):511-514.
[15] Tuominen,K.,&Savolainen,R.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use as discursive action[C]∥In P.Vakkari,R.Savolainen,&B.Dervin(Eds.)Information seeking in context.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Needs,Seeking and Use in Different Contexts.London:Taylor Graham,1997:81-96.